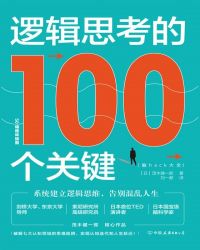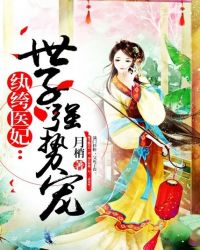国潮1980_分节阅读_第24节
D-理由却是,自己要仔细观摩学习,从中寻找错处。
张口撒谎,不但掩盖了自己贪婪性情,反倒愈加显得孺子可教也。
老爷子自然被哄得十分开心,高高兴兴去上班了,让他自己一人家里慢慢看。
至于这些东西最后要怎么处理?
这就是当天晚上,师徒俩人坐在一桌子好酒好菜旁,要商量的议题了。
说起来康术德带宁卫民去鬼市的初衷。
原本就是为弄两件儿值钱的货色,然后快速倒手卖出去,换点资金给宁卫民当学费。
从今往后,老爷子是打算就让宁卫民每天去鬼市上转悠去了。
说兹要宁卫民自己觉着看明白了,或者感兴趣就可以下手买。
买对了当然是好事。
即使买错了亏了钱,也没关系。
因为主要目的,还是借此让宁卫民开眼,长学问。
在老爷子看来,真本事就得这么练出来。
说得再多,耳听为虚。
怎么也没有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强。
人只有吃过亏了,疼过了,才会把教训记一辈子。
人也只有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才爱琢磨。
所以老爷子表示愿意放任宁卫民去寻摸他自己感兴趣的品类去,好以此领他进门。
哪怕老爷子再陪着去,也不会为宁卫民做现场指点。
但回过头来,却肯定会对着东西,告诉宁卫民哪儿错了,为什么错。
对师父的这个主意,宁卫民作为徒弟是相当感动的。
同时也觉得很有趣儿,很具挑战性,还真有点摩拳擦掌,急不可耐的兴奋。
这怎么论,无论前景还是钱景,确实都比他倒腾热带鱼强多了。
可唯独就是他一时舍不得那些东西啊。
觉得哪怕不算枢府瓷,可另两件瓷器和书画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宝贝。
未来的价值至少是以千万计算的,现在卖也忒亏了。
无论怎么选,他心里都疼。
好在师父就是师父,康术德是个有成算的人,直接就告诉他了。
肯定得把书画卖了,压根不用选,也没的商量。
原因就是因为保存书画是需要有保存条件的,他们的居所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像那个大户人家就差点把这两件东西给糟践了。
这两幅字画,其实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与其捏他们自己捏手里,让书画霉了、残了,还不如卖给国家的好。
这既能让这两样东西得到妥善保管,也顺带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这才是对国家对私人都较为合适,相得益彰的法子。
听了这番话,宁卫民这才明白了师父的心思。
他不能不承认老爷子这话有理,也不能不佩服起老爷子的精深韬略来。
到底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做大生意的老前辈,从思路上就比他这小老板儿高了一筹。
而他自己的贪心和不舍,反倒是真有可能把两件宝贝耽搁在手里,彻底变成废物的。
那不卖还能怎么办呢?
卖!
有意思的是,也是多亏这一卖啊,他又从中发现了另一片广阔天地。
非但是不觉着卖亏了,反倒还觉着卖值了。
因为无意间,这又证明了老爷子告诫他那句话了。
人必须得勤快啊!
别看就为了卖画,多走了几步路,却让他看到了风光无限。
(注1:伤了,书画行话,指书画质地因虫蛀、水湿或外力摩擦而损伤,若地子缺损,就叫“残了”“缺了”。)
(注2:起霜,书画行话,指因潮湿而发霉)
《国潮1980》正文 第五十三章 名店
在京城这地界儿,要说卖画,去哪儿卖啊?
那还用问嘛,当然是奔琉璃厂的荣宝斋了。
琉璃厂是京城中驰名中外的古文化街,就位于和平门外。
因元代曾于此设窑烧造琉璃瓦而得名。
明代永乐中期,将元代的琉璃窑又扩大为厂,故称“琉璃厂”。
不过这块地方真正的兴旺发达起来,那是清代康乾两朝的事儿。
康熙朝,朝廷下令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朝,朝廷又下令编纂《四库全书》。
结果正是这两部大部头的编纂任务,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学者响应,各自带书进京。
又因内城外城有别,当时除旗族和少量工匠之外,民人只能住在外城。
于是乎,不但前门附近逐渐变得会馆林立。
琉璃厂也成为这些学者们,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们,看书、售书、购书和换书的最佳去处。
与之同时,还引发了金石考古之学的发展与发达,带动了古玩商们来琉璃厂开店经营。
无论金石、陶瓷、书画、碑帖、古钱币,还是涉及风雅文化的其他行业,均在此情形下发展起来。
琉璃厂的名气也就这样打响了。
琉璃厂真正成势,繁荣兴盛以来,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三百多年的世事变迁了。
那么这条街上自然有许多知名老号。
像荣宝斋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家。
荣宝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斋南纸店。
原本只是一家单纯经营各类纸张以及文房四宝的店铺。
但这里的木版刻印技艺和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非常有名。
乾隆年间,内廷官文用纸、朝廷的考试用纸都是专门由松竹斋提供的。
光绪二十年,由业内高人庄虎臣出任店铺经理。
他为债务缠身,经营陷入困境的松竹斋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就有把店铺更名为荣宝斋,并扩充多种业务的决定。
于是从此,荣宝斋不再局限于做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买卖,还涉足到了买卖书画,以及代客订购书画业务。
在经营上,荣宝斋更秉承“以文会友”的宗旨,着重于与书画名家们保持翰墨情缘。
从而逐渐成为了书画家甚为信赖的朋友,甚至被视为“书画家之家”。
正是因此,清末民初时,琉璃厂各家老店为招揽顾客,纷纷争悬名家书画于窗前,引人驻足观赏的宣传活动中。
其中尤以荣宝斋名画最多,最为热闹,成为琉璃厂的一道风景。
到了民国时期呢,两位著名文人大家,又委托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更是让荣宝斋声名远播。
建国之后,荣宝斋经营权逐步由私变公,归属美术出版社领导。
随后又合并了画界知名的和平画店,风头一时无两。
直至此时,荣宝斋已经发展成为在琉璃厂店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
业务内容涵盖出版、印刷、修复、装裱到书画购销的综合性营业部。
并以其精湛的传统技艺和诚信经营方式,深受国内外顾客的信赖与青睐。
在这条街上,与之同样具有古代书画购销权的店铺,仅有文物局直属单位宝古斋一家。
可尽管表面上看,康术德和宁卫民来琉璃厂卖画,就是奔着荣宝斋的名号来的。
不过卖也没那么简单,可不能直来直去。
和抓货时一样,同样不能图省事。
否则这价格高低,就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去,真弄不好把好东西卖出个贱价。
康术德可是这行里的尖子,不但懂行,还有心计。
他要撒手什么物件,首先必定得提前摸底,做到心中有数才是。
像在真正奔琉璃厂之前,隆福寺商场的旧货门市部,西单的旧货收购点,护国寺大街路西的悦雅堂门市部。
老爷子不怕麻烦,和宁卫民带着字画都分头跑了一趟。
哪怕到了休息日这天,他带着东西和宁卫都来到了琉璃厂,真的该当出手了,也没着急。
还是先去了宝古斋询了个价,才开始实质行动。
说真的,老爷子原先其实还打算王府井的京城画店去问问的。
可走到门口,他突然想起来了。
那家画店和荣宝斋一个东家,都隶属于美术出版社。
他怕一去露了风声,这才没进去。
什么叫腿勤、口勤啊?
得至少做到这份上才行哪。
其次,到了地儿还不能直接卖画的事儿,因为上赶着不是买卖。
荣宝斋盛名在外,又是国家单位了。
在加上这年头各行各业服务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存在着某种通病。
这样的交易中,私人太容易处于被动了。
所以康术德得想办法让店方开口求他,才好要到理想的价码儿哪。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好办。
大可以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啊。
差几分钟十一点的时候,康术德终于带着宁卫民来到了荣宝斋。
说实话,这年头的荣宝斋,其实有点让宁卫民意外。
因为它的店面居然是一个水泥石墙简洁外观的一溜平房。
看着有点像苏式建筑,并无多少复古风格。
但门户大,挂着牌匾,外有游廊。
也确实是比这条街上其他门市部都要气派正规一些。
进去之后,完全是传统商店模式。
就是绕墙一周的玻璃柜台。
玻璃柜台里摆着毛笔、印泥、墨、砚,等精致小件。
后面的博古架上则是各类纸张、笔架、墨盒、摆件儿、扇面,等一派古色古香的大件儿。
只是对店里的格局,和这些销售的东西。
宁卫民一时也来不及细看,他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了师父的身上。
因为他可知道,进了荣宝斋的大门,这表演才刚刚开始呢。
“我说同志,你们这儿是不是能修复书画啊?我想问问……”
“往里走……”
嘿,根本就没容康术德彻底把话说完呢。
卖毛笔的柜台后头,一个精瘦,没有表情男售货员就打断了他的话。
漫不经心拿手往里一指,就不言语了。
根本就不抬眼看人,好像谁欠了他八百吊似的。
不过也没法挑剔,反倒还得谢谢一声。
因为实际上,哪儿哪儿都这样,他们去别家也一样的待遇。
要为这个生气可不值得,那就别出门儿了。
更何况,康术德和宁卫民那略显寒酸的衣装多少也起了让人鄙夷的作用。
要是他们能穿好点,像个外宾似的,再包个小车儿来,兴许就不是这样了。
《国潮1980》正文 第五十四章 穷卖
往里走就往里走。
康术德和宁卫民按照售货员指出的方向往右一拐,发现里面更大。
依次是装裱室、修复室、木板水印,印刷出版、画廊等一溜儿不同经营品类房间。
还有挂着“书画家之家”牌匾的接待室呢。
但宁卫民和刚才待在最外面那一间营业厅时一样。
根本来不及多瞅几眼,就跟着康术德进屋去找修复师了。
还真得说,这屋里的几位老师傅,态度要比外面好得多了。
一见他们进屋,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暂时放下了手里的事儿,主动过来询问来意。
这大约年长与年幼的不同,或者压根就是搞专业的技术人才和普通人的区别。
反正素质上的差距不小。
康术德更没什么可扭捏的,见这位挺热情,赶紧就让宁卫民痛快把东西放下,把书画展开来。
什么是行家里手啊?
老师傅一看,表现出的态度,也和康术德当初看到这两幅字画差不多。
叹息不已。
“老先生,您这两幅字画儿啊,真是不错,可惜保管不善,全都朽了。”
“您看这幅石涛,含藏葆光,但这都有伤了。这一幅沈周,也有点朽了,后面更是起霜了。”
“幸亏您来我们这儿了,要再耽搁几年,这两样东西恐怕就毁了。”
康术德也是唉声叹气,一副痛心疾首的后悔样子。
“是是,要不我干嘛来的呢。好几百年的东西了,又是名家之作,您可千万别让他毁我手里。我谢谢您了。”
“不会不会。您也别太过虑了。”
老师傅一听,赶紧出言宽慰。
“我们店的修复技术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绢本、纸本都能做,工艺流程完备。抢救过无数破损严重、濒临失传的艺术珍品。比这损害更严重的,都能做到修旧如旧。”
“像前些年,一副郑板桥的墨竹,送过来时都快成碎渣儿了,我们历时八个月,也给补全了。”
“您这活儿呀,我得说算是送来及时。现在抢救,问题不大,最多三两个月就能弄好。您只要把东西交给我们,就放心好了。”
康术德赶紧点头,“这没错,百年老店嘛,名声在外,有口皆碑。这时间我等得起,精工出细活的道理我懂。只是这价钱……”
老师傅听出了康术德最后一句的潜台词,这在他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毕竟康术德和宁卫民的衣着旧得没了样儿,瞅着都洗得发白了,一看就是生活不富裕。
他反倒是觉得,这种情况下还能惦记着修补字画的人,颇为不容易。
于是应了一句。
“这个嘛,您放心,我们诚信经营,多收不了您的。我给您好好算一算啊。”
他就本着敬业的态度,对照着展开的两幅字画,拿着纸笔开始一丝不苟的统计和计算。
那是从大到小,一处一处的说,一笔一笔的加,一项一项的估算。
足足忙和了得有七八分钟,最后得出了数字,才拿过单子来给康术德过目。
“老先生,您看,这幅字儿,我们得冲洗、揭旧,然后重新装裱才行。这画儿呢,也得托补、全色。这要合在一起啊,这就是最后的价钱了。书卷得一百二十二元。这画卷得七十六元……”
说实话,这近似于二百元的价钱,真没多大水分。
但即便是这样,康术德仍然是跟挨了一刀似的,立马就叫起疼来了。
“哎哟,怎么这么贵啊!您就不能便宜点吗?”
老师傅一嘬牙花子,这下真有点为难了。
可皱了皱眉,看了一眼康术德那衣角上的毛边,人造革提包用胶布缠的提手,还是让了一步。
“这……您要是嫌贵,我再给您个折扣,就算一百八了。您看行不行?”
但这仍不足以让康术德满意。
因为他要的就不是这个啊。
“那也贵啊!这都合我小半年的工资了!咱能不能……一百块?”
“哎哟!这价儿可没这么划的呀……”
老师傅情不自禁面露苦笑,忍不住诉上了委屈。
“老先生,我们这不但是国营商店,还是百年字号,明码标价的事儿,不可能懵您。”
“尤其是修复和装裱业务,我们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抢救书画为重。价格本来定的就不高,基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
“我是体谅您大老远来的不容易,也替您可惜这两幅书画,才按照老顾客的待遇给您打了九折。您要再不满意价格,真恕我无能为力了。”
“再说了,老先生,刚才我不都跟您说清楚了嘛,这修复是个占人工耗时间的精细活计。”
“别的不说,就光这揭旧一道工序。我们每天都得用指肚,跟搓泥儿似的一点点揭,没个二十天弄不完呀。这还算最容易的哪。”
“干您这活儿,我们得占三个人,一个师傅带着俩徒弟最少忙和俩月。您还嫌贵?哎,让我说什么好呢……”
这话里说的不但真诚,还包含着一些从业人员不被理解的辛酸啊。
连刻意难为的康术德,都有点被老师傅感动了。
可问题是,他的心中早有成算,本来就是故意把事儿往崩了谈的。
他要不把人逼到没招儿,也不好进行下一步啊。
所以为了不功亏一篑,他也只能硬起心肠,把这套迷魂掌打完了算。
“您说的都对。我没说您的价钱不公道不是?可问题是我……我这手里……”
“我也实话跟您说啊,来之前就凑了一百,是真没想到,为这两件东西要用这么多钱。”
“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这价格就这样了,我认可。可钱我真没法一下都给您。先给一百。其他的,咱只能日后再付清。”
嘿,好嘛。
这价儿,康术德倒是答应了,可他提出附加条件却又是老师傅绝无法应承的。
那老师傅还能怎么办啊?
对这样的要求,他根本无权做主,苦笑着擦了擦冒汗的脑门和眼镜。
也就只剩下最后一招,去请示上级领导了。
其实老师傅哪儿里知道啊,刚才的讨价还价全是虚晃一枪。
偏偏这样的结果,才恰恰是康术德真正想要的。
怎么呢?
因为荣宝斋的领导不但权力大,见识广,有文化,脑子也比普通职工活泛啊。
康术德算准了,这事儿这么通报过去,只会有两种可能。
要么人家看不上这两件儿东西,打发他们走人。
要么……那恐怕就是领导提出收购建议,期望能变相解决,主动往他摆好的套儿里钻啦。
就在老师傅请康术德在此稍等,自去请人的档口。
宁卫民也低下头自己个儿偷笑起来。
并且带着佩服,在心里给师父点了个赞。
因为康术德的用意,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