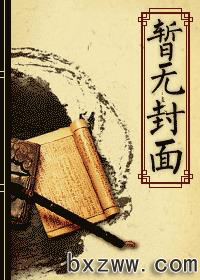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月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哥哥醒了。
是什么时候醒的,他完全不知道。身体里灼烧的痛苦无法纾解,他喘息着,抓着自己的领子想找个解脱。没有办法。这灼烧是在骨子里的,他没有办法。他难受得扬起头来想哭,却看到哥哥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眼睛,正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他害怕得窒住了。
“毛毛?”哥哥的眼睛灼热得怕人。
“我难受,”他语无伦次地想逃避,“哥哥,我难受。”
“没事的,毛毛,”哥哥抱住他,把他的脸按在肩头,“哥哥知道。”
哥哥不生硬了,也没有不耐烦,只是抱着他在他耳边喁喁地说了许多话,说得他的脸红了又红,往哥哥怀里缩了又缩。
“别害羞,毛毛,”哥哥哄着他,“你是长大了。没人告诉过你吗?”
他赧然地垂下眼睛,享受着被哥哥抱住的温存,手指玩弄着哥哥领口的扣子。
“再过几年,毛毛成家了,就明白了。”哥哥的喉结动了动。
“我不要。”他抗议道。
“嘘——”哥哥轻轻地,“你是害羞,怎么会不要呢?”
“我不要,”他很急切,就像他不要分家那样,“我要和哥哥在一起。”
“哥哥也不能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能的,”他坚持,“我要和哥哥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你活一日,我活一日,你死了,我也去死。”
哥哥放开了他,退开了些许,看着他。他握住哥哥的手,哥哥的手竟然在轻轻颤抖。
“毛毛,别胡闹,”哥哥想要松开手,“你以后要成家,要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算哥哥死了,你也得好好生活。”
“我不要,”他又着急了,“要成家,我也只和你——”
“胡说。”哥哥在他腮边打了一下,打完了又急急地凑上来看。
被打的地方有些火烧火燎的,他的牙齿也磕到了嘴唇上。可他只顾着看哥哥。月光下,他看清了。哥哥是着急的,是心疼的,是痛悔的。哥哥越着急,越心疼,越痛悔,他越高兴。
“哥哥,我只和你在一起,”他痴痴地看着哥哥在月光下英俊得不真实的脸,“你说过你不会不要我的。”
“我是你的哥哥。我只能是你的哥哥。毛毛,你不懂吗?我们是兄弟。”
“不是的,”他懂得了哥哥的意思,奋力地辩白,“不是。”
他翻身爬起来,扑在哥哥身上,拉开哥哥的衣领。
锁骨上的刀伤,依然留在那里。
那天又不是做梦,哥哥是知道的,他是忘了吗?
“我们就是兄弟,”哥哥猛地抱紧了他,不让他乱动,“家谱上还写着我们俩的名字,我们就是兄弟。毛毛,裘潋!”
哥哥几乎从来不叫他的大名,家里人都很少会叫他的大名。他被这一声震得怔了一怔。
“我不姓裘,”他很快又哭闹起来,“我根本不姓裘。”
一两个月间,他的病时好时坏,一直没能治愈,连考试的时候都是带着病,考完之后就又倒下了。
家里只有哥哥和嬷嬷,看了多少医生,吃了多少药,还是那样。嬷嬷甚至提议找算命先生来看一看。
“万一是撞了什么邪祟呢?或者流年不利?哥儿,你找的这屋子的风水怎么样?房东有没有同你说清楚?”
哥哥沉沉地叹气:“医生说了,叫他好好吃药,也要心情畅快,否则郁结在内,也有妨碍。”
“我看小哥哥儿就是小时候亏着了,家里也不经心。小辫儿也不给留,百家饭也没吃过,百家衣也没穿过,连把长命锁也没戴过。”
“嬷嬷,你这都是迷信。我也一样没戴过。”
“你怎么没戴过?你那时候小,不记得了。你有三四块长命锁呢,有别人送的,也有太太买的。学走路的时候就爬高上低,你嫌那锁又大又重的,挂在脖子上不痛快,就自己丢了。太太当年收在哪个箱子里了,你没再见着罢了。”
隔着门,外面静了静。
哥哥又道:“嬷嬷,你只看住他,每天的药都按帖喝了,一帖也不能少。”
“他不肯喝,我还能强灌他吗?”
“灌也得灌下去。”哥哥生硬地道。
他躺在床上听见,不争气地流泪。
嬷嬷端着药碗来,再怎么好劝歹劝,他就是抿着嘴不喝。
“小哥哥儿,”嬷嬷在他背上拍一把,“你这是寻死吗?”
他赌气闭着眼不答,眼泪却止也止不住。
寻死。他气鼓鼓地想。就是寻死。
国立艺术学院揭榜时正是暮春。他还在卧床,出不了门,是才来帮忙的女工芳音去看的榜。
“没瞧见小少爷的名字。”
芳音在外面低低地同嬷嬷说。
“看真了吗?没看漏了吧?”
“我前前后后看了好些遍呢。小少爷这个名姓都不常见,不会看漏的。”
“唉,”嬷嬷叹息了一声,“为这一场考试,病得这样,反倒考不取了。”
下午时分,哥哥就回来了,进门就问:“毛毛考上了吗?”
外面没说话,大概是做了手势。
“我去看看。”哥哥说着,又出去了。
“你还看什么?”嬷嬷追出去,“我让芳音去看了两回,看真了的。”
太阳渐渐地西沉,玫瑰色的晚照从窗户落了进来,他睁开眼睛,抱着枕头,有些闷闷的。
那绚丽的玫瑰色也渐渐地淡去了。
靴子的声音响起来,是哥哥的脚步声。
“哥儿,回来了?”
“啪。”
房门被推开了。
他赶紧闭上眼睛,就听哥哥的声音:“毛毛,你改名字了?”
他全身僵硬,梗着脖子不回答。
“为什么不告诉我?”哥哥上来扳他的肩膀。
他只是拗着。
“哥儿,怎么回事?你不要扭着他了。”
“毛毛考上了。”哥哥说。
“哎呀。”嬷嬷喜不自胜。
“我真的看了好些遍……”芳音内疚地说了一句。
“不怪你,”哥哥道,“是他把名字改了。”
“改名字?这个时候改什么名字?还不够添乱的!芳音,快出门看看,外面铺子还有卖什么的没有,拣小哥哥儿爱吃的买。”
“哎。”芳音答应着。
两个人都出去了,只有哥哥还在他床边站着。
“温潋秋,”哥哥的声音沉沉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温潋秋。
这个名字写在榜单第一个。
温是他母亲温氏的温,潋是他名义上的父亲裘仕昌取的潋,秋是他和哥哥出生的季节。
“为什么不告诉哥哥?你让嬷嬷悬心了一天。别赌气了,喝了药快起来,嬷嬷还要给你庆祝。”
嬷嬷果然很快端了药碗进来,殷勤地问:“小哥哥儿,你想吃什么不想?快喝了药,嬷嬷给你做去。”
“不。”他用力摇了摇头。
“哎呀我的小哥哥儿,这么大的喜事,你还闹什么?快,把药喝了。”
“不。”他仿佛想甩掉噩梦一样又用力摇了摇头。
“那怎么行?”嬷嬷拉起他的手,耐心地哄着他,“药怎么能不吃?小哥哥儿,你是懂事的。”
“我不吃!”他猛地一挥手。
药汤泼在他手上,“嚯啷”一声,药碗也砸碎了。
“小哥哥儿!乱挣什么?烫着了?”
眼泪又从他眼睛里涌了出来。
嬷嬷擦着他手上的药汁,轻轻地替他吹着烫热了的皮肤,用力拽着他的手。
“小哥哥儿,你坐好。生了病得吃药,吃药才能好。”
“我不要,”他近乎嚎啕地大哭起来,声音都变了调,“嬷嬷你放手,我不想好。让我死了干净——”
他几乎立刻被人拎着坐了起来。
“哥儿,你做什么?”嬷嬷着了急。
“你说什么?”哥哥的声音冰冷。
他闭着眼睛,咬着牙关。
“你说什么?”哥哥离他又近了一些。
他摸索地抬起手,想推开他。
哥哥冷笑了一声。
“哥儿,你别揪着他,你的手里不知道轻重。”嬷嬷在旁求情。
“嬷嬷,还有药吗?”哥哥不为所动。
嬷嬷迟疑了一下:“有,我再去热。”
哥哥俯身靠近了他,把枕头在他身后叠了起来,扶着他倚了上去。
他睁开眼睛,正和哥哥的目光相对,心里一颤,又合上双目。
床沿轻微窸窣,是哥哥在他身边坐下,就这么静静地和他僵持着,直到嬷嬷又端了一碗药进来。
“小哥哥儿,”她仍是好言好语地哄,“我们吃一口药,吃一口蜜。”
他不理不睬。
“药得趁热喝,冷了就不好了。我们小哥哥儿又不傻,怎么能做伤自己身子的事情?”嬷嬷絮絮地说着。
他一动不动。
“嬷嬷,你出去吧,不要管他。”哥哥生硬地道。
“哥儿……”嬷嬷欲言又止。
“你出去吧。”哥哥又重复了一遍。
门轻轻地关上了。
哥哥的呼吸在他耳边,汤匙碰着药碗的轻微声响让他坚决地抿住了嘴唇,然而他紧接着却听到药碗搁在床头柜的声音。
突然,一股大力把他按住,有灼热的温度贴近了他。他刚要挣扎,却忽然意识到,那是哥哥的嘴唇。
在他很小的时候,让他吃药是很费事的。无论吃了多少药,他都无法习惯,经常大哭着打翻药碗。为了让他乖乖吃药,家里人想了无数的办法,这无数的办法中也包括他的哥哥。
哥哥会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这药并不苦。”
“苦!”他大哭着,抗议这拙劣的谎言。
“你瞧。”哥哥说着,自己喝了一口,很轻松地向他扮了个鬼脸。
这让他迟疑起来,低头看看那药汤的颜色,再次大哭出声:“苦!”
“怎么?哥哥喝的味道和你不一样?”哥哥笑着,又喝了一口药。
这一回哥哥没有咽下去,而是凑近来,嘴对嘴地喂给了他。
“你看,不苦吧?”哥哥向他求证。
他呆了一呆。
他的味觉告诉他这就是个拙劣的谎言,可他竟然动摇起来。
“是不是?”哥哥一面对着他笑,一面又端起了药碗。
药汤是微烫的,温潋秋在猝不及防间几乎只剩下吞咽的本能。
两人的嘴唇分开时,他喘息着睁开眼睛,看见裘灏端起药碗又抿了一口,回过头来看着他。他觉得裘灏的眼睛在逐渐暗淡的夕照中闪动了一下。他们的距离又在慢慢靠近。裘灏的手按在他胸口,这次没有很用力。
唇齿相接的时候,温潋秋发觉自己早已放弃了防御姿态,裘灏轻而易举地把药汤喂了进来。
药碗逐渐见了底,裘灏沉默地看着他,再次吻了上来。
这真的像是一个吻,裘灏的双手拢在他身体两侧,在喂完药汤后还短暂地停了片刻。
温潋秋不禁又闭上眼睛,却感觉裘灏的手臂抵着床褥微微用力。他唇上一空,听见裘灏已站起身来,拉开床头的台灯,收拾了药碗,离开了房间。
床头的台灯坠儿在墙上映出摇晃的影子,温潋秋渐渐地醒过神来,发觉自己的身体竟紧张得在被褥下蜷了起来。
他慢慢地侧身从枕头上滑了下去,隔着被子抱住自己的膝盖。
门忽然又打开了,他戒备地从床上弹了起来,看见裘灏又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什么。
离近了,他才看清,那是一个月白绸缎喜鹊登科花样的荷包,虽然素净,却仍看得出做工精巧。裘灏拉开荷包,从里面抽出一条纤细的银链,那银链底端穿着一把小巧的银锁。
“长命锁。”裘灏言简意赅地道。
接着,他将这把长命锁往温潋秋颈后一扣,沿着银链轻轻抚摸,在温潋秋锁骨下方微微用力,按住那把锁。
他什么也没再说,但是温潋秋却瞬间明白了,眼泪直往上涌。
哥哥这是要锁住他的命。
还要锁得长长久久。
※※※※※※※※※※※※※※※※※※※※
作者:葛格,既然提到“锁”,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鬼畜文里的年上会用大链子把人锁起来酱酱酿酿啊?
葛格:呵。他们都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作者:葛格,你有没有听说过有首歌叫《法海你不懂爱》?那个法海总是说,我们不能在一起←_←
葛格:……闭嘴!他是我的底迪!我知道怎么做对他最好! 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