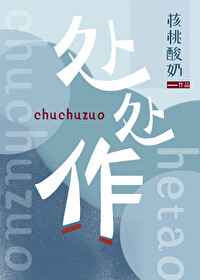段榆呆了一秒,随即火气上涌,一巴掌拍在他脸上。
“你有病?!”
谢桥看着他脸上的牙印,和泛着亮光的自己的口水,心中郁结顿时消散。
“对!我有病!”谢桥大声承认,“我不仅会咬你,还要睡你的床,逼你吃我做的饭菜!”
“知道我送的礼物什么含义还要给别人,给就给了,别让我知道,不然我一定问他们要回来,告诉他们我在追你。”
“你觉得我坏,我就当坏人。”他一副无赖的样子,“你想怎么骂就骂好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心了,不会再被你伤害!”
段榆抽了张纸用力擦脸,但是脸上湿热的感觉残留不走,闻言,他冷笑一声,脱口而出的话不受控制。
“你这副深情的样子装给谁看?在一起的时候,你给过我什么掺杂真心的东西吗?那时候没有,现在更没必要。你是成年人,别玩小孩子撒娇要糖吃的那一套。”
段榆胸膛起伏,指尖冰凉,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向心脏,以供它能剧烈地跳动。
他吝于说这样的话,觉得这样的想法自私,斤斤计较,没有风度,像是向别人乞讨怜爱。
他不需要怜爱,如果谢桥给不了,他不会勉强,静静离开。
但谢桥总在逼他,一步步踩进他的底线。
谢桥怔了一下,终于知道段榆的心结在哪了。
“你……你追我的那一个月,不是我想玩你,也不是耍你。我很久、很久以前喜欢上你,很久、很久之后才发现,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也刚好喜欢我。”
太幸运了,让人不敢置信,要不断、不断地去确定,证明他的喜欢是真实的,不是大梦一场就能抹消痕迹的存在。
“这种好事,像在做梦。”
段榆扯了下唇角,“做了一个月的梦?”
谢桥沉默一会,小声说:“三个月。”
段榆:“……”
“我送你的礼物,你都不喜欢?”谢桥又问,
段榆反问:“你说的是骷髅头手链,还是绿帽子?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样?”
“我觉得挺好玩的,”谢桥声音更小了,大约这段时间他真的成长了很多,终于意识到那些东西有多不讨人喜欢了,心虚地说,“你很少笑,我只是想逗你高兴,没用对方法。”
段榆一愣,缓缓捏紧手里的纸团,指甲抵在掌心,带来几丝疼痛。
他抿唇,拿起桌上的剧本,朝卧室走去。
“砰”的一声关上门前,他说:“滚。”
酒店房间隔音做得很好,段榆听不见外间有什么响动,也不知道谢桥走了没有。他坐在床边,怎么也无法把注意力转回到剧本上。
谢桥真是会烦人。
不愿意浪费时间,与其干瞪着剧本,不如早点休息,养好精神明天早起,段榆带着这样的想法关了灯,钻进被窝里。
他久违地做了一个梦。
梦里场景和现实没有差别。
环境宜人的郊外,空气清新,天气很好,长长的阶梯延伸至山头,引他到父母墓前。
他又坐在墓前的小台阶上,蓝天白云,没有旁人打扰,一个人静静地坠入回忆里。
母亲是没有经历苦痛去世的。
人到一定年纪身体机能就会下降,年前老人家跌了一跤,没有伤筋动骨,但明显体质大不如前,经常会有各种小毛病造访。
似乎真正的衰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步一步,无法挽留,直到最后死亡吞噬了她。
没有病痛,也没有“罪魁祸首”,没有任何可以埋怨或憎恨的对象,但似乎就是这样,才更让人无法接受。
老人家离开前的最后几天若有所感,把要交待的事都交待了,最后看向他,只剩一声无奈的感叹。
“你这小人怎么成天不见笑……”
她普通话说得不好,经常和方言掺杂着,小人就是小孩儿的意思。对她来说,段榆永远都是小孩子。
段榆那时候还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难以自渡,无法感受到母亲临行前对自己的担忧,反而觉得她也不懂自己,很偏执地说:“人生在世,有很多不如意,我找不到值得高兴的事。”
母亲说:“那就找愿意逗你开心的人。你和你爸一样笨,人生短暂,笑笑就过去啦。”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想起来总是后悔,责怪自己,没能给出一个让母亲安心的回答。
到时间了,梦里的段榆起身,凝望着两座挨在一起的墓碑。
接下来的情节却突然和现实脱节了。
现实里,他会像往常一样告别,轻轻说句“我走了”,结束这段难得的独处的时光。
但这次在梦里,他看着父母,张口问道:“是他吗?”
段榆猛地醒了过来。
疯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