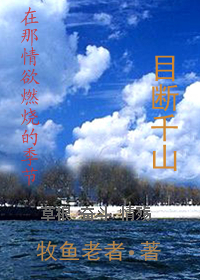[第1章引子]
第9节第9章父母离奇的往事
枯黄的草地,柔软而富有弹性,几只大黑蚂蚁在草叶上慢吞吞地爬来爬去。一只小蚂蚱在一片枯叶上弹了弹腿,一下就蹦到了白明的脸上,他伸手把它捉住,捏住它的两条腿把玩。
老王看看他,说起他父母的经历来。给读者讲过的,这里就不再重复。
那年秋天,白仲文带着妻子回到白家庄,大吃一惊:有人告诉他,已有好几个人饿死了。独居的老父亲瞪着眼睛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不久前还写信说自己在乡下过得很好,要他不要挂念!白仲文跪在父亲的床前,失声痛哭。老父亲见儿子回来了,指指自己的心窝,挣扎着对儿媳妇笑了一下,头一扭,去了。
白仲文抱着父亲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装殓时,发现父亲的胸口掖着一张纸。原来,老父亲听说儿子要被精简回乡,就舍不得吃秘藏的两麻袋稻谷,宁可自己饿死也要给儿子留下来。冥冥中,仿佛算定儿子在他临死前一定会回来似的。交代完后事,又附上一行大字:积谷防饥。切记!切记!切记!
白仲文又痛哭了一场。
帮忙抬棺的人饿得连棺木都抬不起。虽然有途中不能停棺的忌讳,但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不知在路上歇息了多少次,才抬到山上。
出于对乡亲们的感激,也出于同情,也许还因独占偌大的一笔粮食而内心受责,白仲文偷偷取出一部分谷子,用石磨磨成粉,掺上许多能吃的野草树叶,用队里办公共食堂时留下的大锅,煮了满满两大锅,帮过忙的没帮过忙的都请来吃。
据说许多年后,村里人还在念叨那顿饭好香好吃,还在感激白仲文夫妇的好。以至于后来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次被遣送回庄里接受劳动改造,也没真正受过多大的苦。这是后话。
白明的母亲儿时在战时孤儿院混过几年的,那时的孤儿院条件不好,有一顿没一顿,挨饿是常事,跟教养员学到过很多的求生本领,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下可派上用场了。
由于大旱,地里种的作物颗粒无收,小溪也快见底。起初,家家户户都去溪里抓鱼回来煮汤喝,权当改善生活。据说那鱼,太多,闭眼伸手就能抓到一条,大家都只抓大的。但没有油水,没有调料,顿顿吃鱼喝汤,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闻到鱼腥就直想呕。等白仲文回庄时,虽然小鱼满溪,却再也无人和他相争了。
由于对未来充满恐慌,人性的弱点在这时都暴露无遗。自私,贪婪,无情,偷盗,抢劫,弱肉强食,且不说这些——竟然真的发生了到死尸上割肉的事。
白仲文夫妇团结族老制止了这种野蛮的行径,天天带领大家到远近的山上去找吃的。那时,庄里没有活干——旱了大半年,干了也白干,况且,老是吃不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还能干活?偶尔,上边也派点救济粮下来,但杯水车薪。白仲文夫妇是秋收后才回庄的,没有工分,有人反对给他们分粮,夫妇俩卖力帮忙运了几次粮一无所获,也就不再指望。在妻子委屈地痛哭了几场后,白仲文明白,眼下最重要的,首先是要保证两个人都好好地活下去。何况,这大饥荒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白仲文于是谨记老父的遗训,轻易不去动用老父亲付出生命代价留给他们的那点谷子。白天常常整天呆在山上找食,累了困了夫妻俩就相拥着睡一会儿,冻醒了赶快爬起来继续。能存的,就带回家里,做成干货,藏起来。
常常,夜里饿得慌了,就跑到野外去逮山鼠,剥掉皮,去除内脏,抹上点盐,再去溪里抓几条鱼,烧起篝火慢慢烤着吃。吃完了,就默默地数星星,望着空寂的旷野发呆。偶尔能逮到野兔野鸡,就是无上的美味。烤熟后只吃一部分,余下的带回家里藏好,等到有时机会不好,在外一无所获,也不想吃鱼,饿得实在扛不住了,再取出来分吃几口。
好不容易熬到春天,白仲文照例去公社做每月一次的思想改造汇报,惜才的书记向他宣布一纸决定:为了更好地挽救和改造白仲文,调白仲文到学校任教。
要知道,那时候只要能拥有一份公职,就意味着活下去有了保障!
白仲文夫妇每月有了二十八斤米面,加上以前节存的干货作底,生存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思儿的痛苦煎熬却随即缠上了他们。由于白仲文是被改造的对象,妻子是右派家属,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思儿还切也只能苦受。
据说有一天,白明的母亲终于忍受不住了,带了一只包袱,天刚抹黑便溜出白家庄上城去见爱儿,半夜时竟赶到了家门口。趴在墙头好不容易等到儿子饿醒哭闹,老父亲亮灯起来寻吃的,才瞧上儿子。看到儿子白胖可爱的模样,知道老父将其照料得很好,也就放了心,把包袱往门口一扔,跳下墙便跑。
连夜往回赶,到达白家庄时天刚微亮。
一早,负责在路口巡夜的民兵就赶去报告公社说,怀疑白仲文的妻子夜里上城了,只是未看真切。负责治安的民兵紧急带人上白家庄去查,却发现人家好好地坐在堂上。原来,先天晚上她飞身经过路口时,被民兵发现了,民兵回神去追赶时哪还追得上!
有一个人神秘地通过路口上城,且查不出到底是谁,这还了得!公社书记便亲自过问此案。那个最先看到黑影的民兵知道自己负责不起,就一口咬定,自己看见的就是白仲文的妻子。等到书记亲自上门盘问,她却镇定自若,不露半点破绽。她淡淡地反问书记:“这白家庄距城里有多远?”书记一愣,对呀,最近也是八十公里,往返就是三百二十里,而且村里人都证实,人家天黑时还在家里。满打满算不超过十个小时,夜里又没车经过,难道飞过去吗?转念一想,这白家庄的人世代习武,也不无可能,便打电话到城里派出所,请民警去查问。
能查到什么线索,那岂不是笑话?老爷子是何等人物!夜里听到响声,开门见到包袱就知道女儿回来过,连夜做了处置,所以民警去查问必然是白忙一场。
那个民兵还要争辩,书记眼一瞪,命令他:跑到城里打个转,限四十八小时!
结果那家伙一个星期也没能跑回来。
这件事在当地被当作笑话传了许多年,而到底白明母亲上没上过城,到底十小时之内是如何跑完三百二十里路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现在看来,只能如此解释:思儿心切,老爷子打造的武功底子,加上人的潜能。
这件事平息之后,为免惹祸上身,更怕连累老父和儿子,加上以后的种种变故,夫妻俩便再也未上过城。
“四清”运动达到高潮的那一年,白仲文一个在信用社工作的好友出于江湖义气,借给一位朋友几千块公款去填补其挥霍的窟窿,结果朋友还是过不了关,竟投水自杀了。等清查到自己头上,巨额亏空百口莫辩,加上受不了折磨,那个好友竟然走了同一条路。好友的妻子是贞烈女子,受不了歧视和屈辱,有天夜里把四岁的女儿送到白仲文那里,回去后竟撞墙而死!
这女孩小白明几个月,当年两对夫妇聚首时正各怀身孕,便击掌约定:是龙凤便结为亲家。这样,白仲文便收养了这孩子,改名白梅。为了悉心照顾这个孤儿,夫妻俩决定不再要孩子。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白仲文由于这几年各方面表现得实在太好,在他身上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加上他模仿领袖的字体说得上“神似”,就被造反派征召去专写“语录”。没想到这竟惹来一场大祸。
为了写得更好,白仲文找来一些旧报纸练习。有天没注意在一文革领袖的肖像背面写下这么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且墨汁浸透弄脏了肖像。这还了得,一级级地报告上去,上边命令彻查老底,白仲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据说本来是要判重刑的,白家有一族人在县革委会里担任要职,不知怎么一活动,白仲文便被从轻发落,交给原籍白家庄监督劳动改造。
一晃十二年,听说开始落实政策,夫妻俩就上访去了,大半年不见回来......
白明听得入了神,一只寻食的长尾鸟跳上他的鞋尖,扇扇翅膀,伸腿在他鞋上拉了一泡粪,他也没发觉。那只鸟低头在他鞋上磨了磨长喙,又去啄他的鞋带,叼起一拉,掉了,再叼起,老王扬了一下手,它便“吱呀”一声展翅飞到对面的树尖上去了。
老王继续说:“见到你父亲,请转告他,当年办案时没收他的那几本日记,我替他处理掉了,请他谅解。”又转向白明,解释说:“日记里有些内容对他很不利,我就自作主张偷偷把它们毁掉了。”
说完,老王如释重负似的,拍拍白明的肩膀,站起来,大声说:“走啰,不早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