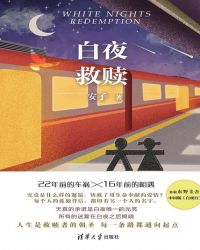时间就这样晃晃悠悠地碾过去了,西皇庄的房租我已交过三次,在这九个月里,我和雷海生发展的应该说很顺利,雷海生对我还是很好的。而骨子里,我是渴望被人爱的,或者说,我是渴望获得他的爱的。
这九个月里,我告诉过自己无数次:一日夫妻百日恩;也下了无数次决心: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我在第一个月的某个周末,和他一起添置了木头案板和汤锅,用来取代我原来使用的那个简陋的塑料案板,用来一起体验“有家的感觉从锅开始”。我在第二个月的某个周末,和他一起添置了新窗帘,两个人一起动手将西皇庄破旧简陋的房子装饰一新。我在第三个月的某个周末,如他所愿,给自己买了一件像样的内衣,从内心里,我还是希望取悦于他的。
然而事实上,生活远不像小说情节那么简单,就算是正式恋爱了九个多月,我也还是很难真的从心底里愿意和他白首不相离,我甚至很难相信,他是真的爱我。
这种感受,说与任何人,可能都难以理解,所有人都觉得他对我很好。如果没有足够的爱,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你,陪你买菜,给你做饭呢?可我心里,就是感觉不到,如果非要说我感觉到了,那么也是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雷海生是爱我的,而不是内心自发的感受。
雷海生想要的生活,就是“饮食男女”。
他爱做的事情,只有两样,那就是“饮食”和“男女”。
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做丰盛的饭菜,这让我觉得很温暖。
没错,这九个月里,我们一起吃的每一道菜,几乎都是他做的,而我做过的菜,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我不擅长厨艺,总觉得时间太珍贵,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工作、写作,用来去争取更好的未来。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唠叨,让我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不愿意在他面前做饭,不愿意为他做饭,或者说不愿意在他面前,做除了学习、工作之外的任何事情。
而每次吃饱喝足之后,必然就是“男女”,是让我头疼不已的“男女”。
难道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从不关心女人的感受?
好吧,实话实说,这九个月来,雷海生要求了N次,被我拒绝了N次,于是我被强迫N次。为这件事,我打过雷海生的耳光;我甚至整整一周不理睬他,不与他说一句话;我还在某个被强迫的周日,用枕头捶打了他很久很久……
雷海生每次都对我说:“活着,如果不能开心的吃饭、睡觉,还有什么乐趣。人类的动物属性最简单、最直接,也最真实,亲就是亲,爱就是爱,就是在一起,舒服得要死。”
然而对于我来说,并非如此。如果非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还是那个不堪入目的词:奸尸。
我和雷海生之间,总是隔着什么,就像他不理解我对于“爱”的拒绝一样,我也不理解他对生活的无谓和唠叨。
他是个太过无谓的人,对自己的事情,似乎万事都无所谓,当然,除了我,除了“爱”。
虽然他看起来很细致,但事实上却是一个非常非常粗心大意的人。
他每次来,进门后都不记得随手关门;他每次做饭,都会把厨房弄成一片狼藉,而且从不收拾;他送了一盆君子兰给我,有一次吃完饭,他竟然顺手就把菜汤倒进了花盆里,一盆被我照顾得鲜活靓丽的君子兰就这样毁掉了;情人节那天,他送了我一只小狗,我开心得不得了,晚上终于不用害怕了,结果半个月后的周末,他炖鸡给我吃,然后把鸡骨头都喂给了小狗,结果小狗卡住了,两天后挂了……
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对他实在无奈。那天,哭着掩埋小狗的尸体时,我禁不住想,是不是有一天,他也会粗心大意地喂我吃鸡骨头,然后看着我被卡住而手足无措?
他对工作也非常无谓,很难说他是心宽还是根本就不在意。我也粗心,也写错过投递报纸的地址,可没像他,竟然有一次,把报纸错发成光盘,第二天才发现。整整300张光盘啊,如果不是他运气好,邮局的邮件太多,积压到次日下午他去查询时还没发出,他就真的责任重大了。
他对人生似乎也很无谓,闲聊时,我曾经问过他对于职业和未来的规划,他似乎完全没有规划,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他说人不都是这样,命不由人,可我却并不这样认为。
与他的无谓相反的,是他的唠叨。他太唠叨,对我如此,对世界亦如此,对此,我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处女座。
事实上,在他第一次到西皇庄,和我共度周末的那一天,我就被他唠叨得颇为不快。
当时,他正在厨房做饭,我在公用卫生间里涮拖把。我承认自己不是个特别灵活的人,无论肢体上还是思想上。卫生间地面湿滑,我不小心就滑了一跤,虽然扶住了墙壁,但还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发出“咕咚”的声响。
厨房就在卫生间隔壁,他听见声响,便过来看,见我坐在地上,并没伸手拉我,而是皱了眉头,不满地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说完就转身回了厨房。
说实话,就在他拎着菜,笑眯眯地进门时,我还决定,不管怎么样,事已至此,就试着和他好好恋爱吧,可此刻他一句话,瞬间就把我刚刚蓬勃起来的勇气打入了谷底。曾经,他在小田的病床前,不合时宜地狼狈地摔了一跤,我都没有责怪他,如今,他为什么要如此苛责我的摔跤呢?
如果我在那一天,拒绝了他的冷漠和苛责,毅然决然地要求分手,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无奈和苦楚了。
然而,即便时光逆转,反倒重来,我依旧不会在当时翻脸,我以为,仅凭一句话,就去否决一个貌似明媚的未来,未免太任性,太矫情;就凭一句话,就放弃从一而终的美好理想,未免太可笑,太幼稚。
然而事实上,我对于他,似乎太过宽容了。
在搬到西皇庄的第二个周末,我就扭了脚。
那个周日,雷海生到来的时候,我正要去邮局取汇款单,邮局不算远,来回也就20分钟,于是我请他先进屋去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那是我当时收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笔汇款单,一千多元的稿费,比我半个月的工资还多,让我颇为开心,回来时,我连上楼都蹦蹦跳跳的。可没想到,就差一层楼梯了,我却一个不小心扭了脚,摔倒在台阶上,钻心的痛,一动也不想动。等疼痛稍作平息,我拨通了雷海生的电话。
“你在干什么呢?”
“洗菜。”
“哦,我在三楼,你能下来扶我一下吗?”
“怎么了?”
“扭了脚。”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的人了,上个楼还扭脚!”电话那头传来烦躁的叫嚷声,让我感到有些寒凉。
当然,雷海生最后还是下了楼,把我背回了家,不过我心里却并没有因此而温暖起来,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他的表法方式,也许是我真的太笨,但不管怎样,我就是觉得不开心。
真正开始相处,我才发现,雷海生是那样一个唠叨的男人,报社打饭的大姐将菜汤泼洒在饭盒边缘他唠叨,我的衣服上有线头他唠叨,就连邻居孩子用完卫生间忘了冲他也唠叨,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问题,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在他眼里都不完美。事实上,我们都是平凡的人,都是忙碌的人,哪里有时间去追求那么多的完美和精致,难道就因为上帝赐了你一张精致的面孔,你就有资格去要求这个世界毫无缺憾?
而当我第一次看到雷海生的身份证时,禁不住惊呆了,他真的就是处女座。
那一天,我去邮局取编辑部的汇款单,雷海生托我帮他查几封挂号信,顺手将自己的身份证递给我。我坚信英雄不问出身,真爱不问出处,所以从认识他到当下,从未打听过他的家庭、学历,乃至过往,可去邮局的一路上,我还是忍不住将雷海生的身份证看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他身份证上的住址就在朝内大街附近的大拐棒胡同。
原来,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推算,他真的就是处女座。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真的和雷海生有未来,那么嫁给他之后,我就可以成为北京媳妇,可以结束漂在北京的命运。
这就可以解释,雷海生所有唠叨和挑剔的根源,并不是不爱我,而是天性刻薄。
那是我和雷海生正式恋爱以来,心情最明朗的一天。
在我们相处的第三个月,我意外怀孕,我的内心异常恐惧,尤其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呵护。然而,当我对他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想结婚,不想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像充气气球一样,“砰”的一声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