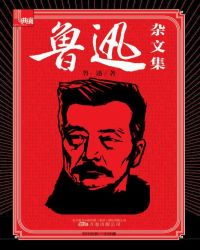第十一章 兵逢狭路运天机
第十一章
兵逢狭路运天机
轰隆翻卷的声浪,析出无数悉悉索索的轻声细语。在阿满的每日汇报之外,雪信也爱信马由缰地听些平叛军中的声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是小皇帝在教阿满念诗。
偏偏阿满烦他,也不愿听他讲解诗里的意思。她拿着诗就近问周都尉,周都尉说他是动武的粗人,讲不好。阿满又找高承钧,高承钧找到小皇上,让他少教河东军的大将军读没用的书。
阿满却上了心,追着高承钧问:“为什么这书不能读?哪里没用了?句子明明很美。”
高承钧回答说:“很美的东西,总让人心软。为将者不能心软。”
“可是高家哥哥送给雪娘子那一窝小狗崽儿,不就是哄她心软?”阿满不解。
“雪娘子总是硬扛她扛不来的东西。”
“我倒是没见过雪娘子有什么扛不下来的。阿满小时候帮寨子里的阿妈扛米包,起初时二十斤米背不起来,发发狠背上了,没几天就不吃力了,过几天还可以背三十斤米,然后是四十斤,五十斤。要是二十斤的时候不逼着自己,那这辈子都以为自己是个连二十斤都背不起来的废物呢。”
雪信在遥远的安城听见阿满这么回应,不禁赞叹,阿满总是时不时用她诚挚的回答敲中别人的麻筋。
“我希望雪娘子这辈子,连二十斤的米也不用扛。”这是高承钧在说。
“总有别人照顾不到的时候,就如眼下,高家哥哥不得不离开她。没有人为雪娘子扛米,雪娘子就该饿死吗?”阿满问。
“她已经扛得太多了。”高承钧加重口气。那是阿满听不懂的事情。
雪信听到这里便不高兴,她把那段声音推远了。
她又捕捉到苍海心的呓语。苍海心似乎并不知道自己讲述的是世间的真实事件,只是感情充沛地向另一个人交代他的梦境。而另一个人是个固定的讯问者、记录者。
苍海心:“我总是梦见雪信,这不对劲。”
女子劝慰:“少主总是想着新乐公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什么不对劲。”
“我梦见她用针刺我的翅膀。我醒来时,手臂上就有一个刚结痂的针眼。我梦见自己被拷在木桩上,四周是朱砂粉洒成的大幅符咒,醒来我就觉得自己躯体沉重。她用一把刻着符咒的匕首划伤我的翅膀,我醒来时胳膊上有一条血痕。我反复梦见雪信对着我咔擦咔擦地摆弄一把大剪刀,对我说着什么,但是口型太复杂,我没看明白。”
“新乐公主在说,少主还不进安城解救她于水火,她只有用那把剪刀自裁了。”那女子说。
可是雪信明明对那只海东青摆出威吓姿态,说的是“你不退兵,我就剪掉你的翅膀”。
她已彻底明白苍海心在鹰目所见的梦中听不见声音,唇语也不太好用。她尝试写字给鹰看,但从谛听中反馈来的消息看,效果也是平平。
梦中的信息太容易佚失了,一张大纸,写个满篇道理对方即便是看了清楚也记不下来的,写一首诗对方只能记住一半,写一两个字苍海心倒是能记得,但那个密切关注他梦境的女子会把梦境解释往别的方向,每每把雪信的劝和歪曲成叛军攻下安城的理由。
阿满风雨无阻,在挖下的地坑里汇报她的从军见闻。
她讲大军终于在通过地形狭长的崤函古道后驻扎下来,扼守住道口。这里是从中州进入安城境内唯一的通路,也是小皇上向各亲王通牒会兵的集合点。陆续赶来的亲王世子们向小皇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
“静西侯应该主动出击,早日结束战事。”他们讲的话大同小异,均是不耐烦在这寒冷的谷口虚耗费时日。
高承钧对小皇上说的是:“我方人心不齐,需要休整。敌方远路粮尽,急于求战。只要扼守古道,阻断敌军前路,敌无粮自溃。敌军前锋是各地投奔的饥民,仓促之间不及编训,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只要挫了他们前推的锐气,日久必作鸟兽散。”
高承钧的判断是精准的,可是决定战局的不唯有军事,还有政治。
作为各诸侯军首领的诸王世子认为高承钧怯战是别有异心,日日里说出难听的话。
小皇上也亲至阵前劝降。
敌军打的是“勤王”的旗号,道义上不能有亏失,态度上不能不对小皇上恭敬些,但对小皇上的那套说辞则满不以为意。
苍海心先是与小皇上辩论,后来双方道理讲腻了,就你来我住,你退我进,交战几次。
古道口狭窄,高承钧部署联军以新月形扎营,借天险拒守。
越军则是由南而北,从低地冲向高处,不仅攻城器械运输不便,也无法布置滚木落石等等的战争装置杀伤敌人,时节又是冬末春初,滴水成冰,信风西北,天时不与便利,水火战术也使用不上。
越军里的暴民除了每日里丢石块骂战,也无前推战线的良策。高承钧则日复一日地挂起免战牌,与催促出战的亲王世子们周旋。
战事并未大规模爆发,阿满的汇报里也多是山中狩猎的情形,大段大段的言语在说着新鲜野味的滋味。
在谛听中,那个女子对苍海心重复:“主人来信严辞催战,要速战前推。”
苍海心回答:“敌在隘口我在平原,敌在高处我在洼地,西北风从敌营吹掠我阵,他们在河口上游我们在下游,迎风爬坡,旗幡打脸,越地兵士已多有冻伤,根本没法打。他要打让他来打,我不想让兵士们送死。”
女子回答:“饥民图的是一口粮,粮尽他们就不会听话了。况且他们也早有自觉,与其饿死不如吃一口饱饭再死。打仗哪有不死人,为将者要做的不过是为他们的死亡排好次序,他们本就是准备着被耗掉的兵员。”
“他们跟从我是为了活下去,不是为了死!”苍海心暴跳如雷。
“他们吃主人的一口粮食,就把命卖给主人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主人筹谋得早,趁时局太平天下粮贱时囤积,如今我军粮食还可支付一年,安城却要绝粮了。催少主进兵,是救安城,救新乐公主。”
那女子又一次把苍海心说得沉默了。
雪信也是暗暗心惊,高承钧比拼消耗,原本是理智的应敌策略。但这也是基于安城国库的储粮多过叛军的判定,叛军以未经训练的饥民为兵卒,远路来攻战线拉长,稍延时日必然兵锋疲老,军心溃散。
可是叛军粮足就另当别论,消耗战最终拖垮的就可能是安城了。
她又不由想起在安城变乱的前夕,每一场风波都煽动起安城公卿们对奇珍异宝的渴求。龙涎香、水蚕丝、青虫簪、集翠裙,她也无意中成了帮凶。越地来的商人们趁机天价出售名香珍缕,还没捂热的钱一倒手就买作了粮食运进越王的粮仓。大厦将倾,安城的人们却醉心于宝器带来的虚荣,对迫近的危险一无所知。
安城情势危如累卵,安城的人们却还在摇摇欲坠的山巅享乐。
“我要见苍海心。我要劝降他。”雪信对玄河说。
“恐怕他一人止步,于大势也难有回转。”玄河说。
但玄河还是去安排了。天铁床台搬进药园军帐,雪信怀抱海东青,拔下鹰颅上的银针,刺进自己的手指。不多时,她犯困了,倒在天铁床上睡去。
睡梦中一缕金色飘絮在她身边浮动,雪信伸手抓住,金色飘絮被一缕金丝系着,她就把金丝缠绕在手指上,绕着绕着,被金丝拽起来,飞上虚空。
雪信看见了安城完完整整地呈现在她视野里,城郊已搭起连片鱼皮暖棚。月光透过云翳,百娘子和甘娘子还在指挥军民忙碌着。她们是真尽心,也明白自身使命对安城的意义,连睡觉都舍不得。
再缠绕手指上的金丝,如缠卷的风筝线,只不过被拉起来的是自己。雪信看见高而狭长的古道,这是越地叛军攻入安城唯一可行的通路。高承钧并不信任诸王联军,古道前后道口均是高家军的旗帜。
阿满在熟睡,雪信察看了她的梦境,她正在重温幼年时与母亲依偎的情形,她所挂念的四只小狗崽显现了形象,也被她安置在左右。
她也去看了高承钧,他皱着眉在深夜里睁着眼睛,待要走进他眉心时,高承钧的脸上浮起赤红狰狞的兽纹,她再也走不进去。险些忘了,高承钧以幽泉铁纹面纹身,从此不受术法侵扰。她亦再入不了他的梦。
雪信在高承钧的帐中盘旋,戚戚然盘卷了手指上的金丝飞腾离去。
再一次下落,是越军前锋的营地,雪信找到那顶睡着苍海心的营帐篷,她穿透顶篷落下,终于看清了那个睡在苍海心榻前地垫上的女子。
地垫铺了三四层,过去北长安令的女儿,莺子,她的一条胳膊搁在毯子外头,露着洁白的一截腕子。手腕上戴着一只特异的金镯,确切点说,是一支翠羽金簪被弯成了一个环,戴在手腕上。
雪信一点也不想看她的故事,但还是走进去瞥了一眼。金簪令的原主人孱弱早亡,没有等到自己的任务,临终前把翠玉金镯子套到了女儿腕上。华城来的人没有放过那女孩儿,在她的父亲被斩于市,她被发配官卖的当口找到她。他们为她设计好了新的未来,新的使命。也是同时,雪信找到给官卖牵线的刘牙婆,要替苍海心买几个侍妾。
如此就都说得通了。苍海心在安城时突有一阵抑郁乖张要出家,又后来一个坐在金线缂丝屏风后的女子扔给印社掌柜一个抄本,如此悬案都找到了源头。
莺子躲在暗地里做的事,还远不止这些。
苍海心四肢摊开,睡得毫无防备。雪信指上的金丝正没入他的眉心。
往日里他的梦境是深沟壁垒,无隙可入。但今日因着那一缕金丝向外发散,有了机会。
雪信想着自己散发出与金丝一般的光芒来,想着她的身形扭曲模糊混沌一团,成了一个金色的茧。从苍海心眉心延伸出的纤丝是金茧上唯一的线头,丝缕在回绞,收回苍海心的眉心,丝缕带走金茧上的丝,茧壳层层见薄,像浸泡在热汤盆里的蚕茧,只要抽起一个丝头,不多时被完全剥完。
雪信得以观察到苍海心从少逮列寨子失去消息后的经历。
族长说苍海心伤重,必须留在寨中疗养。瑶香草已差遣阿满送往安城,要他不必牵挂。南诏大祭司来到寨子里与族长关起门秘议良久。至于说的什么,因为当时苍海心没有听见,她也不得而知。
大祭司在与玄河的斗法中亦伤得不轻,无法自己行走,让人用软兜抬着。她行不了术,但带来一种形状颇似死胎的植根,称作毒婴参,样子如同长出了四肢的萝卜。
她用苍海心的手指丈量参身,确定了药量,一刀砍下,亲手在石槽里反复碾压漂滤,如此九次。太阳把石槽里的汁液晒干,大祭司刮下石槽底部的白色粉末,撒入酒中,敬给苍海心。
苍海心服下后,进入了无所不能的梦境。他双臂化作翅膀,直上苍穹。他双掌一合,可以将石头捏作齑粉。他剁一跺脚,大地战栗,裂出道道伤口。他在酣畅淋漓的幻境里上了瘾,幻境之外,接近他的南诏人无不被他撕碎,尸体残破,如丧兽口。
如此七日后,大祭司暂停了毒婴参的供给,把苍海心关进一间石屋。四壁和脚下均是由平整的大石块垒成,石头与石头的缝隙也被一种与石头相同颜色的泥浆抹平,泥浆中也许掺杂了药剂,石室内虽阴潮,石缝里却不长野草,石面上也不生青苔。一日三餐皆从一个狗洞里塞进来,送饭人一语不发,连面目也看不见。
苍海心从无所不能的肆意里跌落到一无所有的空室里,眼前所有的绚烂褪色成灰暗,不出三日,他以头触墙,满额鲜血,他躺在自己的屎尿里,眼珠灰白地盯着灰白的石室顶。
那时候,石室门开了,外面带着鲜绿气息的阳光染进来。莺子端着一杯毒婴参酒走进来,对苍海心说:“药酒给你的是虚幻的力量。做人间的帝王吧,你将永远不会在醒来后怅然若失。”
“滚!”苍海心抓起身下一摊臭不可闻的东西砸过去。
莺子端着酒退了出去。
又一次,门开了,莺子又端着酒进来。苍海心只有一口气了,她把酒给他灌下,趁着他的意识还未被湮灭,对他说:“那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太子坐上皇位了。天下岌岌可危,不知瑶香草种没种下,种下了又不知守不守得住。你就不想知道新乐公主如何了?”
“我要见她一次,让我看看自己做的蠢事,到底有没有意义。”苍海心说。
他眼皮上的光亮闪了一下,大祭司走进石屋。他们关了他那么久,是计算好了谈判的节奏的。大祭司取出一个陶埙呜呜咽咽地吹。苍海心闭上眼睛,他被看不见的埙声架起又抛下,他落入雪信的梦境。
那是雪信在安城外野庙里做过的逐鹿之梦。
那一梦后,苍海心带着莺子去往越地,大祭司也去了,她取下苍海心的一魂一魄,依附在苍海心最心爱的一羽海东青身上,苍海心在夜梦中侦看安城与敌营,莺子把苍海心的梦境记录下来,传书给她的主人,传信的雀鹰越飞越远,地下的饥民越来越多。
苍海心取下了中州许城,在身后设了大粮仓。越军的输粮线往来络绎,一车车的粮食倾倒进粮仓。若把饥民推上战场战死一部分,他们可以撑得更久。
雪信回到苍海心正在做的一个梦里。她惊讶于这个梦着落的地方,是在一个小灶间里。
窗户半开,一望耀目。不记得多久没见过这么洁白又那么厚的雪了,如一床鸽子羽的被子。雪风在窗前被屋子里的热乎气逼退。苍海心在炭炉上涮着鱼脍,一只小松鼠蹲在大条案上剥吃阿月浑子。
雪信发现她也是天衣无缝地坐在这个梦境里,面前是一堆碧绿的阿月浑子果仁。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安详之地,哪怕这个地方在梦境之外从未存在过。每个人也会给自己摆好陪伴的人,哪怕与那个人本身无关。在雪信到来之前,已经有一个“雪信”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所以苍海心专注于绯红的薄鱼片在沸水中转成雪白,那个熟知且习惯的慰藉,他没有更多贪求,只要她在,维持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不知道在松鼠眼中,人是不是都长一个样,雪信给那只松鼠相面,她不确定它是否是从她的梦境里跑出来的,曾经捱了她一箭的倒霉鬼。
她又捻起颗果仁丢入口中,颗粒在舌尖破碎散开。她看向苍海心,佩服他,面对一锅吃不出滋味的鱼片,他还能一片又一片地续。
该怎么开口呢,从私情切入是容易打动他的,可私情上他才是债主,怎么有脸再提?
谈大义吗?他是被她从山里用美食美色骗出来的,他哪来的大义?
唯有一个弱点,他心软,可怜饥民,不忍用他们的尸骨开路。
“好吃吗?”雪信问他。
举筷下一片,锅中那片正好半熟可以捞起来了,而碟中那片凉得可以入口了,口中那一片正好咽下去了。苍海心原本是在环环相扣的节奏里,突然听见雪信开口,乱了套,筷子上的鱼片放进嘴里,又被烫地吐出来。
“没我想的好吃。”苍海心扔了筷子,“可是有雪信陪着我吃,吃的什么,什么滋味,无所谓。”
雪信揉了揉脑门:“咱不说这个。”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还能张口说出动人情话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骗子,要么是真的缺心眼。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位,轻易表白只会让人捉到软肋,依然在表白的,要么是表白能省事地达到另一些目的,要么是一无所有没什么好担忧的,或者是脑子不清醒以为自己没什么好被人算计。
雪信听见表白就头疼,因为她面对的,是老谋深算的对手或者是二傻子,两者必占其一。她硬着头皮说:“这不是你寻常的梦,我也不是你梦里的摆件。”
苍海心点点头:“我知道,雪信你来了。你别害怕,别跑,我什么都不做。”但他已经把炭炉铜锅踹一边去了。他像是只兴奋的猎犬,被皮带勒着脖子才没有向猎物扑击。
“你梦见自己化身成鹰,鹰目所见是世间真事,不是虚妄。”
“我知道,所以并未尽言梦中所见。”
“回去吧,别来给安城添乱了。”
“安城粮不多了,我打下安城,你们就有饭吃了。”
雪信起身,关了窗子,再打开时,窗框所嵌的景色不再是纯粹的雪原,而是安城东郊的一处鱼皮暖棚。
她复现给苍海心看的正是前一日春播典礼的情形。
在别处还是冰河冻土时,暖棚里已是温润的沃土。雪信束起袖子,赤足在田垄间奔跑,四只小奶狗颤颤巍巍地在后头追着。张太后也来凑热闹,亲手洒出发了芽的谷种,以示对屯田的支持。
“吃粮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的。你不带着野心者的夙愿干扰安城的秩序,就是帮了安城百姓大忙了。”
“不对。你们的人要吃粮,播种也要粮。人要取暖,田地也要取暖。你们的粮炭不够支付的。”苍海心从座位上蹦起来,逼近雪信,“你在诓我。别任性了,你养不活安城子民。”
“安城人口大不如从前了,十成里九成投奔了外乡,剩下的一成随便养活养活不是难事。百姓与军队一同在田间劳作。我们不用和叛军拼粮仓。百娘子和甘娘子的异术让谷米一个月即可采收。收获粮食我们可以募兵扩军,接着翻田播种。而如今从越地到中州,叛军如蝗虫啃光了土地,平民被你们卷入战争,无人耕作。接下来的一整年,叛军盘踞的土地上都不会长出一颗粮食。”
“而且,你们的仓粟也不够了,才发了疯地催动战争,即便拿不下城寨也要战死一部分,粮食才够吃,是不是?自从你报告了安城中的阵法祭台,莺子就故意放出粮食可支付一年的假消息,意在吓退反抗,是不是?! ”雪信盯着苍海心的眼睛。
“越军不是无法推进,只是对无辜的人来说,代价太大了。”苍海心到了雪信身旁,他关紧窗子,再推开时,窗外已换做了他虚空里推演的战法。
大地隆隆震颤,叛军攻向狭窄的道口,当先的是四头林邑国来的白兕,三百钧的重躯排成一个箭头阵列冲向联军的防守营地。犀甲无惧剑雨,独角挑翻来组的军列,撞开营门前的重重关卡,捣毁防御工事,切割守军阵列。
紧接着而来的是战牛。双角捆上了尖刀,尾巴浸透火油燃烧着。它狂躁不已,势若雷霆,摧天崩地般结群冲撞营盘,将抵抗者踏作齑粉。
接下来的一阵是饿了三天的狗群,它们的数量众多,受过训练,一入峡谷就清扫还站立着的军人,扑咬他们的喉管。
三轮冲击后,饥民组成的前锋部队才冲上来追杀联军残兵。燃烧的土地上,疯狗开始吞食肉糜和残肢。
也许在某个地方,苍海心做过类似的演习,他才能绘声绘色地推演出一场末世劫难般的战争。他关上窗子,对雪信说:“高家军人单势孤,诸王联军心又不齐。高承钧扎下营盘后,未敢发起一场袭扰试探。”
虽为将军的女儿,雪信却没有亲历过一场战争,推演中血肉横飞、骨头爆裂的景象令她脸色苍白,脚步虚浮。她倚墙滑了下去,苍海心来拉她,她做出了拒绝的手势。
苍海心就蹲在她身旁,用一个老好人的口气说:“让我犹豫的,正是不能伤太多性命。你们抵抗不了兽战的。你们降吧,我保证不动新君性命。”
雪信又扶着墙站起,走到大案台前,抓过一把阿月浑子果仁塞进嘴里。这时她领悟了吃东西的另一种意义。在完全尝不出滋味的情形下,她情不自己地保持着咀嚼,好安定心绪,让头脑运作。
片刻后,她开口说:“不。若是兽战可行,你不会停下。你有三个忌惮。一怕兽战难以控制,你怕我的表弟,新任的皇上在混战中有失,则你们叛军再不能以勤王的幌子稳固人心。二怕林邑国的白兕熬不住中州大地的早春严寒,无法尽数发挥你预期的战力。三怕东南信风未至,火攻反烧了自己。”
苍海心露出两排雪白的牙。他是在笑的,可在任何人看来,他好像是猛兽在炫耀他的撕咬力:“分析得在理。可即便我受严寒掣肘,你们也只是凭空得了两三个月的残喘。你们的粮食支撑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又如何?你们才是一帮乌合之众,重创之下,你们的联军会裂成几块,向哪几个方向溃散,谁都可以预料。”
“没有粮食的军队,才是时时刻刻坐于炉火上辗转难安的吧。”雪信并不肯认输。
“那我们倒可以比比看,谁家的粮先耗尽。”
“那就耗着瞧。看谁先撑不住。”
“你可能没有见过,也无法想象。绝粮后,一个地方的草根树皮先被挖出来吃掉,然后是泥土,再后来就是尸体,然后是活着的孱弱者。”苍海心字字珠玑。
“你见识过,即是说越地百姓已绝粮。”
“绝粮,有时是天灾,有时是人祸。一座城池饿死了许多人,它的仓廪却不一定是空的。”
“所以不是蝗灾,是早有预谋。”雪信迟疑道,“你还是我认识的苍海心吗?”
苍海心叹息:“天下乱了,没有粮食了,我来安城救你,救你关心的天下人,有错吗?”
他讲得过于真诚,他也真切地以为事已至此,他才是天下的拯救者。
他的信念笃定,雪信也没有了反驳他的言辞,愣愣怔怔地看着他:“我不会让叛军见到中州的春天。”
“那我也不会让安城捱到粮食采收。”
“你醒一醒,南诏大祭司的毒婴参酒会迷失你的本性吗?失去一魂一魄,你的心智被蒙蔽了吗?”雪信感到有些悲哀,苍海心看着好好的还是他,他推演的战局,说的话,又是全然的陌生。
“你来谈判,谈完了吗?能不能说点私事?”苍海心捧住了她的脸颊,“我好想你。少逮列的姑娘,越女吴娃,怎能与你相比?”
雪信在后退:“我讨厌拿别人与我比较。”她抬手从后脑拈出一支绣花针,针迎风而长瞬间时成了一把长剑,透山剑指出了苍海心的面门,“我是来谈判的,我要你退兵。”
“不可能,兵无故不起,兵不故不能止。”苍海心说,“无故退兵,就是承认我们错了。我们没有错!我们在拯救即将崩塌的天下!”
雪信手中长剑一划,她眼前的小灶间破为两半。碎片崩飞,苍海心还在虚空中叫嚷着什么,她已听不见了。手指上的金丝拖拽着她,而她腾空后退,掠过两军对峙的阵营,掠过河洛田野,猛然坠落,在安城药园的军帐中醒来。
雪信翻身滚跌下天铁床,睁开眼,尚分不清自己是醒在梦里,还是从梦中醒来。玄河递给她一盏醒神汤,她席地饮下,旋即吐了一地。
一夜之中,她先行谛听术,再行旋天术,神飘魄荡,精力耗费,魂不安于躯壳,心脉脏腑运作紊乱。她又去伸手在案几上摸索,抓住了什么,塞进嘴里,又吐了出来。是过药的蜜渍果脯,太甜了,甜成了砒霜。
舌尖有了滋味,至少提醒了她,身在梦外。
她又伸手向几案上摸索,找到一盒乳香炼制的糖丸,丢到一旁。
玄河问:“公主在找什么?”
“我想找点吃的。”
“公主想吃什么?”
“我想尝尝阿月混子。”雪信目光倏然变得深远,似在回忆梦中,“梦里它们看着像珠贝里的翠玉,我以为会很好吃,可嚼着像蜡丸,没有香气,没有味道。”
过去在公主府里,说一声要什么,马上就给找来。如今的安城里,却不知去哪里弄一捧阿月浑子。
玄河从衣袖里提出个小布囊。他私藏的口粮是一把甜杏仁,倒在几案上慢慢剥去壳。
“看来苍海心分离了一魂一魄后,也丢失了鼻观舌尖的感觉。他的梦里也不会有气息和味道。”玄河把剥好的杏仁递给雪信。
“他不但嗅觉味觉坏了,脑壳也一团浆。我和他说不通。”雪信行云流水地往口中扔杏仁,紧张地咀嚼。果肉破碎后在舌面翻滚,她把它们嚼得更碎一些,细细榨取杏仁特有的脂香。
“他们还有多少粮食?”
“我不知道。当他们发现我在谛听,他们的密语也就不可信了。也许是匮粮求战,却故意放出假消息骗我们出谷一搏。也许是天时地形不利,前锋被阻道口,他们故意说大了存粮数目,瓦解我方军心。”
“战前的安城,一粒明珠万斗米,珠贵而米贱,粮食被商人低价赎买不啻劫掠,叛军也有可能囤积了足够多的粮食。他们能等待着安城掏空老底后打开城门,等着平乱的军队献出皇上交换粮食。”玄河分析着。
“战争转入消耗就不会有赢家。家贼与外寇,虎视狼顾,垂涎三尺,磨牙霍霍。只等交战的两家伤了元气,哄抢争食。还是要尽快打出结果,解决罪首。”雪信不嚼杏仁了,眼光落在玄河胸膛,“调养恢复得如何?”
玄河笑答:“公主有用,就凑合着能用。公主没有吩咐,我再惫懒些时日也无妨。”
苍海心在他的梦里也点中了雪信的要穴,雕虫小技又岂能对抗天时。
同门有异术可使粮食早播快收,但一个月即熟的谷粟也只有寻常一季成熟的庄稼的三分之一大。贪省了两个月,收成也折去六七成,人力翻倍,还要加上物料费用,种一亩就亏一亩。
况且炭一时备不了许多,搭建暖棚必须的大鱼皮非寻常江河撒网可捕获,无法大片推行。雪信请骆百草和骆孰甘来主持早春的播种,是向迷惘无措的人展示一个奇迹,告诉他们她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安城可以活下去。
在雪原冻土上开荒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在于信念,众人抱定了希望划动危崖瀑布上的孤舟时,不可能也会被撬动。但当所有人被微小的奇迹激励起来时,也必须有几个人冷静计算现实,考虑别的对策。
地已划了出来,雪信将城东大营里的河东军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与民夫一道犁田翻土,骆百草和骆孰甘会挑选耐寒扛冻的谷种和菜籽撒下去。生长和采收快慢早晚各有一些,长得最快的菜很快能进伙房营的大锅。开春后,她们调拌的肥料可使土地不停轮作,不需要休息。另一部分军队与在山腰结营驻扎,边练兵边狩猎。两部人马定时轮换,猎来的肉食分一半去屯田营,而屯田营也会把收获的菜谷输送进山。
雪信上半天会在山营中训练女军,操演大阵。下半天去东郊巡视田亩,猴子每每会泼一通苦水,再提出一两个麻烦要雪信解决。入夜后回到公主府,关雎等在府中汇报招贤馆白日里招待了什么人,又有何人要与公主密谈。
然后抱一抱流采,雪信就往药园去了。
她在药园里读完张太后给她送来的奏折抄本和前线塘报抄本,入高台搜听有用的密语。而后她小睡两个时辰,天不亮就起身赶赴城外山营。
清晨的阳光里,出早操的军士们头顶热汗蒸腾,他们看见雪信身披红袍,肩上架着海东青站在帅台上,斗篷帽子上结了厚霜。她坦然露出了她的面孔,癍痕又淡了些,相侵的颜色也柔和了,竟像是一种新创的时世妆,像是对美丽的欲盖弥彰。
美丽是桩不足挂齿的小事,或者说她并不想要“让人看着喜欢”这种美丽。她如今要的是人们的敬畏。
高台上的红影安定坚毅。
“儿郎们,国乱未平,家仇未报,该当如何?”雪信无视高承钧留在营中的几个将军,例行训话。
“厉兵秣马!蓄势待发!”河东军山呼震响。
战场上对峙的僵局不破,谈判桌上的筹码也不会消长,谁也不会凭空让步的。
想当初的高承钧,在大漠上自由驰骋,迅捷如风,劫掠如火,如今据险而守,勇武不得彰显。
少年时见苍海心,左擎苍右牵黄,驾着块破木板在雪坡上乘风破浪,如今也是前路壅塞,豪情不能舒张。
总会有个人沉不住气,会跳出来闹些动静。
与苍海心谈判失败十日后,塘报抄本后半夜加急送来,把雪信自榻上催起。
张太后说,要公主立刻拆看,看完进宫相商。
报上说,叛军前锋营寨后退三射。高承钧在古道东路口以宁王世子苍孟极为左翼,楚王世子苍并封为右翼,高家军分作两部各护卫皇上所在的中军和后路。鲁王世子苍陆吾在新月阵营臂膀环抱处设一字营,为屏障。
叛军前锋日日来阵前讨战,赤身露体,抛掷石块,吼些不堪入耳的言语。或者穿上裙衫涂了两腮红胭脂,故意扭捏作态从阵前来回巡弋,那些人的抹额布巾上,均写上我方将帅的名字。
张太后当然是不明白,为何好好的,叛军要后退,高承钧为何在敌人后退后加固防御。叛军既后撤为何又来搠战,高承钧为何要把没什么打仗经验的苍陆吾顶在最前方。她关心的是高承钧的决策会不会有失,她的儿子有没有危险。
她也是明白的,挂帅的是她的儿子,但指挥打仗的还是高承钧。若高承钧的调遣布置不恰当,也只有雪信能写信提醒。
雪信说:“苍陆吾没什么打仗的经验,在安城时,哪里打架也少不了他,他与苍海心打得多,自然有结了仇。再加上他又没耐性,是个戳一下就跳起来的人。初次上战场就更妙了,他是层一磕就破的蛋壳,敌军渴望胜利,就不会放过他。” 听香录(全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