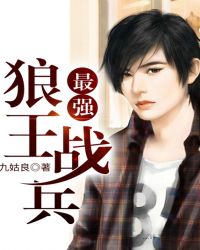第十七章 行人南北分征路
第十七章
行人南北分征路
十日过去了,安城药园恢复了往日的齐整。田块划得四四方方,长得快的草药又能收下来一批了。
城外最安静的地方是荒坟野庙,城内最寂然的要数这药园了。虽是人影憧憧,川流不息地忙着,药僮们却都保持了缄默,没人说话,也没人笑,谁都不会再徒劳地尝试开口,让自己和别人听见气流空洞洞穿过喉咙的声音。
只有药园中心的一片地,还耸立着那座小土山,山坡土面刻画满扭曲的划痕,如同符篆上神秘诡异的天书文字。玄河提着一条铁棍修补维护着土层上的刻痕。
枇杷树又油绿了些,风过叶声簌簌。十天里他给枇杷树浇水,第一桶汤药还是浓稠的参汤芝露,第二桶药剂却掺山泉水稀释了十倍。十天里,雪信再没有从树根下升起来。这是他可以理解的结果。
玄河扔掉铁棍,在树旁盘膝坐下,目光穿过土层看进了沉香山子内部。
那里是浓稠如浆的黑暗,灌满了死亡与新生的味道。黑暗里交叠着另一幅若即若离的图景,居然是灼热刺目的阳光,他拨开厚绵绵的云层落下去。
底下是个小镇,不见一个人走动,但小镇是活的,柳绵飘飞,流水缠绵,生生不息着。他找到了一家小酒肆,门口种着漫如伞盖的泡桐树,红色酒旗半新不旧,墨书着“百酿泉”。树下铺着一张毡毯,少女枕着一叠账本躺在毯子上,姿态谈不上淑雅却是放松的。泡桐花在她身上落了薄薄一层,她随意捡起脸旁新落下的一朵放在唇边吮蜜。雪青色的花朵细腹敞口,与曼陀罗花有几分相似,却更小巧玲珑,浑然天成的花盏。
“甜吗?”玄河开口问。
“甜啊。”雪信回答。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有过美好的回忆吗?”玄河四顾。
“锦书在梦里给自己造的地方,我看着喜欢,照样弄了个。从华城到安城,从安城到龟兹,安逸时不自在,自在时不安逸,何曾有过宁静,何曾有过我不去找事、事也不来找我的日子。”雪信似睡非睡,回答也半是梦呓。
玄河走进小店,不多时抱了小坛酒出来,用袖子扫开毯子一角的落花,小心翼翼坐了。
雪信用脚碰碰他的脊背:“我一个人躺着才自在。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玄河移到石板地上坐了,拍开酒坛封泥。
“这里的酒能醉人?”
“能啊。”玄河回答,仰头就喝上了,“你不问问外面的情形?”
“外面什么情形,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出不去的时候,急也急不来,不如享受安宁。”
“你是生气了吗?”玄河问。
“要是过去,我会抱怨受了骗,又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握。可这次,决定是我出的,拉拢利诱你是我做的,我有什么好抱怨。没有人会完全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做决定,你收取代价是理当的,我不生气。”
玄河松了口气,又听见雪信说:“既然你帮助我是收取代价的,价码可以谈谈。你帮助我,我回馈你,我也不欠你,心里也不会有歉疚。也是公道的。”这十日里,她不找玄河争辩,是等着他来谈条件的。
“那你打算好了用什么换取自由呢?”玄河自然也明白雪信的意思。
“这里的宁静可与你共享。你孤独的时候,我同你聊聊天。但我要出去,我去哪里,做什么,你不得干涉。”
“一想到你与我聊天也是一种筹码,每一句话都在计算代价,可能越聊越觉寂寥。”玄河苦笑。
“若我把你当做朋友,闲聊自然也不必一边聊着一边摆算酬。可你又把我当作什么呢?”雪信抬起手臂看了看,丝线勒痕犹在,“枇杷树,就是你拴狗的桩子?”她的愤懑终于没藏住,摆上了脸。
“我说过的,去得太远,会回不来的。我怕你消失不见。”
旋天术之所以被本门列为禁术,自然是已有不少人死在这种术法上。魂魄得以旋天而上,遨游九霄,晓遍世事,观透人心,能力近乎鬼神。
而世上没有无代价的好事,魂魄无穷无尽的力量依赖于施予躯体的药剂。即便坐拥金山银山换得来各种稀世名珍的药材,又哪里去找忠诚照料那具躯体的人呢?财尽人去的那一天,飞翔的灵魂终究得回到清醒的躯体里。
但体验过了无所不能,躯体就成了逼仄沉重的囚笼,魂魄回到躯体中,路要一步一步走,人心隔阂,世事亦无法洞察,谁愿意回去?于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不回去,他们运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切断了魂魄与身体的联系。
而后有人穿梭在陌生人的梦境里汲取力量存身,渐渐忘记了自己原来是谁,被称作魇鬼。有些人的魂魄在游荡中遇到了更强大的力量,消散了。
“好吧,就当我错会了你的善意。”雪信说,“可我还是要出去。”
“你十日出去一次,每次以一盘香篆为限,逾时不回,我会召你回来。”玄河开出了他的条件。
“一盘香篆烧完,我必回来。”
“还有,”玄河把自己从青石板上挪到了毡毯上,躺到了雪信身边,“我要在这里休息。”
雪信点头:“可以。”她又拣起一朵泡桐花吮吸花蜜,却暗暗把花揉得稀烂。
玄河闭上眼,又睁开,回到现世的药园里,他从卫士看守的作间里拎来两桶汤剂浇在土坡顶上,目送着雪信化作蝶群升起,又化作金雕扶摇直上。
这一回,金雕先在安城中盘桓一匝,见到永安宫中,太子换上了皇帝的冠袍,登上宣政殿听群臣吵架。看见城外大营中,河东侯生出了连鬓络腮的胡子,举着剑鞘对空劈砍发酒疯。又看见太上皇与锦书轻车简从行在去往东都洛城的路上。他履行了诺言,放弃了皇位,可他传位太子,无异于把那个天真的少年推向虎狼堆。
金雕折向南方,见到马背上的苍海心,他骑的是五百里加急的驿马,按说早该深入南诏腹地了,可伤势拖慢了他的脚程,才刚进入南诏地界。
其实以他的伤情,能在如此颠荡的赶路中活下来,都已是个奇迹了。他生命力顽强得像狗一样,没那么容易死,隔不了多久又活蹦乱跳的。
金雕换形作了蝶群,扑向苍海心的眉心,迎面就撞上了一道无影无形却坚如金刚的屏障。差些忘了,苍海心的梦是不好窥探的,华城的那个人对他就是偏心。
蝶群再次化作金雕盘旋而起,金雕目光如电,扫视着密林遮盖的大地,俯冲向了一座竹子搭建的王宫。
玄河从没有提起过南诏那条生长瑶香草的地脉从哪里走,穴眼又在何处,但雪信在南诏王宫里见到一片重兵守卫的花园一点也不惊奇。在花园的翡翠栏杆之中生满了瑶香草。
在她亲手从高承钧手里夺过那株瑶香草毁掉,在苍海心对她说他要去南诏找瑶香草的那一天,她只把自己的未来盘算到把锦书唤醒为止,之后是什么样,她不知道。
每次豪赌,输了大不了一死,她不怕死,她还幻想着人死后灵魂会从沉重的躯体里挣脱出来,破茧成蝶,来去自由。即便蝴蝶也会被风吹死、被雨打死、被霜冻死,她也不遗憾。
那时她并不需要高承钧手里的瑶香草,也不指望苍海心从南诏带回新的瑶香草。如今她猛然发现,躯体的生死和灵魂的来去皆不由她。瑶香草又变得重要了,瑶香草能把躯体和灵魂的所属权归还到她手里。
雪信站在瑶香草中间自嘲地笑笑,她能做别人梦中的主宰,却撼动不了现世的一片叶子。她刹那间去得了万里之遥,却带不回一颗沙粒。
这就是她曾期待的自由?
蝶群在王宫里试探寻觅,绕过了成群穿着手织布长裙的侍女,见到一名正跪在木桌前捣药的小姑娘,十三四的年纪,穿着白茧丝长裙。蝶群飞进她的眉心,那里有些无趣,捣药的姑娘梦里依然捣着药。
雪信袍袖一拂,简陋的竹屋隐去了,茂绿的山水也没有了,小姑娘捣着捣着,手底下的药杵与石臼消失了,她抬头望着立在云上的雪信,转而低头见自己的双膝也跪在厚绒绒的云上,“哎呀”了一声,向后坐倒,又立刻爬起来,向雪信摸去:“天神终于来看阿满了吗?天上是这个样子的吗?天神果然比阿满见过的所有人都美丽。”
雪信选中这个女孩子只因看她装饰素雅,衣料娇贵,想来身份与众不同,年纪小又容易哄骗,没想到一上来被抱了个满怀。
翻看这个自称阿满的小姑娘的回忆才知道,她乃是南诏新一任的圣女。只是阿满不大开窍,被选为圣女一年有余,也不曾有过感应,久了人们也不再期待她带来神的旨意,她也不好意思在王宫里做个混吃等死的闲人,就常来帮着王宫里的医官做些杂活儿。
雪信调整好神色,露出慈爱的笑容,暗中使劲把阿满的小胳膊往下摘:“这些年,女大王阿水管理南诏做得很好,辛苦了。”
“阿满会把天神的褒赞传达给大王!大王一定会高兴的!”阿满语气兴奋。
“圣女必须通过天神的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女。我迟迟不来,是因为担心你太小,通不过我的考验。”雪信琢磨着瞎话开始骗阿满。
“阿满被选为圣女,不就是天神的认可吗?天神的考验?祭司大人没有对阿满说过啊。”小姑娘说话一点也不懂拐弯。
雪信挂下脸道:“南诏圣女,是天神的传话人。南诏祭司,是天神的侍从。你是听天神的还是听祭司的?”
小姑娘了悟:“是了,阿满要听天神的,祭司大人也要通过阿满听天神的。”
雪信趁机说出自己的目的:“我有件事要阿满去做……”
阿满打断雪信:“可是阿满只是给天神传话的,不管什么事,都是祭司大人安排去做的。”
怪不得这个小姑娘一年多没有感应呢,死心眼,一根筋,没感应也学不会装些感应出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好不容易有人入梦,一上来就呛对方。雪信气得捂住她眼睛:“阿满困了,睡会儿吧。”
“阿满不困,阿满要听天神的教诲。好不容易见到天神,怎么能睡着?”小姑娘移开了雪信的手,眼睛瞪得溜圆。
雪信居然无法把小姑娘哄睡着,只有再把手一拂,云层洞开,底下是恢弘华丽的安城,她让脚下的云徐徐落下去,让阿满瞧得更清楚些:“有一个人从天朝的安城来,他与同伴星夜兼程赶路,把驿站的马都累伤了。前路的驿站提供不了足够的快马,他让同伴留下,自己带着三匹最快的马独自上路。”
她让阿满看见了一个在三匹马的马鞍上来回腾挪的青年,头发蓬乱,华服上旧血干涸渗出了新血。
“他出发前受了很重的伤,一路骑行,伤口反复裂开,不能愈合。”
“好可怜,他来做什么?”阿满问。
“他来南诏找瑶香草。若他在南诏遭遇不测,祸事便会降临南诏。”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给南诏带来灾祸?”
“他死在南诏,南诏才会有麻烦。”雪信没好气地纠正。
“那为什么他死在南诏,南诏就会有麻烦?”
雪信耐住了性子才没把小姑娘提起来吼一番:“天神只需要说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只需要传达给大王,前去迎接这个人,给他治好伤,把瑶香草交给他,护送他回到安城。”
“瑶香草不能离开圣地,离地即枯,不可以带走的。”阿满又说。
“移栽瑶香草,可以挖走根下的土,植于玉盆,两个时辰换一次盆土。可这样要带许多土,负重翻山越岭,走太慢了。不过还有一个法子,就是收集瑶香草的种子,贴身收藏在洁净赤诚之人的心口。你们圣地的瑶香草根下埋了个罐子,里面就有瑶香草的种子。”雪信说。
小姑娘惊诧:“天神连这个都知道?”
“阿满是不是不把我当天神?”雪信留下这句话,一转身就走出了小姑娘的梦境,她的耐心已经被这小姑娘磨尽了。
金雕掠过南诏潮湿油绿的大地,向西北面飞去。山脉群石骨峥嵘,白雪皑皑。
祁连山是把吐蕃阻挡在中原王朝西南的天然屏障。长城在北面抵御塞外部族。祁连山与北面蜿蜒的长城墙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唯一的通路,通路的尽头,玉门关与阳关是通商要道,也是运兵咽喉。
金雕低旋,在一支商队里感应到了属于她的公主金印的气息,它落得更低些,看到是领着高家军扈从的秀奴与带着公主府侍卫的花奴。
她们换上胡服女装,遮上面纱,扮作胡商姐妹,军士中有胡人也有汉人,都改扮作了伙计。马背上运载了大箱子和串串茶陀,晃晃悠悠地徐行在向西去的路上。
金雕用金色眼瞳翻遍商队中的每一张面孔,唯高承钧不在其中。蝴蝶分散进入他们的梦中,得到了他们十天前的记忆。
在狂奔中,他们的马已开始出现暴亡,还有磨坏了蹄铁需要重新钉掌的。所有人都清楚,这支队伍只会把高承钧越拖越慢。
随行军士都出自高承钧当年带领的高家军死士部队,一旦坐骑失蹄,滚跌倒地的军士会拔剑刺死抽搐中的爱马,而后自刎。秀奴的价值人所共知,不需要高承钧下令,每一回她摔下马,都有人默默让出自己的坐骑,代替她留下。
在路口,高承钧选择了去秦州的方向。秀奴与扈从们无一人开口问高承钧有何打算,接下去的路又要怎么走。他们在疲惫与亢奋之间挣扎,随时可能崩溃,而高承钧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这个时候高承钧的沉默坚定,让他们确信路是走得通的,不管他们付出多少代价。
秦州城下早有准备,队伍齐齐整整地迎候。迎候人员只有百余,皆捧着酒肉与银钱。
高承钧那位少年兄弟豪迈大笑,说:“高兄来时与我痛饮同醉,今日高兄回安西,怎可不来饯行?”
高承钧下马到少年兄弟近前,嚼了肉,饮了酒,对方忽然拔剑,剑还在中途,高承钧手里片肉的小刀已刺进对方心口。接着高承钧拔出自己的佩剑斩向已围住他的秦州军。百余人瞬间死了一半又散了一半。
高承钧从容不迫地割下少年兄弟的头颅掷上秦州城楼,又命令扈从将抛散一地的酒囊熟肉挂上马背。
城楼上自顾自乱了,有人说高承钧再凶狠也不过是零星几人的末路穷寇,此刻众人出城必能击杀。但去开城门的人被反对的人杀了。反对的人说,守城主将已死,余众还要送上去陪死未免愚蠢。
在秦州军的眼皮底下,高承钧风卷残云地完成了补给,上马狂飙而去。
在通往凉州的路上,高承钧下令劫杀了一支商队,他们补充到了清水、干粮和马匹。商队的马匹擅负重、耐远路,却不能飞驰突袭。高承钧下令掩埋了商队成员的尸体,命秀奴与扈从扮作商队缓行,出阳关走南路,寻找巴图所带领的高家军。
“带去我的手令,命大军停止前进。若巴图抗令,其副将取而代之。”
秀奴与扈从以商队的脚程走了十天,期间花奴那一拨人追了上来,加入了这支假商队。而高承钧在十天前,一人一骑独向玉门关方向去了。
金雕离开秀奴花奴的队伍,向更西更北追去。沿途每座州城,她都要望一望城楼上有无异样,有没有挂起高承钧的脑袋。
她在碛滩上见到躺在巨岩阴影里睡觉的高承钧,心才落回原处。
凉州、甘州、沙州,小小一条河西通道,北有突厥,南有吐蕃,夹在中原王朝与高家控制的西域之间,有中原王朝派驻的戍边部队,有袭扰不断的流寇,有混成了老户头的外族细作,也有地方大豪绅招募训练的民团。
高承钧死在安城——不,也有说高承钧叛出了安城又杀了秦州守将的。
高家军与葛逻逯起兵为高承钧报仇——不,也有说是早有布置,此时起兵是接应高承钧的。
皇帝传位给太子——不,也有说皇帝已崩,朝廷秘不发丧而已。
回纥、突厥、吐蕃,正在集结力量将三面夹击中原王朝——不,也有人说他们只要趁乱扩张一下势力范围就好。
来源不同真假难辨的消息扔到一个锅里,咕嘟咕嘟蹿个不停。正是势力错综,人心纷乱,朝廷的大事到这里反而不算大事了。
高家在西域是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力量,但在河西就没几个人认得出高承钧了。驻守城关的部队尽职尽责,日日举着绘制得不太像的画影图形盘查大股商队,甚至没什么人注意到一个乔装改换了面貌的高承钧马不停蹄地从他们身边穿插过去了。
在出玉门关前,高承钧最后一次停下来,枕着马腹睡了长长一觉,睡得像死了过去。黑马鬃毛间挂满盐霜,高承钧下巴新长出了胡茬,头发混进沙粒子结成一团。
雪信落在他身边,几乎不忍打扰他力竭后的酣眠,可她还是走进了他的眉心里。
梦中的高承钧坐在一顶帐篷里,帐中陈设布置与龟兹城外高家军大营主帅大帐中的一样,只是营帐空荡,没有士卒守卫听令。他伫立在沙盘前,死盯着前方相隔不远的两条路。
雪信骤然出现在沙盘的另一端,质问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为什么还是走了秦州?”
高承钧抬起头:“你终于来了。十天里我在马背上恍惚打盹,也曾再梦见你,梦见十几年来你的模样一一都转了一遍,可我知道那都是假的。假的你高高兴兴的,也会说些让人舒心的话。你不高兴了,我就知道真正的你来了。”
“为什么不走泾州?”雪信神色冷冷,她估算着香篆上未燃尽的长度,心内焦躁,顾不上唏嘘别后感伤。
高承钧回答:“若果真如你所言,泾州守将是有大义之人的话,放我过去,他不免以死谢天下,亦会牵连河东侯。而秦州守将不顾念少年同袍之谊要取我性命,被我枭首是他咎由自取。”
“若是我说秦州守将无心害你,泾州守将要杀你,你是不是会取道泾州?”
“秦州守将放我,我可以从他处补给水粮,日后自会重酬谢之。秦州守将杀我,我也从他处得到了补给,此外还要叫天下人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那两句话听得雪信头皮发紧:“那支商队里又有谁背叛过你?”
“我若不杀他们,死去的安城平民是白死,一路追随我的扈从也是白死。”高承钧的回答里听不出他对死去的人有什么愧疚。武将的功名本就是拿人命垫,不死上那么多,前头填进去的人命全没了意义。他连自己的性命也敢豁出来赌,遑论他人了。
那一刻,雪信有了犹豫。高承钧逃出安城,搅动天下风云,他要活下去,就会有更多人死在他手上。若是高承钧困死在安城,如今的天下也不会更太平,暗怀鬼胎的人依然制造得出理由举事,人并不会少死几个。
天下英雄忙着乱中取胜,高承钧岂肯过早放弃,平庸地死去?雪信摇头,如今她也进了赌局,不能让高承钧死。
“过玉门关,有两条路。”高承钧说,“你告诉我走哪条?”
玉门关为通西域的襟喉,在肃州东石关峡内,城关据天险而立,南北两侧山岩壁立,陡不可上,过关只有一条峡道,关上玉门都尉统兵五千。
由此过关前往龟兹,要多绕百余里的路,但沿途不乏水草,容易穿越。在瓜州北五十余里外,葫芦河东岸,有一座前朝废弃的玉门城关,由此出关便进入八百里瀚海,风灾鬼难之地,驿程虽短,但沙漠中沙山形状随大风变换,一旦迷失方向,耗尽水粮即在烈日下倒毙。
巴图走南路,古力佩罗走北路,留出中路不管,即是认准了高承钧过不去,最后他要么在城关前被乱箭射穿,要么在沙漠瀚海中蒸干体内最后一滴水。无论高承钧死在何处,高家军的兵权都会顺势落入巴图手中,而仇怨却要算在朝廷头上。
“随你走哪条路,我都会让你活着。”雪信口气淡淡的,还有些无可奈何。
高承钧与她又有何不同?都是嘴上问着意见,其实心中自有打算。她已拥有的力量,应该足够纵容高承钧的恣意妄为。
高承钧的手指点向了废弃城关的方向。他亡命十一天了,脸上尽是油泥,指甲缝里黑黑的,但在梦中,他的手干干净净,指头修长,骨节匀称。
武将也有武将的尊严,他不愿像一只狩猎场上的鹿一般被包抄驱赶射杀,宁可死在无人的地方,宁可无人见证地死去。尽管后一种死法耗费拖延,折磨人得多。
“你看清楚了。”雪信手一挥,沙盘上八百里瀚海地貌有了些微改变,“这是最近几日瀚海沙山的形势。”手指虚空划过,在瀚海中勾出一道线,“不要远离这条地下暗河。”
“雪信,”高承钧唤起她的名字,格外郑重,“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你在安城还好吗?”明明应该是他更熟悉这片地域的,但沙山的形势、地下河的走向,都会随气候季节而变换,也不是哪本书、哪册地图能确切记述描绘的,她居然知道得如此详尽。
雪信装作没有听见他的疑问:“我十日后再来。不管前路多艰难,你也要走过去。”
如同鱼被钓上岸、风筝被收了线,雪信回到安城药园,沉入沉香山子中。
她躺在泡桐花树下,花没完没了地落下来,要不了多久就盖了她一身,她却连抖抖衣袍也懒。总也是艳阳,艳阳也会看腻,总也是和风,在黑云压城城欲摧里维持一片虚假的艳阳和风,也越来越令她难捱。别人上刀山滚沸汤,而她却躲起来,等别人拼命拼出了结果再去收割。这使她在无法无天地狂妄同时,又生出自己连一粒尘沙也不如的微渺之感。
玄河走进沉香山中的小镇,一切如旧,只不过泡桐树树身上多出了几道透山剑的刻痕。山中小镇没有昼夜交替,只有参考山外的天色和玄河给枇杷树浇水的间隔,刻木计算时日。
“安北都护府兵马严阵以待,朝廷也遣使突厥,以防回纥与突厥联盟。河东侯率军开拔,准备御南路高家军于阳关之外。”玄河问,“雪信,你想把朝廷的命运推向何处?”
无论高承钧能否活着回到龟兹,战争都是一触即发。朝廷的命运,天下的命运,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改变,但某个人某件事却切切实实是积重难返的拐点。
“朝廷这艘船,东南西北都有妖风怪浪在推。最后去哪里,得看角力的结果。”雪信说。“你却说得好像凭我一人意志就决定得了什么似的。”
旋即她领悟,玄河在这场风波中所得到的,不止是她许诺给他的陪伴。
太子继位,东宫幕僚皆成新贵,玄河这过去的太子宾客如今也是新皇身边最亲近的人。在太上皇那一朝,玄河只是有能力影响天子,而至新君一朝,若玄河愿意,他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变成天子的所思所想。新君心思单纯,又信任这些过去的玩伴,控制他,是雪信也做得到的事,对玄河而言,新一朝的朝政大局已在他手中了。
雪信叹了口气,不是她到现在才想通,是早先还是不愿把世事揣摩得如此灰败。玄河是为她动了心,却也不妨碍他做些别的打算。他本是站得离雪信、离权力最近的人,一旦他下决心去争,机会也比别人多。
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服从你也是好的。忍辱负重的高承钧成了反贼,谦谦君子的玄河成了权臣,而那个最应该坐收渔利的人此刻却带着一身伤远离了安城,跑去南诏寻草了。也不知远在华城的那位阴谋家,会做出什么表情。
“我的那位表弟,你要照顾好他。”
“自然,那也是太上皇的托付。”玄河答应得很快,“新君问起过你,下旨解除了对你的圈禁。等你真正从沉香山子里走出来,你也要担起辅佐新君之责。”
这话倒令雪信意外:“我还有走出沉香山子之日吗?”
“新君已遣使南诏取瑶香草。待海内安定,新草成活,就是你从地下走出来的时候。”
话初听来顺理成章,可在雪信心中莫名翻了一下。她问:“苍海心不是已经去了吗?”
“路遥伤重,途中多寇匪,恐回不来。”玄河没有拐弯抹角。
“海内安定,又是怎么个安定?”
“回纥葛逻禄退兵臣服,突厥吐蕃与新朝通书建交,河东侯平定安西,高承钧死。”玄河缓缓吐出这句话,雪信为换高承钧与锦书的生路,连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不要,也只有高承钧死,他才安心。
玄河等着雪信目眦欲裂地与他争执。雪信只是又笑了一回。过去她以为只有她精于算计,旁人都是傻子,如今看来,她才是傻子。
她拔出透山剑在泡桐树身刻下一道新痕,数给他看:“又该出去了。”
“记得回来。”玄河也那么云淡风轻地嘱咐她,笃定了一炉篆香的光阴,她什么也改变不了。
蝶群飞起,化作金雕直向南诏而去。
雪信望见苍海心牵马走进了一个寨子,向迎面撞上的第一个人打听什么,显然是言语不通,两人比比划划鸡同鸭讲。
苍海心捡了块有尖棱的石头,在泥土地上画出一株草的模样,又掏出一袋矿盐在蛮人寨民眼前晃。要么是苍海心画得太糟糕,要么是瑶香草在南诏也是秘密,寨民解下背篓,倒出一堆新采的草药,让苍海心挑选。
苍海心仔细翻检,显然是没有他要找的,临去又转回来,抓了一把草药嚼烂了塞进衣服里涂抹伤口,顺手把盐袋扔给寨民。
金雕又看见,在苍海心所在寨子的西南方不远处,搭起了一个临时营地。
有一顶帐篷外,垒着三块石头搭成的简陋灶台,底下生火,吊罐里煮着浓茶。围在火边喝茶的尽是耳戴银环的精悍战士,共二十人。水边还有人下河叉鱼。
南诏小圣女阿满换了身黑底绣边的短裙,挽着个竹篮,站在浅水里,捞起一把把青苔。捞满一篮,就提到岸上,岸上几个与她装束相若的小姑娘正在杀鱼烤鱼,顿时分出两个人来搓揉青苔。阿满不多时又捞了一篮来,这时先前那一篮青苔已被摊成了薄饼烤熟烤脆,她举起一张就咬,吃得香甜。
雪信走进阿满的眉心里,在梦中那小姑娘依然捧着青苔脆饼。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思洁净了,手里做着什么,心里就想着什么,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思绪。
雪信忍不住问:“青苔好吃吗?”
“当然好吃啊。”阿满撕扯咀嚼青苔饼的声音像只吃草的小动物所发出的,悉悉索索也是美妙。她这才回过神来,“天神又来看阿满了!天神要不要来一张?”她在身边的竹筐里挑选,找到了一张摊得最大最圆、没有破洞的青苔饼递过去。
雪信顺手接了,又放回竹筐里去,问:“你们可是去迎接安城使者的?”
阿满边吃边回答:“正是。上回天神来看阿满,阿满把天神所说的告诉了大祭司,大祭司禀告了大王,大王命令组成使团,护送瑶香草种子到安城,向安城里的新天子表达敬意。”
阿满用一只手摸了摸胸前的红棉绳,挂绳末端连着一个彩丝刺绣的小荷包,瑶香草种子就在其中。
可是雪信十天前,并没有向阿满提起过安城里换了天子的事,向新天子表达敬意,才是使团的真正目的吧。
雪信说:“你可以告诉大家,使者已到了。”
“可是大祭司告诉大家,如此再走一个月,我们会在剑南关与来接我们的安城使者相遇。”阿满又困惑了,“大祭司说今日我们会遇到来南诏偷东西的贼。到底是大祭司说的对,还是天神说的对?”
玄河口中那句“路遥伤重,途中多寇匪,恐回不来”果然有深意。今日玄河把这句话透给她,也恰恰是今日苍海心会遇到南诏使团。
雪信惶急:“阿满,我要借你的眼睛看一看,借你的嘴说些话,你睡一会儿吧。”还不等小姑娘明白她的意思,她一巴掌拍在对方脑瓜上。
梦境之外,苍海心已奔马到了南诏使团临时营地前,见使团众人打扮整齐划一,不似前头遇到的几拨生蛮,当即决定去试试有没有能说上话的。
他跳下马,清了清嗓子,先用安城官话道了声:“诸位吃着哪?”
火堆边的众人齐齐向他望过来,却没有一个人应声,也无人起身。
倒是他自己中气十足的吼声把胸口的伤又震开了,苍海心伸手按住绷带,换了华城口音说:“有没有人听得懂哪?”
火堆边一名南诏战士从随身竹筒里取出一个纸卷展开,向纸上看看,又向苍海心望去。纸卷轻柔韧腻,不是南诏所造土纸。
苍海心向他们走过去,歪头看了看,又改成他年幼时在长白山中学的鄂族话说:“你们手里那是我的画像吧?虽画得不如我本人魁伟雄壮,也瞧得出是我。对了,应该是皇上传书给南诏大王,让你们来接应的。”
他不客气,倒了碗浓茶刚喝了一口就烫到了舌头,只能放下,又用安城官话:“官书也没我跑得快,我的画像还能跑在我前面?”又用华城话,“书信与画像用信鸽传不就比我快了吗?”他又改用鄂族土语,“天儿聊不下去了。”又换回安城官话,“你们就没带个懂安城话的通译?”
他叽叽咕咕,来回切换语言,才把眼前诡异的境遇解释通了,又瞟见火边的二十来个汉子没声没息地把一只手探到身后。这些人俱在腰侧挂一把环首短刀,背后腰带中斜插一把长刀。
苍海心端起茶碗唏哩呼噜地吹气,悄摸摸地把脚尖向篝火凑了凑,一旦对方长刀削来,他打算踹翻了茶罐烫他们一脸再说。
“苍海心,这些人要杀你,你还不走?”
是清亮清亮的小姑娘的声音,咬字吐音无可挑剔的安城官话。
一个打着赤脚、长发高高盘起卷在脑后的小姑娘从河滩边跑来,眼神如同小鹿,细如米粒的粉蓝色小野花被她编成小花环,穿在耳垂上。
“怎么也要打一下,打不过再跑。”苍海心顺口回答,眼光瞥向已跑至近前的小姑娘,耳朵却关注着二十把长刀最轻微的声息。 听香录(全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