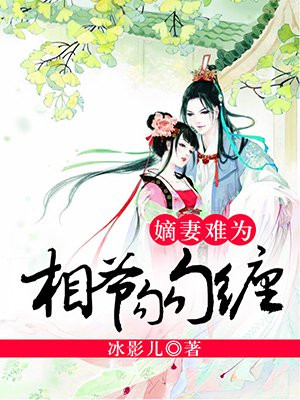第十五章 眠里犹问昼间事
第十五章
眠里犹问昼间事
当夜,高献之来到怀梦居,后园的陈设又变了。
花房里亮了灯,在蔷薇花盆与重重画屏之间的空白处摆放了多株铜灯树,树杈布满灯盏,高者几乎与琉璃顶相接,低者离地不盈寸。密布一周,只留下一个缺口,成了一面灯围屏。
由外观之,整个花房如一盏硕大无朋的琉璃走马灯,流彩自内溢出,徐徐转动,照彻整个花园。花房外十二根灯杆灭了灯,灯杆下,各立着一名侍卫,手按佩刀。花房里的灯光从他们的银白盔甲上依次扫过去,将他们染花。
雪信依旧穿着那身墨蓝银缂织的裙子立在花房门前,灯光洒在她静止不动的身上,被底色深重的裙衫吸了进去,只能沿着她身体的轮廓打一圈晕影。站远了看,她与侍卫们都好像琉璃灯旁的绢人。
伊斯克亚抢步上前,佩刀拔出了一半,高献之喝住他,让他回来,走在自己身后,别大惊小怪堕了自己的威风。高献之到底是血战沙场的统帅,这么点人的小阵仗吓不住他,他昂首挺胸走在前头,穿过侍卫们把守的灯杆圈,走到花房门前。
离近了,雪信还是不动,僵着脸,嘴唇嘟得能挂个油瓶上去,分明是摆了张臭脸给高献之看。
“郡主今日的布置可又是什么新鲜花样?”明明心里暗自捏着冷汗,高献之却故意说得轻松从容。
“没有新花样。我点那么多灯,调那么多人,是叫人看着我的花房。”雪信甩头进了门。
高献之不解其意,只是看雪信使小性子,也不像是会一声令下乱刃加身,于是伸长脖子跟进去,看她为什么发作。伊斯克亚不敢落后,紧紧跟上。高献之对他做了个手势,他会意,立刻选了株铜灯树,拔出银刀伸进灯盏中蘸起灯油来嗅嗅,并无异味,再观看刀尖也无变色。又高高低低换了几个灯盏,都没看出什么来。
雪信瞧着伊斯克亚检查灯油,冷笑一声,鞋尖从裙下探出来,点点地上一个碎花盆,开始告状:“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这案子可难破了。我日落前后来花房照料蔷薇花,就看见花盆被踢翻了一个,还看见一个满身油腻的厨子蹲在澡盆里头刷盆壁。我真是要疯了,这花房我花了多少心思高节度使不是不知道,怎么能让如此粗鄙的人进来!他又臭又脏,做事也粗手笨脚,一进来就弄坏东西,我真是要疯了!”
高献之听得云里雾里,还没理出头绪,伊斯克亚那张比羊奶还白的脸倒是瞬间变成了纸样白,白里还带着透明。他丢下灯树跑来低头认错:“是我一时忙不过来,让王大郎送完菜,顺手把澡盆刷一刷。”
雪信挑眉看着伊斯克亚,大有深意,却没有把话讲下去。
“郡主早有言在先,闲杂人等越少越好。你居然犯懒耍滑,把密道之事泄露给一个厨子?”高献之言语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
“接下来,大概高家那些挑水的、喂马的、生火的、打更的,都要由密道来到我的怀梦居了,任何人都能闲逛我的花园,到花房里来走一圈。”
伊斯克亚双腿膝盖一弯,立刻跪下了,口中迭声说:“不敢不敢,再不会有闲杂人等过来了。”
“既然是伊斯克亚犯错,冒犯了郡主,那处罚便由郡主定吧。”高献之摆摆手,把伊斯克亚的小命送到雪信手里。
雪信作势思考,伊斯克亚满心怨恨,也不得不强忍下去,抬头眼巴巴地看着雪信,随时准备为自己求情。
“这一次就算了,如果有下次,高节度使干脆换个贴身伺候的干儿子,让伊斯克亚去军中做个最末等的军卒。”雪信说。
最末等的军卒,甲不坚兵不利,连坐骑也没有,没有特别关照,乌泱乌泱一大群冲上去投入混战,太容易被捅死了。雪信要伊斯克亚死,不用她动手,甚至连个“杀”字也不用说,只消找个错处推他一把。
高献之却认为雪信处置得潦草,不过瘾:“你也不说打他一顿,杀了厨子?”
“算算伊斯克亚既要做高节度使的贴身亲随,还要安排厨子做饭,送酒菜过来,刷澡盆提羊奶生炭火……这些活儿从嘴里说出来都要喘口气。我姑且就饶了他这回的忙不过来。再说那厨子,我早听说他做的菜色合高节度使的口味,我要说杀了他,高节度使恐怕也舍不得。既然他已经知道密道,就让他替伊斯克亚做些忙不过来的活儿吧,但不准他踏入花园,更不准进入花房。再有犯的,那我就喊打喊杀了。”雪信看也不看伊斯克亚。
“难得郡主体恤他们。”高献之听出雪信是卖了他面子,还挺感动。他心思不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那请郡主撤了外头那些人吧。”在里面看不清那些手按佩刀的侍卫们,但只要想一想他们还在外面,随时有冲进来的可能,他心里还是发毛。
“我爱清静,若能保证我的清静,我也不想弄一群人时刻围着。”雪信走到铜灯树下,依次扳动机括,盏中灯芯缩入盏底,灯树一株接着一株熄灭。骤然间,花房中漆黑一团,高献之眼底还残留着灯墙的反色影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听见雪信说,“请高节度使准备浸浴。”然后衣裙簌簌,她走了出去。
花房外,一圈灯笼同时亮起,灯杆下银盔的侍卫们如一列松开猎物的长蛇,盘旋着追随着雪信游开去了。
回到后堂,雪信坐着出了片刻神,刚把绣绷子捧起来,侍卫队长到了门外汇报:“巡夜的弟兄在花园外墙上捉住了那位,拖到堂前院子里了。”他也不知今日要如何称呼,打了个愣,含混指代。
雪信扔下绣活托起下巴:“怎么会呢,那位身手不差,你们河东侯撵着他打都不容易,怎么让你们逮住了?”
“全赖那位不把我们当外人,骑在墙头向弟兄们打听今夜布置的底细,又问起今日晚饭郡主吃了什么。诓他下来他就下来,把他擒住他兀自以为弟兄们在与他逗趣,告诉他们绳子这么捆捆不住他必须那么捆那么系扣。”队长说着说着,吭吭吭憋了一肚子的笑,又请示,“郡主要如何处置?”
雪信顺着队长的讲述想了想苍海心那德性,也笑了,说:“找个麻袋套了,吊到你们营房梁上,天不亮别放他下来。”说到这儿她先叹了口气,“他什么时候能对别人多点提防。”
“今夜以后,怕是再也不好拿住了。”队长说。
队长带人去处置苍海心,伊斯克亚又来了,依旧是高献之有请。
“有没有办法让我回到昨晚那个梦里?”不等雪信穿过画屏,高献之就迫不及待地问。
已经躺进羊奶里的高献之,再也不花心思琢磨怎么把雪信哄到澡盆边了。
雪信本是另一份执念的替代,太久太远太没可能太绝望,才退而求其次,输了也要抓个慰问品在手里,显得没那么惨。当他的绝望遇到一丝活气,枯萎的执念苏醒过来,替代品就看不上了。
雪信不再是他的目标,但他还缺不得她。
“高节度使说的哪门子话,梦境缥缈,可遇不可求。”雪信说。
“你一定做得到。你一定要做到!我要回到那个梦里去,再看她一眼。”高献之神情狂热。
“回到梦中的关键在高节度使不在我。若一丝不差复原昨夜入梦前的情形,或许能得个相似的梦。”雪信说。
“那快去复原昨夜的情形,一丝不差。”高献之除了雪信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救命稻草。
伊斯克亚首先被高献之赶出花房,只不过高献之再没有说“天亮之前不用回来”的话,雪信那些侍卫雄赳赳的样子还令他心有余悸,他令伊斯克亚在花房外巡守。伊斯克亚倒了霉,天寒地冻,弓腰缩背,沿着灯杆外侧一圈圈走。
花奴穿着铃铛舞袍踏上花房外的响屐道。雪信盯着画屏上交错的影子,有屏上本来绘就的山河,铜灯树没有树叶,灯盏皆铸成玉兰花形,投下的影子是千树繁花,花奴在花房外旋舞不歇,影子接地连天。一重叠一重,一道压一道的影子。她拔下银柳簪,从袖中取出小鼓,双腕齐颤。
高献之记得昨天夜里他还吃了肉,喝了酒,于是也不管什么滋味,尽往口中填去,不一会儿肚皮鼓胀,抬手渐渐迟缓,手抓不稳玛瑙杯滑进澡盆里,银刀也掉在地上。酒杯落水,银刀落地,额外的响声搅乱了铃鼓的节律,高献之仿佛突然惊醒了一下,想要弄明白自己在何处,但很快忘记了这个疑问。
他听见了雨声打在船篷,亭角风铃轻动。他爬出船舱张望,见到了江岸边的亭子里,背对他坐着一个名蓝衣少女。他手舞足蹈,张口狂呼,几乎吐不出有意义的话来,只是“嗬嗬嗬”“喂喂喂”。
少女转过身来了,他当然认得她,虽还是失语叫不出她的名字,但他高兴得像个还没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需求的小娃娃,在船头蹦跳。
她的模样一点没变,还是离开他时,他记得的样子,连脸上冷静的神色也没变。她对他招了招手,这一招手,他喜极反而呆住。她叫他呢,叫他呢,叫他呢!
她一招手,江水止住了奔涌,船随之停驻。可是他不会水,也不会弄船,要怎么把船靠过去呢。他在船上找,找到了一只铁锚,用力掷向岸边。蓝衣少女抱住铁锚,把它钩在了亭栏上。成了,他扯动锚链,将船扯向岸边,不及船靠稳,跳进齐膝深的江水里,跑向她。
跑到她面前时,他的下半截已被江水浸透、上半截已被雨水和汗水浇透了。少女看着他滑稽的模样,“扑哧”一声笑了。
她一笑他就会说话了,叫了一声:“锦书。”
雪信从花房里出来,月还未至中天。她摆摆手,花奴停止了舞蹈,小跑着回后堂休息烤火。雪信经过伊斯克亚身边时说:“高节度使已安睡,你要不要去后堂暖和暖和,吃点东西?”
伊斯克亚刚被她饶过,生怕又被抓到什么错,正色道:“义父在这里,不能没有人侍奉。”
雪信点点头,赞许他:“忠心可嘉,好好侍奉。”
不待雪信走远,伊斯克亚一头钻进了花房,先不说忠心不忠心,花房里温暖如春,随便找个角落倚着就能睡着,比在外头吹风溜达强太多。
今夜收工比预计的要早,雪信长出一口气,心头计较的是就寝前要不要吃些什么,这么个不早不晚的时候,不吃会饿,吃了又会撑。她心念一动,脚下却朝着花园后门处值夜侍卫的营房去了。
队长被值守营房的侍卫叫起来,打着哈欠来见雪信。
雪信问:“那位如何了?”
队长说:“已经把他套袋吊上房梁,我亲自看守着。他悬在半空还拉着我聊天,聊着聊着打起了呼噜,我也冲了盹。不过,郡主召末将,末将出来前检查过,他还睡着。”
“带我去看看。”雪信说。
“郡主不是说天亮以前不放他下来吗?”队长担忧,“还没到夜半,放出来可就塞不回去了。”
“谁说我一定放他下来看?你不觉得隔着麻袋拿棍子捅他几下很好玩吗?”雪信笑了,眼中闪闪发亮。
队长觉得郡主此刻就像一个乡下皮孩子,抓了稀奇虫子,怕它跑了就编个草笼子关起来,虫子在笼子里不动了,又担心虫子死了,用草棍去戳。
他领雪信进他的舍间,见梁上悬着一条空麻袋,忙奔上前细看,麻袋中部被利刃破了条大口子,逃脱得那叫一个干净,身上零零碎碎没有落在袋子里的。
队长急汗下来了,诚惶诚恐拜倒:“末将这就召集弟兄全宅搜捕。”
“不用了,反正他也做不出坏事来。把花房守好,别让他混进去就是。”雪信倒没多大惊怒。他能逃脱是再正常不过的,逃不了她才看不起。
到底还是没有加餐,回到卧房,婢女已熏暖了被子,铺妥了床,垂下帐帘。雪信打水卸妆,又匀上一层夜容粉,拆散簪环,换了双红绫绣面软底鞋,脚踩塌鞋跟,趿拉着进了帐帘,然后从枕下摸出玉盒,向帐中熏球投入新香。
她坐在床沿,双脚垂在脚凳上,围屏两扇小门要关不关,叫了一声:“白儿。”
白儿不在窝里团成一个球睡着,叫一声也不见它颠儿颠儿跑过来。
雪信又叫了两声,依旧没动静,不由捶了下床板,怒道:“你钻床下也就算了,但别捂臭了我的白儿,快把它放出来。”
床下有了悉悉索索的响动,有人回答:“我没捂它,是它自己不愿应你。”
“到底是谁养的狗?”雪信又捶了下床板。
“我给它吃的,比你喂它吃的好吃。”苍海心在床下说,伴着一堆小狗不情不愿的哼哼,似乎他又努力把狗往外推,而白儿僵住了不肯挪窝。
“你躲哪儿不好非要躲我床下?你在床下臭气就会往上跑,今天茴香气味尤其冲,熏臭了我的床我还怎么睡。”
“不能的,床板厚密,我的气味透不上来,要熏也是你熏我,你白檀床板快把我的鼻子熏坏了。”
“那你还不从床底下爬出来?”
“我不爬出来,你还能叫人来你床底下捉我?”苍海心吃一亏长一智,一夜之间智谋又突飞猛进。
雪信还真没这个厚脸皮让侍卫冲进屋子从床底下拖男人。她收起腿,合了围屏两扇门,倒在枕上。她对付高献之,主意笃定,计划周详,步步为营,容不得别人扰乱。但她一个人制定计划,调派差遣,终于得来了至关重要的进展,她不能让人看出她的得意,可所有人都不知道她高兴以及为什么高兴。
“什么时候天才能真正暖和起来,山青水绿。”她叹息,抬手抚摸漆屏上平嵌的螺钿山水,“但愿回去时赶得上吃第一茬最鲜嫩的秋葵。”
也许是床底下的处境与躺在船舱相似,苍海心想起前一夜高献之梦见船篷顶壁有诗,他满腹好奇:“老高果真躺在澡盆里便好似去了小蓬莱?”
“小蓬莱有什么稀奇,人人去得。有仙根道骨的活着去,凡夫俗子死了去。”雪信冷笑三声,露了杀意。
“那‘万迭红芳一旦开’,也不是吉兆咯?”
“日中而昃,月盈则亏。花开盛极,锦绣繁华,泰极否来。”
“一个梦正说反说都是你在说,到底有没有准?是凶还是吉?”
“梦可分九种,一曰气盛,二曰气虚,三曰邪寓,四曰体滞,五曰情溢,六曰直叶,七曰比象,八曰反极,九曰厉妖。到底是哪一种,梦由心生,事在人为。”
“你既那么厉害,早些使出手段,你那侯爷爹也不必猫外头去了。他天天不放心,天天让大毛带字条给我,让我汇报你一日三顿吃的什么,几更安歇。他还放出话来,临去前他是找了大秤称过你的,等他回来二次过秤,少了几斤,就割我几斤肉下来。”苍海心抽抽鼻子,“我又没气你,要割也去割高承钧的啊!”
雪信在瑟瑟枕上轻掠乌发,把压在脖子与枕面间的碎发挑出来。她确实曾经束手无策,走投无路,若不是真真被逼到绝境,高献之又怎么会相信她已经屈服呢?况且,在苍海心失踪后重新冒出来前,她还使不出这样的手段。
沈先生是教过她的,然后又用诡异的方法叫她暂时想不起这本事。什么时候能想起来,掌握在沈先生手里。她走不到那样的境地,也就用不上这番本领。苍海心出现在龟兹,摇一摇拨浪鼓,念上一段神叨叨的止小儿夜啼咒,锁着她这番本领的柜子轰然打开,她取到了沈先生早就为她准备好的新玩具。
阴诡之法,都是正面实力不敌,又非要取胜不可,才被琢磨出来的。
这么说,沈先生这一回与皇上同仇敌忾了,两人一心要干掉高献之。皇上派来了河东侯与长平郡主,沈先生特意安排苍海心来分一杯羹。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苍海心除了在高家放一把火,给雪信传个咒,调查调查酒肆的毒药酒,替河东侯照管郡主吃喝,剩下就是尽职尽守地在高家伙房做饭,没做什么有用的大事。
苍海心听雪信不说话,只是在床上翻身,敲敲床板说:“我前几天也做了个怪梦。梦见我左边耳朵上戴了只玉耳环,一碰就掉玉渣。我寻思了好几天,我是不是要变女人了?毕竟只有女人才戴耳环,戴的还是破耳环,这霉头触的。”
雪信思忖了会儿,才说:“君子左耳为郡,玉去一点为王,看来此行必能大捷,说不定回去会被封个郡王做做。”
苍海心哼哼:“你不是骗我?你对高献之也说吉兆,背地里却说他要死。”
“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都是反解。”她说,“你来此地的任务是寻机建功,不是做我爹的眼线,不是给我包饺子的。”
“寻机建功?我这就去一刀捅了澡盆里的老贼,你让吗?”
“还不是时候。就算有这一刀,我也要留给我爹捅。”雪信怂了,“你还是当好你的厨子,回安城后,我爹会把你夸得跟花儿一样。”
睡意上来了,她不再说话,也听不分明苍海心叨叨咕咕又讲了什么,也不在乎他躲在她床下要躲到什么时候了,反正他愿意待在床下,就不会跑花房去捣乱了。
翌日巳时,高承钧来了。守在正门口的侍卫说去通报,高承钧认为自己没有立在门前恭候通传的必要,一脚踏进宅子。那侍卫由速去通禀成了头前领路。毕竟高承钧是未来的郡马,这事已经由皇上说了算,高承钧就是他们半个主人,侍卫们都不敢强硬。
正堂四壁垂下厚厚的帘幕,隔绝外头的喧嚷和寒冷。帘子不是粗砺的毛毡,是轻若无物的蚕丝,吹一口气就能飘起来的绡纱,一重复一重,也不知叠了多少重,劲风刺进门缝,弹在纱幕,如急雨落在湖面,波纹起伏不已,却打不破掀不开。
花奴着了一件浑身是铃铛的宽大袍子,在练舞台上旋转腾挪。主位坐北朝南,摆了张便榻,雪信侧歪在榻上,像是睡着了,一只腕子垂在榻边,手指随着铃铛与踏步声一起一落,活似只好吃懒做的猫,一早起来,也不过换个地方睡,却也不会结结实实睡着,耳朵始终倾听着附近的动静,尾巴惬意地拍着地。
侍卫也不知道郡主这算是在听舞,还是睡觉,踟蹰着不敢上前。高承钧摆摆手,示意他出去。侍卫如蒙大赦,赶忙放轻了步子溜出去了。
雪信的手指头停住了,睁开眼,看向花奴。因为高承钧忽然闯进来,花奴愕然间踏错了一步,被雪信捉住了。花奴忙行礼认错,从头来过。
高承钧已经走到雪信面前,她视若无睹,又安然闭上了眼睛。他们都习惯了,历来都是吵架了高承钧先低头的,不管他是否知错认错改错,他总是会先低头来哄她的。不是他的错他要承担,是他的错更要承担。只要他先低头,事情总是容易协商解决的。
高承钧从怀里掏出一只鸽蛋大小的金盒,握住她那只打拍子的手,把盒子塞进手心里。雪信闭眼掂了掂,睁眼看,金盒盒盖上铁线阴刻宝相花,打开盒子,一汪浅草色,舔湿了无名指在草色上一擦,一抹娇红漾开来,正是她满城寻找过的那种叫做翠金娇的胭脂。盖好盒盖,她在高承钧的脸上蹭掉了指头上沾的胭脂,细声说:“龟兹城里不是买不到吗?”
“我写信给安城的朋友,让他们给我捎来的。”高承钧把脚凳拉过来,挨着床头坐了,正是可以伏着榻沿说话的高低。
“有这么快?要有这么快,你早该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赚零花了。”雪信已经满意高承钧的求和了,盘问揶揄也是在享受她的胜利。
“信去物来,是夹带在驿马传送的塘报文书中送来的。”高承钧说。
“那么说,你已经在替你父亲处理塘报文书了?”雪信在他淡淡的解释里抓住了头绪,扬起头来。她关注这个消息,甚于金盒胭脂。
“有些繁琐的杂事不值得父亲劳神,父亲就交给我处置了。”高承钧回答。
他们都没有把话讲到十分满,顶多只讲了三分,都在防备,也在蓄谋。
“你脸色不好,人也瘦了。”高承钧握住她那只手,虽然身子被重重衣服裹着,脸也没有给他正脸,从一只手的骨肉上他就感受出了她的清减。
雪信抽回手,忽然就想起苍海心说的玩笑:“你真心疼我啊,那我少了几斤,你就剁几斤下来赔我。”
“你一个人住在外边,吃不好,睡不好,我不放心……”
高承钧话还未说完就被雪信打断了。
雪信坐起来,把金盒在手里抛着:“要我吃得好睡得好,要我搬回高家去,你得先把高家打扫打扫干净。”
“葛逻禄与别的部落因地盘起了争执。”高承钧碰了壁,兀自另起话头。
两人说话轻声,还是被堂上另外一个人听去了。花奴是葛逻禄来的,关心则乱,一听就错了舞步,干脆停住等着听下文。
“父亲命我去裁断调解。不会有危险,你要不要随我出去散散心?”
葛逻禄是个好地方,上一回在桑晴晴的婚礼上他们就很开心。
“这种出风头立威信的俏事,他都懒得自己去了?”雪信关注的还是另外一面。
“随我去吧。”高承钧又说了一遍。也许是在他人生又一个重要关头,他需要她看着。也许是这样一个弥合裂缝的好机会,错过可惜。
雪信对着他抿嘴一笑,可眼里根本没有笑影。如果她这头没有高献之要料理,她也愿意去的。可是如果她这头困不住高献之,高承钧又哪里有机会去草原部落中建立他的声威。她是走不开的。
“车马劳顿,我不想去,让秀奴随你去吧。”
高承钧眼里的热切凉了下来,他盯着雪信,好一会儿才说:“即便你不愿受旅途颠簸,也不要做画蛇添足的安排。”
“不错,我是画蛇添足。秀奴是葛逻禄的女儿,这种事她怎么可能不回去。”
两人的对峙刚刚和缓,又杠上了。雪信也弄不清自己说的最后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要留下继续对付高献之,秀奴回去协助桑晴晴处理部落间的纠纷,如此清晰明了,各有各的使命,有什么好不满?把秀奴留给高承钧,也是她的决定,凭什么又难受起来?
他们的对话间开始填入大片大片沉默,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像坠上了巨石,沉入湖底,不见天日。
“你既不放心,为什么不随我去?”高承钧说。
雪信闭了闭眼睛,终于长长地叹息:“草原的事归秀奴,朝廷的事归我。”
部落纠纷是草原的事,而换掉高献之,是朝廷要做的事。要去旧,也要立新。
“那你的安排是为了朝廷,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
“恰好可以为了朝廷,为了你,也为我自己。一举三得。”
这一回,她把他们两个人都难住了。无论高承钧听她的,还是不听她的,无论他怎么做,她都不会满意。
高献之过了午就来了,躺在澡盆里,向雪信问起高承钧:“那不成器的东西今日也过来了?”
“他向我抱怨近来日子辛苦,又见不着我,要我搬回高家去。我说我正自在快活,不回去。”雪信随口扯谎。
高献之急急道:“不回去,不能回去!我昨夜又梦见锦书了,我已经上岸到她面前了。现在她在亭子里等我呢,我还要回到梦里去。”所以他今日早早来了,连半天也等不了。
雪信垂首:“要回到那个梦里,必然是要重复前一晚与前前晚做过的事。可如今天光还大亮,花奴作不了影舞。梦是心头想,想是虚妄,高节度使还是多眷顾眼前为好。”
此刻的高献之怎么听得进去,雪信越是推脱,他越是坚定。眼前还有什么好眷顾的,西域三十六国臣服了,美酒佳肴吃腻了,美得千姿百态的女人睡起来其实一个样,还有个小狼崽子已经长大让他日夜如芒在背。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已别无所求。没有尽善尽美,哪怕拥有许多许多,也会遭遇遗憾,而这遗世独立的针尖特别扎,比针毡扎多了。一针戳下去,就成了世上唯一的最大的痛楚。
清醒着等待重生太漫长了,万一那只是雪信的缓兵之计呢?就算不是骗他,他有了与心上人匹配的皮囊,万一她还是拒绝他呢?在大家都青春正盛的时候,她不是拒绝他就是骗他,从他手里跑了一回又一回。有机会重来一次,大概她还是会拒绝他、骗他、坑他吧。在他清醒着的眼前,他无时不忐忑。虚妄是抵达梦想的捷径,躲过了患得患失的煎熬,也不怕失败。他的梦境是他说了算的,怎么可能失败。
“高承钧今日出发去葛逻禄部落解决纠纷,若你不能立刻让我回到那个梦里见到锦书,我就派人把他追回,换伊斯克亚去。”高献之还没有糊涂。他料得到雪信努力部署所为何来。但是这笔交易他不亏,他愿意拿自己所有的和他厌倦的去换未曾得到过的。
澡盆边,伊斯克亚低头斟酒布菜,听见自己的名字被提起也不抬头。
“我尽力而为。”雪信看向伊斯克亚。
伊斯克亚识趣,向高献之报告:“我去花房外巡守。”他还有那么点儿期待雪信这回办砸了,那么高献之会不会让他取代高承钧,处理部落纠纷事宜呢?
不消雪信发话,高献之开始大饮大嚼。因为喝得太快,酒液自嘴角漏下,滑入他置身的羊奶中。雪信取了发簪与小鼓在手,说:“请高节度使闭上眼睛,不用紧紧闭合,眼珠上翻,眼皮留一线,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即可。”
高献之依言而行,白日天光穿过徐徐转动的琉璃壁,五色斑斓掠过他的眼皮。
鼓铃悠悠,好似由天外落下,眼皮前浮起了旋转舞动的巨大黑影。那样的舞蹈过目即难忘,只要听见鼓铃催动,闭上眼几乎原生原样出现在面前。窸窸窣窣的雨丝打在窗纸上,激得檐下的铜铃被风催动。斜风急雨,沉沉夜,曳曳烛。
满室灯火,他的眼前一个红衣身影在走动,取下红绸灯罩吹灭一支支蜡烛。每一支蜡烛熄灭,屋子里的幽暗就浓重一分。窗外有人打更,屋里女子行动间,髻边珠钗金流苏簌簌摇动,腕子上三个绞丝金镯撞来撞去,裙带末端垂下黄金铃一步一惊,琐琐碎碎的细微脆响如影相伴。
“不要灭灯。”他低低地说,声音有气无力。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床帐中。
女子回过身来:“我不喜欢太亮。”她款款走到他床前,“那些客人也太讨厌了,狠命灌了你许多酒,你横倒了他们才满意。”
“锦书……”他使劲回想她的话,回想被灌酒的情形,似乎模模糊糊有记忆,又不确定,他又问,“我们是在哪儿?”
“你是醉糊涂了吧?成亲的日子忘了自己在成亲。”锦书把他从枕上扶起来,让他斜倚在床围,又扯过一床新被子垫在他背后。
她走到房门口,从婢女手里接过一只小碗,稳着步子走回来坐到他身边,低头在碗沿边吹了吹。
“太酸了。”他闻着碗中酸气扑鼻,要躲闪。
“酸才解酒,我亲手煎的醒酒汤,你不喝?”锦书眼波一横。
“我喝我喝。”他捧过碗,一气喝了,还是发呆,“我是在梦中吧?不然你怎么会嫁给我?”
锦书接回了碗没好气道:“以后见到你那群将官,先不问情由打他们每人三军棍再说,都把你灌傻了,说起混账话。你是在梦中,那你快掐自己胳膊,快些醒了罢。”
“我不醒我不醒!”高献之生怕锦书把他推出梦境,吓得甚至往床里缩了缩。他又说,“只是我从没见你如此对待我,还不习惯罢了。”
锦书召婢女来取走了空碗,她双手轻拍脸颊,犯疑道:“我以前是怎么对待你的?”
“你对我很生分,我能给你的你都不喜欢,我的礼物你不想收下也不愿意回馈。我很怕你突然对我热情起来,你一笑,不是骗我离开我,就是有事相求。等我做完了,你又会骗我离开我。”高献之说。
“那你就愿意我整日冷冰冰地对待你?”锦书歪着脑袋说。
“不不不。我希望你对我好,是你愿意对我好。我能为你做任何事,也不用你虚与委蛇交换。”
“此情此境,固君所愿?”
“让我照照镜子。”高献之突然想到一件事。
锦书取了妆台铜镜来。新磨的镜面有种兵刃的锋芒感,一片昏黄中,高献之见到自己剑眉虎目,稚气新脱,少了威严,自有一股少年人的傲慢。好一个英武逼人的少年郎君,眼看着还有大把的余地,还能更英武逼人。
离开花房,月已西斜。从花房到后堂的一段路,不足百步,雪信脚步滞重,走走停停,歇了好几次。
苍海心坐花园墙头看了会儿,跳下来,跟在她身后说:“加把劲儿,后堂马上到了,我炖了参汤,做了蔷薇饼,坐下立马能吃。”
雪信回头瞪他,那眼神一瞬间打了个盘桓,是累得走不动后面半截路,想要他扶她一把背她回后堂去,可她是拒绝惯了苍海心的,宁可死了也不愿沾到他头发衣服上的荤腥味。
苍海心的眼光也踟蹰了下,放在以前,他可以二话不说,抱起她穿过整个宅子,她不用穿鞋,脚不沾地。但是如今不行,如今不管是论起表面的名分,还是私底下的情分,都没有他的份。她只要瞪一眼拒绝了,他也只好悻悻然陪着她一步一歇,小碎步踩蚂蚁。
“前两夜,花奴在花房外顶着寒风跳上大半个时辰,那是真累。以前在老家村子,看萨满神蹦蹦跳跳,那也是累。你不过在里头站一站,不过没吃一顿晚饭,就能累到虚脱?”苍海心见她苍白绵软的样子,起了疑心。
雪信说:“出发来龟兹前……我的底子就没养好,格外经不得累罢了。你以为站上五六个时辰,摆弄出别人指定的梦境,是件容易事?要心坚如铁,又要心细如发,是耗血化油,点那一盏灯。”
“你那身板能熬几两灯油?要不你教我,要不咱换个法子折腾老高?”
“船在江心,只能进不能退。”雪信又回头,“你不是那块料,学不会的。”
苍海心没再搭茬,因为雪信说上一句话,都要歇两次。他小跑开去,转眼工夫,带了两名侍卫回来。那两人抬了张简陋步辇,是两杆长枪绑在坐几腿上临时拼凑的。雪信坐上步辇,把气匀顺了,对侍卫说:“先把我送回后堂,再把这厨子送柴房里关到天亮。”
“我好歹是给你端汤送水的,你能对我慈爱些吗?就关在后堂行不行?”苍海心跟在步辇旁,为自己争取待遇。 听香录(全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