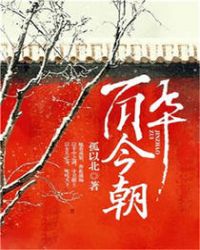长安又落了雪。
秦宜歌趴在窗边,她已经记不得这是入冬以来,长安下的第几场雪了。从刚开始的兴致勃勃,到如今的平淡乏味,她也不知为何会如此。
从下雪开始,她便没有陪她赏雪之人,她也一直看的是津津有味的,为何如今竟然觉得无趣。
难道是因为……长安城中再也没有了可以看雪之人吗?
她有些烦闷,可却不能纾解,只能一直闷在心中。
那种不愉的心神,似乎已经明目张胆的贴在了脸上。温月近身服侍的时候,手脚也不免的带上了几分慌乱。
秦宜歌清浅的转了眼神来,吓得温月的手脚一软,差点将手中的茶壶给摔下去。
秦宜歌见了,微微蹙眉:“你何时变得这般浮躁了?”
“奴婢见郡主心神好像有些恍惚。”温月不动声色的关切的问着。
因着温月那事也算是什么大事,秦宜歌也没有心思追究,也就让她打着马虎眼过去了。
不知何时,玉蝉也走了进来,她悄悄地拉了拉温月的衣角,便让她随着她去了屋中的比较僻静的一角。
温月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玉蝉,不太明白。
玉蝉浅浅一笑,附耳到温月的耳边悄声说道:“自从沈公子走后,郡主便一直都是这般状况。”
“主子曾经说过,郡主这是害了相思病。”说着,玉蝉还趴在温月的肩膀上笑了好一会儿后,才和温月重新走了回去,站在身边伺候着。
秦宜歌趴在桌子上神游了一下午,快到了晚膳的时候,温月才提议:“如今王妃也是一个人,不若郡主去和王妃一起用膳吧。”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自家郡主和王爷王妃的关系总是有些疏远。
比起世子来……温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总觉得好像打从她入府开始,除了必要的日子,几乎自家郡主都是一个人猫在院子中,哪也不去,就好像这个秦王府没有任何能让她牵挂的东西。
无由的,温月觉得自己心下一片慌乱。
也如她所料,秦宜歌听见后,懒洋洋的吱了一个声,也没说去不去。
她又不是真的秦宜歌,和这个名分上的亲娘,不知道隔阂了多少去。
而且最了解自己女儿的,也该是她这个做娘亲的才是,所以啊,她这个假冒的,还是能离多远是多远吧,免得到时候徒生枝节,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
又过了一会儿,温月咬了咬唇:“郡主是想在哪儿用膳?”
意料之中,那人懒洋洋的换了个姿势:“这儿吧。”
温月不敢反驳,只能应了声,然后退下,唤人去小厨房将饭菜端上来。
之后的日子平淡而无趣,就像是一碗白水,硬生生的让人尝不出半分滋味。
她也不知这事是好还是坏。
不过好在没多久,尹衡便回来了。
她呷了一口清茶,茶水有些苦还有些涩,她细细的抿了好一会儿,觉得不错,又喝了一口。
尹衡就站在她的边上。
重叠的光影里,他沉默的瞧着她。
有时候,他觉得他的这个主子,就像是寻常的闺阁中姑娘一般,只是比之寻常姑娘,面容又要生的好一会儿,坐在哪儿,就陡然生出了满庭华光,就像是屋子中有再名贵的物什,也压不下去她半分颜色。
可是又有些时候,他觉得她经历过生死,看过许许多多的荣辱浮沉,才有一般人都没有淡然薄凉。
他将带回来的消息递了过去。
“大秦出兵西泽,西泽不敌,东苏皇便向大燕求救,如今大燕的军队也已经快要临近泗水城了。”
秦宜歌弹了弹指,似乎对这个消息不太满意:“东苏皇了?”
“因为西泽朝中并无可用的武将,东苏皇便只能御驾亲征了,如今西泽是由周相和裴相两位把持着。”
“东苏皇对这两位还真是自信。”秦宜歌转了转手腕间的念珠,“对了,大秦出兵的这个消息,云止他们知道吗?”
“大概是不知道的,需要属下将这个消息放给他们吗?”
“放什么,瞒着。”秦宜歌笑,“能瞒多久,就给我瞒多久。”
“可是……”尹衡有些犹豫的看了秦宜歌一眼,心下是万分不解。
郡主,明明是大秦的郡主,怎么就见不得大秦好了,如果大燕的军队压境,大秦不曾知道,大抵大秦的城池都要被大燕占去几座。
别更多大燕与大秦仇视多年。
他虽然为大燕卖命,但说到底他却是大秦人氏,自然是不希望看见自己的故土,被人侵占。
“这事你就不必过问了,记得务必要密切关注战事和西泽的情况。”秦宜歌说着,没有克制住,悠悠然的笑了出来,“希望裴靳,不要让人失望才好。”
灯影覆薄衣。
平沧也是越发的冷了。
就算是有武功傍身,在冷清的书房中坐久了,裴靳还是觉得手脚都有些冰凉。
他揉了揉手,对着身边的小厮吩咐:“多加一个火盆吧。”
“是。”小厮领命而去,在屋子打开的一瞬,北风呼啸而至,而他面前的桌上的纸笺都吹飞了些许,他转身拿过东西镇住。
不知怎地,就想起了那双盈盈若水,温软多情的眸子。
他笑了笑,拿起笔蘸上了墨。
没多久,小厮便端着火盆进来,顿时屋子中就暖和了许些。
在小厮的身后,还跟着将卿,他的脸已经被北风吹得都有些僵硬了。
刚一进屋,他便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脸,尽量让自己的脸不要显得这么僵硬。
裴靳看了眼,语气淡漠:“何事?”
“这是近日来那位小郡主……”
不等将卿说完,裴靳便又重新将手中的笔搁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来:“拿来吧。”
将卿立马就屁颠屁颠的将信捧了上去:“这些日子,小郡主就出过一次门,遇见了单家的那位姑娘,那日小郡主的好像脾气不太好,明里暗里的将那位姑娘给挤兑了一遍。”
“像是她会做的事。”裴靳拿着信笺,还是在笑,“她从来都是个不肯吃亏的性子,如果不能当场报回去,那么等着暗里,还不知道要如何折腾人。”
“是啊,其实小郡主的这个性子挺好。”将卿决定睁眼说瞎话,反正主子爱听,这种话他说多少遍,他都乐意的要死。
“她性子可不算好。”裴靳可不会买她的帐,“她这个人,龟毛又记仇,而且啊,睚眦必报,手段狠辣,又凉薄无情的紧,她这样的性子,也只有你会觉得好。”
将卿听了,脸有些抽动:“既然这样,主子你干嘛还要喜欢她?”
“没办法,那丫头太会伪装了。”既然让他觉得,她就是他心里唯一的一道光,是他久居在深渊之中的光明,可后面才知,这些不过是她的伪装罢了。
她的心,可比他还要黑。
明明被捧在手心中长大的金枝玉叶,却不知为何会这般擅于攻心。
看完之后,他将信笺放在烛火之上烧了,没有留下半分痕迹来。
“长安那边,你们在多费一些心思,暗中好好地照顾她,别让她发现了。”
“是。”
在府中安静了一段时日,趁着雪停,秦宜歌便又带着侍女去了玲珑阁。
如今长安中,能与她说上话的,也只有玲珑阁中的那一位了。
秦宜歌捧着温酒一口一口的喝着,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正在算账的慕禅,等了一会儿觉得没甚意思,就伸手去扯了扯他的账本。
慕禅抬头,将账本扯了回来:“九霄他们没有离开之前,你是十天半个月不会来瞧我一次,如今他们走了,清净了,你倒是会来闹我了。”
“瞧你这话说得……”秦宜歌顿了顿,“像个女儿家,拈酸吃醋的。”
慕禅了然一笑,也不反驳只是道:“说吧,你如今来找我,应当不是只为了叙旧这般简单吧。”
“还是你机敏。”秦宜歌将酒杯放下,用手撑着头,瞧着她,“我总觉得这些日子,又人在暗中跟着我,可偏偏跟着我的暗卫,一个都没发现。”
听闻她的话,慕禅皱了皱眉,他家的这个主子,感觉准的可怕。
许是因为过往的事,她对她身边的人和事,向来是十分警醒的,如今她竟然这般说,想来这件事,必定是十拿九稳了。
“等会儿你回去的时候,我会暗中跟着你的。”慕禅说道,“不过他们跟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也说不下来,好像已经有一阵了,又好像是从裴靳离开长安之后。”秦宜歌对于身边出现的这种若有若无的试探,其实是不怎么关心的,只要不妨碍着她,对她没什么恶意,她也不会去管。
可是最近一阵,他们的试探却是越来越频繁了,她担心他们有什么动作,便趁着雪停来寻了慕禅。
慕禅拧眉,有些气恼的看着秦宜歌:“既然有一阵了,你为何现在才来找我?”
“前段时间累得很,不愿意搭理,如今可不行了。”秦宜歌半真半假的笑着。 醉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