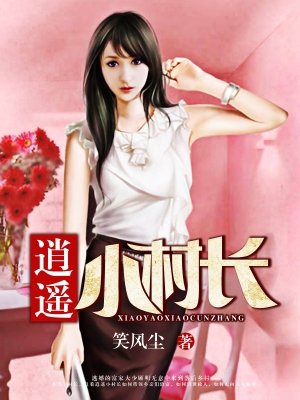阮东琳觉得周是故意的。
连领导都在她面前夸他,说,阮东琳啊,你这小姑娘挺能瞒事儿啊,有这么一个宠你的男朋友却从来不说。阮东琳被领导说得一懵,一句一个“好”的,倒是让她搞不清楚说的是谁了。
莫不是路远扬?
阮东琳这么猜着。
“你男朋友是混血儿吧,样貌真好看,说有多俊就有多俊,人高马大的!中文说得也很不错啊。现在像他这样,喝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乳汁,还愿意学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的ABC,着实不多了吧?”领导“呵呵”笑着,肚子上的肉都随着他的笑声一颤一颤的,颇具喜感的样子,“阮东琳,你要好好珍惜他啊。”领导拍了拍她垂在身侧的手臂,好声嘱咐着。
这下阮东琳就明白了,原来领导所说的所谓“男朋友”,原来指的就是周啊。
不是说路远扬。
总结出这个结论的阮东琳,就好像是被摸了逆鳞的龙,抑或是倒梳了毛的猫,突然就咋呼地跳起来,血红了一双大眼睛,张着嘴愤愤不平地反驳道:“不,不是,您搞错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领导就当是小姑娘害羞,继续“呵呵”笑着。
周时不时就会出现。
一次,阮东琳跑业务的时候遇到了刁难的人,看她是个青涩的小姑娘,便硬要指名见他们领导,说什么“不要叫个小丫头片子忽悠我”。阮东琳受了冷嘲热讽,满肚子都是委屈,便一个人找了个楼梯间,坐在台阶上,抱着膝盖,就把脑袋埋进膝盖间哭。
她没哭出声,只是眼泪却总是停不下来,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扑簌簌往下掉。
她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那么哭过了,多大多难的任务她都一个人挨过来了,比起那些,什么“业务谈不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委屈得她禁不住泪水涟涟的。
她的身边却突然坐了个人。
他坐在她身侧,也不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干状的手帕递给她。
她抬起哭得红通通的脸看过去,是周。
还是那样清俊的眉眼和温柔和煦的笑容,如天神一样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向她伸出援手。
她眨巴眨巴眼睛,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伸手去接。周看她久久没有动作,心里也有些着急了,心想,这姑娘不会是被骂傻了吧?就手持着手帕,主动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和鼻水。阮东琳这才反应过来,从他手里夺了手帕就往自己脸上招呼。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隐藏在手帕后面,闷闷的,听不真切。
“正好在附近办点事情。”周讲着不知是真还是假的说辞。
“那你怎么走到楼梯间来了呀?”阮东琳不信,还是问。
“因为我看到你了呀。”周笑,“我刚刚在办公间就看到你了,只看着你一个人恍恍惚惚、冒冒失失地走过来,还以为要同我打招呼呢,结果你一个转身就进了楼梯间,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周说着说着就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阮东琳破涕而笑,她摆着手说:“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没有看见你。”
“没关系。”周说,“我知道。”
阮东琳站起来,裙子膝盖处的布料被她的鼻涕眼泪濡湿了小小一片,她觉得在周面前,这样的她显得十分不好意思,不住地弯腰去遮。周勾着嘴角,把手抵在鼻梁上,小心地隐藏住自己的笑意,不忍心让窘迫的阮东琳看见。
阮东琳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一直跟他鞠躬道歉,直到走出了楼梯间还这个样子,让周觉得哭笑不得。
“真不用了,你不要这么客气呀。”周苦笑出声,“阮东琳你看,他们是不是还在等你呀?”
周的手遥遥一指,指向的方向,正是阮东琳的同事们站着的地方。他们聚在一起,多是些年轻活泼的女孩子们,便不住地朝着他俩的方向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也正是他们这些人,在阮东琳被客户刁难的时候,还呈现出一副眼观鼻鼻观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的。
“是啊,那是我的同事们。”阮东琳微微点头,“那周,你看,我还在工作呢,我们之后有空再约,我请你吃饭,好吗?”她仰头看向他,带着些恳切的目光。周低着头,也看着她,点了点头,说:“好啊。”
“你电话没换吧?”
“没有,还是那个。你总能联系上我的。”
“真的呀?那太好了,我们之后再联系吧?”阮东琳问。
“嗯。”
“那我先去了哦?”
“好的,你先走吧。”
周看着阮东琳蹦蹦跳跳、好像没事人儿一样走开的样子,想,这是他第几次看着她离开的背影了呢?
他又要再看几次她离开的背影了呢?
****
这之后的阮东琳,其实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无关痛痒的小插曲了,她被工作和生活的艰辛磨砺得来不及去想那些个风花雪月了。以前人人羡慕她的手,说她那双就是千金大小姐的手,细白滑嫩,连一个薄茧子都没有。他们说,她一定有个把她宠得很好的人,可现在,她的手已经完全不同了,虽说不上是面目全非吧,却也早已缺了当初的光彩。因为辛苦跑业务,她的指节也渐渐变得粗大,掌心的纹路都变得粗糙纷杂。回家后,她有时也会在无意间对着路远扬垂头丧气地抱怨,唉,先生,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可不好看了。
“没事的。”路远扬握过她的手,递到嘴边亲上一口,“我稀罕得紧。”
阮东琳的心这会子啊,就可没出息得痒啊痒的。
百爪挠心。
这双变粗变硬了的手换来的,却是阮东琳取得的当月“业绩之星”的称号。经理把粗制滥造的徽章从天鹅绒缎面上取下,牢牢地别在她的胸口,向外围着的一圈职员们朗声说道:“这是我们这个月的业绩之星,阮东琳!大家掌声鼓励!”
啪啪啪啪啪。
人群中发出了齐刷刷的掌声。
阮东琳从小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荣誉与褒奖,一张小脸涨得通红,连连摆着手说:“不是的不是的,没有没有,这都是大家和我一起努力的结果,军功章也有你们的一半。”
瞧她这通发言,真是又红又专,滴水不漏的。
入世这么小半年,她已经摸爬滚打得什么场面话都会讲了。
“我们小阮啊,那么年轻!那么优秀!还那么谦虚!”经理例行发布起慷慨激昂的演讲,“啪”地一声拍在阮东琳的背上,吓得阮东琳一个踉跄,“我们都知道杨总吧?对对对小王说得对,就是要求最难搞、脾气最大的那个杨总!——你们谁都不要说出去哦!”——经理威胁性地将手指向人群,一众职工纷纷摆手说“不会不会”——“我们这次这个与杨总合作的项目啊,线上都谈了小半年了,一直谈不拢,可愁死我这把老骨头了!可是,这我们小阮一去啊,就手到擒来了!你们说,你们说说,啊,我们小阮她啊,厉不厉害!”
人群捧场地对她连连称赞,说“厉害厉害”。
杨总原来就是那天那个害阮东琳偷偷躲在楼梯间哭的那个罪魁祸首。他是公司今年最想拿下的客户,可总是啃不下这块硬骨头,无论开出多好多优的条件,都会被对方皱着眉驳回。公司本想,得不到这次的合作也得把责任择得干干净净的,不能让竞争对手得个他们“没本事儿”的传说,故而就派了阮东琳一个人去与杨总应酬。大家都知道杨总这个人,最是喜欢排场了,只派一个身姿单薄的小姑娘,显然是要引得他恼怒的。公司领导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最后找个借口把阮东琳这样大半年做不出个业绩的小职员开了,看她也卷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谁知道这个杨总是吃错了什么药,主动找上了公司,双手握住领导的手,一边说一边点头一顿夸:“你们这个小员工好啊,她非常好啊。”
领导被夸得是分外蒙圈,被杨总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弄得措手不及,手也被对方握住。那是幸好还没忘记正事儿,“那杨总,这合作的事儿……”
“好说好说。”杨总满脸堆起笑,当天便签下了合同,也没再讨价还价什么条件,主动谈成了合作事宜。
领导直到把合同完全安定下来,还是想不通啊——这杨总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了这个决定的呢?
不过,既然这合同也已经签完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是说什么也是不能反悔了的吧?他双手把合同紧紧地搂在胸口,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心底的问题问了出来。
“啊,这个嘛。”杨总的眼珠子滴溜溜转上一圈,露出了神秘莫测的笑容,“你们公司可真是卧虎藏龙啊,这小员工啊,来头可真不小啊,居然能请到周公子做担保。啧啧啧啧,老陈啊,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她哦。”说完,杨总还煞有介事地拍了拍领导的肩膀,一脸的“你懂的”。
领导一边忙不迭点头哈腰地应着“好的好的,您指导得是,指导得是。”,一边在心里纳闷开了——这周公子,是哪个周公子,是怎样个何方神圣,又与他司的小小职员阮东琳之间有着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一男一女间,能这样出手相助的,不是怨,不就得是爱了吧?
领导边的小助理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一拍脑袋,说:“哎呀,我想起来了,阮东琳去见杨总那天,确实是有一个男的和她一起回来的,我们都看到了!”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半个公司都隐隐约约知道了,看似泯然众人矣的阮东琳有个神通广大的男朋友,人家两口子可好了呢,小姑娘跑业务男友还要偷偷地帮,不但如此,还不让小姑娘知道,啧啧啧,这该是何等的琴瑟和鸣啊。
知道了这层关系,领导层一个个,越看阮东琳越觉得顺眼——嘿,以前的自己也真是瞎了眼,怎么没发现身边有这么一尊菩萨呢?幸好幸好,还是给招进来了。
领导心情一好,嘴一顺溜,就把周的事情给阮东琳透了点口风,“小阮啊,你和你男朋友最近处得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结婚一定要请我们去啊,到时候我给你们可得包个大大的红包啊!”
阮东琳正在网上查要去探访的下个业务对象的路线,正一点一点抄到随身带的记事本上呢,猛听得领导这么一说,发起懵来,问:“什么男朋友?您说的谁啊?”
“哎哟你个小姑娘,还能有哪个男朋友?”领导笑着拍了拍她的脑袋,这一掌,却把阮东琳敲得更懵了,傻愣愣地直着眼睛看着领导。领导见她不识相,便提醒提醒她,“就那个,你那个ABC男朋友呗!”
噢,周啊。
这下子,什么都解开了。
她为什么能拿下“业绩之星”,为什么能分明被杨总训斥跑后依旧谈下了那么大的一笔投资,为什么突然间领导对默默无闻的她格外器重格外偏恩?
还不都是因为,以为她是“那个”周的女朋友。
现在想来,原来都是周的“功劳”。
这样一想就全想得通了,原来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可她不是的。
阮东琳不是周的女朋友。
她不能平白无故受周那么多好,她一定要当着他的面、堂堂正正地讲清楚的。
阮东琳终于拨通了那个号码。
那是周在上次同她一起到中国的时候用的那个号码,后来他们说好要一起回隐国的,可她却临时做了逃兵,留他一个人飞回了隐国。
隐国啊……那段往事仿佛已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了。
也不知道许桑榆现在怎么样了。
上次她同许桑榆在网上视频通话的时候,许桑榆还兴高采烈地对她说,“阮东琳,阮东琳,你看,这是我男朋友。”她将手伸出摄像头取景区外去捉,不一会就用手勾住李锦絮的脖子出现了,“你也认识吧。”
李锦絮略显尴尬地冲她挥挥手,说:“嗨。”那个光头男孩的脑袋甚至反光得整个室内更加通亮了,阮东琳不禁笑出了声。
阮东琳当然认得,那是李锦絮啊,那是她们都是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许桑榆在自家的床上、跟她用最美好的语言描述过的那个李锦絮啊。
“李学长,您好,好久不见了。”阮东琳笑着向他们点头招呼。
“哇,阮东琳,你怎么这么客气呀!”许桑榆又咋咋呼呼地惊讶开了,“没关系的诶,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了,你怎么对他不客气都行!我替你撑腰。”
许桑榆没心没肺地咧开嘴笑开了,阮东琳也跟着笑。
李锦絮看着两个女孩间那份独特的默契,也跟着低下头,羞涩地笑了。
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和许桑榆在机场与她分别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
“喂?”
陷入回忆的阮东琳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到,手机一时没握稳,差点掉到地上。她急忙稳住了手上的动作,磕磕绊绊地回了句,“喂?周,我是阮东琳。”
“我知道。”听筒那端传来一如既往让人心安的周的声音。
“我上次说要请你吃顿饭的,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周笑起来,电话那头的阮东琳似乎感染了他喜悦的心情,也跟着勾了嘴角,“那你是要请我吃饭了吗?”
“是啊,你不乐意吗?”她还是觉得心虚,偷偷跑到公司的楼梯间里给他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乐意,乐意。”周说,“你说要请我,我怎么可能不乐意呢?”
阮东琳以前怎么不觉得周是个这么油嘴滑舌的人呢?她“嘿嘿”一笑,说:“既然是我请,那餐厅和时间都由我来定,怎么样?”
“好啊。我那就恭候着你的消息啦。”
电话终于被挂断,阮东琳抬手一看手表,时间刚好下班,便急匆匆地跑回自己的格子间,取了一会儿要换上的运动鞋。她是典型的朝九晚五的作息,她不够勤奋,不愿早起避开早高峰时间段,平生最喜欢的事情也不过就是睡懒觉了,所以她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总是被挤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车厢里,早晨高峰期的地铁里什么味儿都有,她困难地连气都不敢用力喘。
在这样的环境下,若是再让她穿着细长好看的高跟鞋就太难为人了,故而她每天都会备上一双平底耐走的运动鞋,方便她在上下班的人流里快速穿行。
她那双鞋本是洁白的鞋面,却在长期的跋涉之下,早已变得灰扑扑的。同事们开她的玩笑,说,“阮东琳,你这可是时下最流行的’小脏鞋’啊。”阮东琳不懂什么时尚,只觉得对方应该是在夸自己,便也跟着油嘴滑舌地回一句:“可不是,这一不小心呢,就成了时代的弄潮儿。意外意外,都是意外。”
阮东琳这才真正体会到了社会地位的不同所带来的好处。公司里几乎人人都以为她是周的女朋友,无论她怎么解释他们都不听,就这么误会着误会着,人人做事都会让她一步,有意无意地奉承她,就好像奉承她,就是在奉承她那个“好好男友”,周。
****
她在网上查了好多功课,想来请周这样的非富即贵,一定得带他吃点好的吧?可是太好的她又怕在周面前班门弄斧,吃平价的又不能显出她的诚意。正苦恼着呢,一个名字像闪电一样打进了她的脑子里。
沈欢。
对啊,沈欢。
可以请周去沈欢的店里吃啊。
先不说沈欢那个高深莫测的背景,就单说他那一手让人流连忘返的手艺,就足够拿得出手去请周这样的贵客了。
他们约定了就这个周日,一起聚一聚吧。
时间地点一定,难事儿便已经成了一半,阮东琳握着手机躺在床上,喜滋滋地等着周日的到来。
路远扬看她这副样子,也只是摇了摇头,表达了他的不解,却也没说什么。
阮东琳没敢告诉路远扬她要去和周一起吃饭了,所以她提前了些时间来到了沈欢的店面,双手合十,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一定不要告诉路远扬。
“你担心什么?”沈欢笑她,“以前远扬和那个小明星花知晓来的时候不也同样没告诉你吗?”
阮东琳一脚站定,一脚点地,像个圆规一样无意识地用脚在地上画着圈圈。她说:“先生他身体不好,我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一定会生气的。”
“那你明明知道远扬知道了会生气,为什么还是执意要请这个人吃饭呢?”
“因为……因为我不喜欢欠人人情吧……”
沈欢笑开了,他的右眼睑上有一块挺扎眼的疤,他以前也同阮东琳说过,说这是年轻的时候与人打架落下的,“不过嘛,疤痕就是男人的勋章啊。”阮东琳表示不解,她只觉得沈欢这张秀气到偏女性化的脸,反倒是因为这道狰狞可怖的疤痕显得阳刚意味十足。
她不知道沈欢在笑些什么,只是不停不停地央求他:“大哥,你当我求求你吧。”抓了他的手臂就是说什么都不肯松。
沈欢俯身拍拍她的脑袋,“你看你,都叫我’大哥’了,你说这忙,我怎么不也得帮一把,是吧?”
姑且就算是他答应了。
小姑娘开开心心地对他甜甜一笑,说:“大哥,你真好。”就差没在屁股后头装上一条毛绒绒的尾巴,摇啊摇的。
可沈欢一想起她的说辞来就觉得好笑。
这小姑娘说自己不喜欢欠人人情,可殊不知,她却从来没有对给予了自己最多人情的那个人和颜悦色过,即使是表面顺从,心里也是张牙舞爪不肯服输的。
这都是路远扬告诉他的。
路远扬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来这儿吃饭,神情忿忿地说她没良心,没心没肝的,吃他的用他的最后还要跑,整就一只登堂入室的白眼狼。沈欢笑话他没用,也就只敢在他面前这么咋呼两声,真到了阮东琳身边,又臭着一张茅厕里的冷硬石头样的脸,默默忍受着她的一切“剥削”。
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只是涨红着一张脸,抱着手臂远远地看着在那正襟危坐的两人。
“……周,好久不见。”阮东琳斟酌着用词开口。
“也没多久。”这不是前不久刚见过吗?
“啊……这样。”客套话被对方打回来,倒是显得阮东琳有些尴尬。
“那我们先点菜吧。”周试图给她台阶下。
“好好好。”本是要尽“地主之谊”的阮东琳忙不迭地连声说好。沈欢借机就把菜单呈了上来,周客气地问他:“能劳烦您推荐一下这里的特色菜吗?”沈欢摇摇头,说:“没什么特色菜,就是家常小炒而已。”周点点头,继续翻看着手上的菜单。
两人姑且点了三菜一汤,阮东琳说太少了,让周不要因为是自己请客就跟她客气。周拦下她想要继续招呼的手,说,“就先这样吧,不够一会儿再点,吃不掉要浪费的。”
沈欢看着两人觉得好笑,各怀鬼胎,心照不宣。
可他低头一看手上的点菜单就犯愁了——松鼠桂鱼!这两人是知道不知道松鼠桂鱼有多麻烦多难做!这不是存着心刁难他嘛!
菜一时半会儿上不来,两人就坐着面对面聊天。阮东琳开门见山便说:“周,你能不能……能不能不要帮我啊?”
“噢?你说哪方面?”周不回答,反问她。
“就是……公司那里。”阮东琳整理着措辞,“你能不能……能不能不要去帮我,就算我做不好也没关系,请你不要这样帮我。”她的目光灼灼,不容一丝反驳。
“阮东琳,你误会了。”周把手掌上下叠起,置于自己身前,他的声音低低的,平缓地叙述着事实,“其实你不用这么感谢我的,其实,你报出路远扬的名字,也是一样的。”
这是周第一次正式称呼起“路远扬”的名字,而不是欲盖弥彰地称呼他为“阮东琳的叔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周也是懂得的。
阮东琳沉默了,低着头,不知道这时的她的脸上挂着什么样的表情。
阮东琳,你知道吗?我喜欢你的,所以做这一切都是我愿意的,没关系的。
只是这些话,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跟她讲的,这些话,会吓到她的,会让她产生困扰的,他不舍得让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孩儿露出困扰的表情。
很多人很疑惑,他为什么会喜欢阮东琳?
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世俗观念里的“人生赢家”,什么样子的女孩他没见过呢?又怎么会喜欢阮东琳这样说好看不好看,说独特不独特的丫头呢?
很多人很疑惑,包括叶绯绯也是这样的感觉。
是的,除了顾伯,他还偷偷地去见了叶绯绯。
也不能说是“偷偷”吧?但叶绯绯与周之间的约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人知道这件事。
来见周的时候,叶绯绯的脸上化了明艳动人的妆容——就好像她的名字一样,绯色倾城。她这副模样,和周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上一次周见到叶绯绯的时候,她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恐怕是她人生中最灰败的一段时间。但她从骨子里就是那种,有耐心且有决心时时刻刻保持“美丽”这个属性的人。
包括怀孕了的时候也一样。
叶绯绯的孕象十分明显,突然间胖了一圈,脸都圆润了不少。当她刚从车上扶着腰摇摇晃晃地下来时,就看见周已经站在门口了,替她拉开了厚重的玻璃门。她不好意思让周等得太久,就加快了脚步,小跑着跑向玻璃门的方向。
周一件她跑起来,表情都变了,从门口的方向冲过去扶住她,“叶小姐,您小心点,您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是摔了伤了,我会一辈子都过意不去的。”叶绯绯“扑哧”一笑,既被他的绅士所感动,又颇觉得他这样繁琐的绅士行为显得木讷极了。她玩心大起,忍不住去纠正他对她的称呼:“周,我已经结婚啦,还叫’叶小姐’呢?”
周的脸一红,说:“叶女士。”
“哎呀哎呀,还脸红上了呢。”叶绯绯掩着嘴“嘿嘿”一笑,“哎呀,我是在逗你的啦。不过,被人叫’叶小姐’的感觉也真不错呀,好像我还是很年轻的样子呢。”
“您本来就很年轻的。”
“没有没有。”叶绯绯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两个多月啦都。”
周把她搀扶到餐桌边,替她拉开椅子,让她能够安心地坐下。
“什么时候预产期呢?”周扬着下巴,点向叶绯绯肚皮的方向。
“明年年初就生啦。”叶绯绯算了算日子,“啊,大概正好是农历新年那个时候呢。”
“跨年宝宝,很有福气啊。”
“是啊。”叶绯绯也觉得周说得有道理。
“您和您先生……动作挺快啊。”坐定了些,周就开始揶揄起叶绯绯。
“是啊,动作再不快一点,我就要变成高龄产妇了啊。”叶绯绯扶着额头,露出了一个苦笑,“周先生,上次您救路理那次,我还没好好感谢您呢。”
周没想到她还会提到这茬,不禁有些发懵。他摆摆手,说:“没有没有,我很对不起您。”
叶绯绯也极为客气地摆摆手,说:“不不不,谢您还是要谢您的。”
空气,忽然之间有些凝滞。
两人面对面坐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再说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着眼前那杯茶,不知在想些什么。
是不是又想到那个寒冷的冬天了呢?那个比以往记忆中的任何一个都还要刺骨寒冷的冬天。
还是叶绯绯率先打破了沉默。
她说:“周先生这次约我出来,又是所谓何事呢?”
周喝了口茶,感受到温热的液体慢慢地从口腔、喉道、胸腔慢慢往下淌的那阵充实感。他说:“这次麻烦您来,是想要向你打听一下路远扬与阮东琳之间的事情?”
“噢?你想知道些什么呢?”叶绯绯继续问。
“就有关,他们俩的过往的一些事情。”
“有关他们俩的过往,你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了解的吗?”她也事先查了周这个人,她不相信,这世上会有周想知道、却求助无门的事情。
“我想听听叶女士您的回答。”周说得委婉客气,叶绯绯也同他撕不开脸。
“我的回答嘛……”叶绯绯沉吟了一会儿,“我曾经,是与你的立场差不多的吧?可以这么说吗?”她询问周。
“是差不多吧。”周回答她。
“其实我到现在,很多时候还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阮东琳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有你,有先生,啊,对了,还有那个厨房的帮工是不是?叫什么来着,靳……靳……哎呀,我给忘记了。”叶绯绯拍了拍脑袋,“真是一孕傻三年啊,我这记性啊,最近是越来越不好了。”
“靳楚楠吧?”周提醒她,“他和阮东琳一起去了隐国。”
“哦,是的,靳楚楠,是他。”叶绯绯恍然大悟,连拍了好几下自己的额头,“不过没关系,也不重要了。”
“……”周不敢打断叶绯绯的叙述。
“你知道吗,我爱人都曾经问过我,恨不恨他们。”叶绯绯仿佛像想到了什么一样掩着嘴,“哈哈”大笑起来,“对,就是他们,那对狗男女!阮东琳和路远扬,狗男女!”她还是笑着,周却笑不出来,只好目光安静地看着叶绯绯,等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继续向他叙述。
“……其实我,是不恨的。我甚至很谢谢先生。”叶绯绯仍旧习惯着自己作为路太太时对路远扬的称呼——“先生”,亲昵又疏离,“人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两次投胎,一次是出身的时候,一次是嫁人的时候,真是说来可笑,我两次投胎都不好。先生他把我从叶家那个牢笼里解救了出来,我很感激他。可是命运就是那么猝不及防,他不爱我,我知道,我使着小手段被迫让我拥有了路理,他虽然也很爱路理,可是……果然……”她哽咽了一下,眼里噙着泪花,“不是我的,终究不会是我的。”
周回忆起那个被他救起的孩子,小小的、白白嫩嫩的,眉目间有着不同以往小孩的执着与认真。
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天的路理会突然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公园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掉进了湖里。是的,事后路家人和叶家人都去调查过那个公园的监控录像,试图找到路理这一切不自然的举动后的蛛丝马迹,可是遗憾的是,路理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刚好是监控摄像机的死角,只拍到路理跌进湖里时候在空中挥动的小手,好像在跟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叶绯绯是看不得这些画面的,她一看就会变得面孔煞白,目光呆滞,无论这事儿过了多久,她只要接触到丁点儿跟路理有关的事,就分分钟变成了那个新嗓子的母亲,被抽离了一切神识。
可这会儿的叶绯绯,未等周想好安慰的措辞,就已经自己调整好了情绪,笑起来,“好了,我们不要谈这些了。你不是来问有关先生和阮东琳的事情的吗?”她深吸了一口气,调整好呼吸,接着说,“我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多,当时的我被仇恨所占据,不能客观地面对这两个人。现在,我终于抽身事外了,却更不能够评价什么了。说什么我都是扮演着这部戏里最丑陋的角色。”她苦笑出声。
“不是的。”周急切地想要去安慰她,“不是这样的。您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坚强的女性,您是一位好母亲,您一定会对您肚子里的孩子很好的,像对路理似的一样好,您一定可以的!”
周的中文措辞有着奇怪的翻译腔,叶绯绯听着觉得好笑,但又因为他的真挚,不好意思笑出声。
“周,你觉得呢?”叶绯绯问,“对你而言,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周沉吟了一阵子,开口道:“是镜子。”
“镜子?”这个回答倒是出乎了叶绯绯的意料。
“是的,镜子,是破镜重圆的青铜镜。”周解释道,“阮东琳曾经说过,世上谁都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们是散落在世界上的同一面镜子的两半,是破镜的两块碎片,是注定缠绕在一起的两段命运。”
叶绯绯听了周的叙述,骤然大笑出声。她笑得那么开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说:“周,你可真有意思。”
她说:“我以前曾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的时候,是嗤之以鼻的。我以为,那海自有舟可渡,那山亦是有路可行。这话何不改为’此爱翻山海,山海亦可平。’我也曾也坚信’郎心自有一双脚,隔山隔海会归来’。后来……后来,我才知道,’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山海亦可平。难平是人心。’爱这种东西,比任何一座山,比任何一片海,都还要难以翻越,你爱的人不对,走再多路都是枉然。”
她说:“会想他吗?会想的,他那么好,他是那么那么好的一个人啊。可是又能怎样呢?总不能因为做了个旧梦,就打电话给故人吧?总要放开。”
最后,她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停下来,不再继续往错误的路上走下去,就是一种进步了。”
“不过。”叶绯绯接着说,突然间,她的声音变大了,“我不曾后悔嫁给先生的。他对我的好都是真的,只是不是同一种好,只是不够那么好,不够对阮东琳似的那么好。他也对路理很好的,我很感激他。路远扬这个人呀,回忆起来,真是挑不出丁点儿毛病啊,只是,不爱我,罢了。”
周送叶绯绯离开的时候,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大雨,“哗啦啦”地打在餐厅前的台阶上,溅起朵朵水花。周说,我开车了,不然我送你回去吧?叶绯绯说,没关系的,我叫我爱人来接我就好了。
她给她肚里孩子的父亲打了个电话,不出二十分钟,餐厅门口便开来一辆黑色的私人轿车,那个周一向只听过名字却未见得其人的沈翰闻沈医生从车上下来,撑起一把奇大无比的黑色雨伞。
他打开伞的声音,“砰”的一声,像是什么花朵突然在春天里绽放了的声音。
沈医生撑着伞涉水走来,冰冷的雨水拍在他的脸上,不知不觉间染湿了他的黑发。
叶绯绯笑着冲沈医生招招手,“嘿,嘿,我在这儿。”
周侧头看过去,叶绯绯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眼睛亮亮的,满脸都是小女儿的娇态。——现在的她,不是路太太叶女士,而是叶绯绯她本人。
沈医生将她接走,两人同他道别,问他有没有带伞,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车上还有一把备用伞。周摆摆手说不用了,自己的车就停在餐厅自设的停车场上,他一会小跑过去就可以了。
“那我和绯绯便先告辞了。”沈医生向周稍稍一欠身,周也回以礼,便看着叶绯绯和沈医生渐行渐远。
沈医生手上撑着的伞够大,罩下他们两个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沈医生还是执意将伞往叶绯绯的方向倾斜,让自己大半个身子都暴露在风雨里。以周的方向看过去,都能清楚地看到,沈医生被雨水打湿而显得颜色更加深沉的肩头。
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了沃尔沃边,叶绯绯似乎是发现了沈医生这点儿暗戳戳的小心思,说了些什么。可惜离得太远了,周始终是听不真切,只见到叶绯绯娇嗔着手握拳头捶了沈医生一下,小女儿态尽显。
真让人羡慕啊。
周那么想着,又不自觉地将手往口袋里伸了。
他最近烟瘾越来越重,他也好想变得越来越不像他了。
这是好事,抑或是坏事呢?
****
包括今天的现在这个时候,阮东琳坐在她对面,显出一副唯唯诺诺不敢多言的样子,好像随时都要与他划下一条中英相互不可侵让的三八线,他一见着就觉得心烦胸口闷,一有这样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烟瘾上来了。
尼古丁这个东西呢,就好像阮东琳这个女孩子一样的,你不摸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但一旦你觉得是习以为常了的呢,想戒掉就很难了。
沈欢是时候端上了冷菜,打破了这桌略显尴尬的氛围。
今天店里只有他们两个这桌,沈欢替他们清了场,他觉得阮东琳对面这个小子气度或是举手投足间,都不像是个普通人,而阮东琳又是除了名儿的“小炸弹”,谁知道这两人一旦一句话谈不拢,又会做出点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来?一想到这样的场面,沈欢就后怕十足地拍拍胸口,这二位都是佛爷,都是观世音菩萨,他这样的平民百姓惹不起是真惹不起。
他在心里进行完天人大战,面儿上还不能表现出一分一毫,只能暂时先耸耸肩退下了——唉,他的松鼠桂鱼还没打理好呢,怎么敢管那么多闲事。
可当他刚打算转身走入厨房的时候,门外却传来摁铃声。
叮咚——
叮咚——
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
来者,绝非善类。 山月可知心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