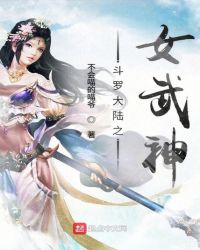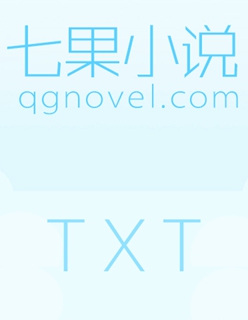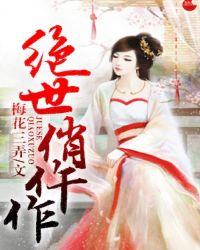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飞向太空港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的确,发射场上的翻译除了要承担接待服务翻译、会议翻译(一天二至六个会),有的还要定在技术岗位上,跟随指挥员下达口令,即做同声翻译。此外,还要担任日常值班,保证二十四小时同美方的沟通联系。
可以说,从宿舍到厕所,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在同美国朋友的交涉中,一旦离开了翻译,中方指挥员寸步难行,一事无成,等于是哑巴、聋子和瞎子。
所以这次在发射场,我见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现象:中方指挥员的身边,从早到晚,始终跟着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保镖,而是翻译。
据说,有一次中方一位指挥员因忘了带上翻译,但又有急事要同美方交涉,结果双方连比带说,反复折腾了好几遍,谁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最后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的吊装对接过程中也是如此。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中美专家之间就无法用语言交流,双方只有靠打手势——用哑语配合。有的操作手势双方都能理解,靠手势还凑合。但有的操作手势重复打了好几次,对方也不明白。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手势表达的意思不同。
比如,中方打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把速度放慢一点,中方调装人员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双方一番大叫大嚷后,只好亮出裁判手势——暂停。
在发射场担任翻译,不仅辛苦,且责任重大。
航天技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尖端科学技术。中美双方一起讨论技术问题时,有的深奥的技术问题,别说把英语翻译成汉语,或者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就是中国人讲给中国人听,也未必完全能听懂。
加之中方是中方的翻译,美方是美方的翻译,当各自的翻译对同一问题理解不同,或者表达方式不一样时,也很容易引起误会,造成矛盾,甚至导致某项工作的失误。
比如,有一次,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对接之后,要进行一次“全区合练”。可双方进入合练状态后,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儿,美方也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出来了。于是,美方指责中方没按规定程序执行,中方埋怨美方没按会议要求办理。
结果,合练被迫中止,开会找原因。
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扯了半天,越扯越乱,越扯越糊涂。直至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理解不同。中方理解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合练,即从西昌—西安—北京—太平洋测量船的合练;而美方理解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全球合练”,即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间的合练。“全区合练”与“全球合练”虽一字之差,内涵却完全不同。由于一个用汉语讲述,一个用英语表达,原本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而到了真正发射卫星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凡是与美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身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在发射程序实施过程中,翻译除了要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如实地传递给美方外,还要用专用电话同美方时刻保持联系,随时交流各种问题;若是在翻译过程中,哪怕译错一句口令,也会导致工作程序错乱。
尤其是在地下发射控制室的翻译,风险更大。发射控制室设有一间空房,如果发射前一旦出现意外紧急情况,需要中美指挥员进行协调,便在这间屋里进行。这就必须依靠翻译。想想,假设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需要重新商定,若是翻译因为时间紧迫、心情紧张,将某个意思或者某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其后果将会怎样?
实事求是地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翻译人员,大都是走出校门不久的本科生或大专生,不少人员都是临时抽调出来的,并未经过发射基地翻译的专门训练,对航天技术尤其是对发射外星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加上匆忙上阵,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发射任务,所以,尽管其中有部分人员的英语水平也相当不错,但就总体水平而言,若用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标准来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是因为,在过去近二十年里,由于发射场位于大山沟,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与外界缺少联系与碰撞,与国外更无任何交往。虽然多数技术人员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也对英语有很大的兴趣,但后来现实生活告诉他们:外语与本身的日子并无多大关系,不懂外语照样活,照样干,照样晋职晋级,照样把卫星发射上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语的兴趣也就渐渐淡下来;到了后来,甚至不少人早就把外语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这次有了发射“亚星”的任务,因了美国人的到来,山沟的语言受到强烈的冲击;加上迫于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压力,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专家技术员们本来已经睡着或死去的外语意识,又开始复活了。
通过与美国人在工作中的直接接触与实际交往,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外语是那么重要。就像一个山区的老农,第一次走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当他急于要上厕所而四处打听时,别人却怎么也听不懂他的方言,这才感到普通话的重要。
不少人开始认识到,随着人类开拓空间文明的不断发展,地球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将会越来越多。英语这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肯定是发射基地今后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
有的年轻的技术员深有感触地说:“外语这玩意儿太重要了,不好好学,看来还真不行!”有的老专家也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这次能用英语同美国人直接对话,工作效率至少可以提高一倍。”
于是,在清晨,或星期天,常常可以看见,基地不少人一大早便爬起来,独自站在小河边,或者菜地旁,面对高高的发射架或者黛绿色的大山,大声地朗读英语……
当然,中美语言的碰撞,唤醒的并非只是中国航天人的语言意识。
美国休斯公司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讲法语。在法国参加发射时,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参加发射时,我就讲英语。但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的技术人员大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汉语,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有时就连一根导线的事,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找到翻译才能解决。看来,这汉语是非学不可了。等回国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学习汉语!”
加拿大太列公司高级专家戈比回国时,在临上飞机前还谈到了语言问题。他说:“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自己也得好好学习汉语。”
我在发射场采访期间,还亲眼见到,美国休斯公司一位老专家的一个小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的空隙,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画着,嘴里还不时嘀咕两句。
我问他:“您都这般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刻苦地学习汉语?”
他说:“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丰富而有趣的。再说了,既然要同中国搞空间合作,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哪行?告诉你吧,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这段时间里,已经偷闲记住了二十多个汉语词汇了!”
二十八、从要走,到再来
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源于落后。
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70年代,在国内打一次长途电话,常常要苦苦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还未必能打通,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曾领受过的滋味。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靶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事实并不尽然。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据说,一位美国朋友在发射场的小宾馆向大宾馆打电话,拨了四五次都拨不通,气得扔下电话,冲着司机就喊:“走,开车,自己去!”
通信问题,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美国人刚到西昌的第二天,中美召开第一次协调会。会议一结束,美国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鲁·马克便给洛杉矶总部打电话,汇报情况。
电话挂得很顺利。马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喂,喂……”
马克刚讲了两句话,电话突然中断了。
“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
马克对着话筒,一个劲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一连串的“嘟嘟”声。
马克急了,“啪”地扔掉话筒,冲进宾馆经理办公室,对着经理就发了一顿脾气,还连连挥动手臂,大声叫嚷道:“差劲儿!差劲儿!简直太差劲儿了!”
经理是河南人,一急,就露出一句河南话:“咋啦?”
马克咆哮道:“咋啦?电话,电话,电话怎么回事?”
经理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电话,电话咋啦?”
马克说:“咋啦,你说咋啦?我在问你,你怎么问我‘咋啦’?”
经理这才急忙改用普通话:“先生对不起,请您告诉我,电话到底怎么啦?”
马克说:“你们的电话不通!”
经理说:“不通?怎么会不通呢?”
马克更急了:“我是顾客,你是老板,你应该知道怎么不通,也有义务告诉我怎么不通,我怎么知道怎么不通?”
经理连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派人去修,马上派人去修!”
…………
接下来,电话不通的故事,在其他美国人的身上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几乎每一天,中方都会接到来自美方的关于通信的告状电话。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还找到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高先生,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要马上离开西昌!”
高先生一听,忙问:“离开西昌?怎么回事?”
佩尔捷说:“我要回美国去!”
高先生说:“为什么?”
佩尔捷说:“我自2月6日到西昌后,你们的通信工作一直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我们五六十名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且就这三条线路还不能保证正常使用。所以,我要马上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回去后,我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
高先生急忙道歉道:“对不起,佩尔捷先生,我们一定尽快想法解决,一定尽快想法解决!”
接着,另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找到高先生,表示要离开西昌。考梯斯少校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这次来中国西昌参加‘亚星’发射的项目人员下次再也不会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我提请你们注意,我反映的意见,是在这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
这两位美国专家都明确表示,他们所说的情况,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注意!
当晚,高先生向卫星发射基地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一早,中方有关领导找到“亚星”项目经理歇尔·纽曼先生,首先对中方的通信问题表示了诚恳的歉意,然后说道:“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通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纽曼先生问:“什么情况?”
中方领导人说:“西昌卫星发射场在去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
“泥石流?!”纽曼先生顿感惊讶。
“是的,”中方领导人继续说道,“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只有半小时的工夫,我们通信团的房屋便纷纷倒塌,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甚至连公路和通信建筑物也发生了倒塌和崩溃!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的人不仅无法正常吃饭,甚至连喝水都困难。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赶在你们来之前,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基本畅通。西昌与全球通信,这是第一次,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
纽曼先生听了后,很感动,连声说道:“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于是,关于两位美国专家要回国一事,纽曼先生表示愿意和他们进行沟通,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解决好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为了保证此次发射顺利进行,中方在通信问题上此前做了很大程度的努力,不光抢建了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还花高价租用了国际电联的四条国际通信专线。这四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七条国际直拨电话线——四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三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但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与美国的通信条件相比,依然无法满足美国人的通信要求。
于是,中方一方面立即着手解决美方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将情况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请求邮电部速派人来协助解决。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