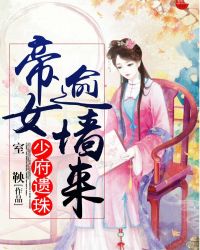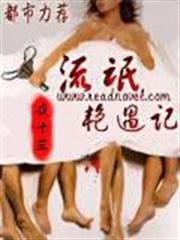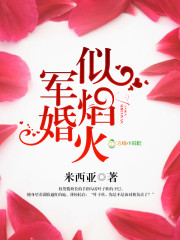第一百二十四章 万世永昌
天下初定,西海宾服,然而在远离咸阳的地方仍旧会偶发一些小型的叛乱。嬴政明白到底还有些人贼心不死,总是借着星火之光想燃起燎原之势。
于是,他准备御驾东巡,一来可以彰显帝国权威,二来也可以震慑人心。
秦王二十八年,嬴政行至鲁地,与儒生商议泰山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关于祭祀礼仪,儒生众说纷纭,一时拿不定主意。
秦国向来以务实闻名,对这繁复冗杂的礼仪素来不甚上心。嬴政实在耗不下去,于是摒弃儒生,亲自带着皇长子扶苏及文武百官登泰山,筑坛祭天、拓土祭地,号为封禅。并刻石为碑,祗颂功德,欲垂万世。
岂料下山时突逢狂风骤雨,嬴政一行措手不及,只得于途中一棵松树下避雨,待雨势稍缓,才狼狈不堪地回到了行营。
入了大帐,內侍们急忙侍奉他除下冕服,热汤沐浴。等他更换好干净的常服,扶苏与章邯、蒙毅已经恭敬地立在了帐内。
“都换了干净衣衫了吗?”嬴政倚坐几案旁,扫视了一眼。
“回父皇,都已经换好了。”扶苏拱手答道。
嬴政点点头,脸色却有些难看:“突遭暴雨,令人措手不及,你们都注意一些,不要冻出病来。之后还要过芝罘、登琅邪,必须保持振奋,不可在国人面前丢了精神。”
扶苏等人又立刻抱拳:“是,臣谨遵陛下之意。”
话音方落,令官蹭蹭进了来,说是赵高求见。
嬴政似乎早有预料,微微颔首示意令官将人给带进来。
赵高趋着步子,脚下生风一般进了来,待叩拜之后又俯着身子乖顺地向扶苏揖了礼。
“如何?”嬴政微微闭着眼,看起来有些疲倦。
赵高连忙回身站正:“回陛下,那些儒生们没有随驾登山,所以都得以避开这次暴雨。臣方才去他们的营帐看过了,毫发无伤,陛下放心。”
“嗯,那就好。”嬴政双手揣在身前,似乎是因为受了雨觉得冷,“这些人名望甚高,堪为天下人的表率,朕请他们来就是想笼络他们,让他们为帝国效力,所以礼数必须要周到,切不可让他们觉得受到了怠慢。”
“是,臣明白。”赵高依旧俯着身子,脑袋却悄悄抬了起来,飞快地瞄了一眼闭目养神的嬴政,“只是……臣担心陛下这番好意怕是要付之东流了……”
嬴政猛地睁开眼睛,继而又微微眯了起来,如利剑一般钉在赵高脸上:“什么意思?”
赵高猛地一缩脖子,复又俯下头去:“陛下,臣听到一些不太好的话……那些儒生们本就对您撇下他们耿耿于怀,眼下听闻您遇上暴雨,便大肆讥诮,嘲笑您……”
说到这里,他猛地止住了话头,似是有所顾忌。
“有话直说。”嬴政拧紧了眉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里竟满含着杀机。
赵高仓皇跪下,一头磕在地上:“陛下息怒,那帮儒生说您狼狈如丧家之犬。”
赵高的言语里带着深深的颤栗,想来也是已经预感到了嬴政的暴怒。扶苏与章邯、蒙毅亦是吓得面如土色。嬴政为秦王时便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贵为天下之主,怎么能容忍这般肆无忌惮地嘲弄?这次东巡,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彰显大秦的国威、始皇帝的荣耀,这些儒生的言行无异于迎头给了嬴政一棒,让他颜面尽失。
然而嬴政半天没有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赵高蜷缩在地上的背影。若不是剧烈起伏的胸口和隐隐爆发的额角青筋,章邯几乎以为他是背过气了。
赵高吓得不轻,可他看不见嬴政的表情,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只好瑟缩着不敢乱动。
“他们还说什么了?”嬴政终于开了口,嗓子明显有些喑哑。
“没……没什么了。”赵高暗自喘了口气。
“呵。”嬴政冷冷笑了一声,“这些饱读诗书的大儒们竟然也如此小气,不过是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便如此计较。”
见他似乎并没有拍案而起的迹象,扶苏心中安下一些,连忙顺着他的话头劝道:“父皇说的是。天下大定,泰山封禅,这些名儒也想借着这样的盛事抬高一下自己的威望。如今父皇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定然存了些不满。不过,此次东巡主要为的是收服天下人心,这个时候不宜与儒生们闹僵。依儿臣之见,倒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此事不曾发生过。”
嬴政微微垂着眼眸,没有回应。扶苏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的话听了进去,只好静默一旁,等着他的决断。
过了片刻,嬴政猛一抬头:“章邯,将朕的太阿剑取来。”
章邯随即从兰錡上将太阿剑取了来,双手奉上。他不知道嬴政为何忽然要取配剑,然而剑为杀器,这让他心中忐忑不安,便趁着奉剑的时候轻声恳求:“陛下请息怒。”
嬴政瞥了他一眼,伸手取剑。章邯默不作声看着他手中的动作,待手指从宽大的袖口中露出来时,虎口处赫然印着一个鲜红的血痕。
血迹未干,殷殷泛红,明显是他自己用指甲掐出来的。章邯顿时明白过来,方才他表面上虽波澜不惊,但内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雷霆万钧。
想到这里,他不由为扶苏方才的大胆进谏抽了一口冷气。
嬴政将太阿剑握在手中,倏然拔出一截,清冽的寒光折射在他的眼中,迅速形成一道光弧,眨眼间消失不见。
“太阿虽负盛名,但锋芒太甚,令人望而生畏。”他一边说着,又利索地回手收剑,只听一声清脆的嗡鸣如流光一般泻了开去,“死在太阿剑下的亡魂太多了,朕不想再让它染血。”
说完,他缓缓吐了一口气,将太阿剑放好,重新倚在凭具上。
“赵高,你奉朕的口谕再去看望一下那些名士大儒,给他们送些金银玉器,就当是对他们此行的赏赐。记得告诉他们近来多风雨,虽然这次侥幸避开,但下一次就不可知了。你要提醒他们,不要肆意走动,免得被淋了雨,会被人嘲笑如丧家之犬的。”
说这话的时候,嬴政神态平和,末了竟还隐隐带着些玩味的戏谑之意,仿佛方才内心中如烈焰奔腾的怒气从未存在过一样。
赵高领了命,匆匆忙忙挪着碎步退了出去。
待他的影子彻底从门帘上消失,嬴政才缓缓抬头看向扶苏。
“方才你说要收服人心,这没有错。但收服人心绝不意味着毫无底线的妥协。对于六国遗民,要能容,也要能管,恩威并施方可令其服帖。朕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大开杀戒,但也绝对不能容许他们肆无忌惮地拿朕的颜面和帝国的颜面取乐嘲讽。收与放之间的微妙平衡,你还需再多想一想。”
扶苏涨红了脸,拱手答道:“是儿臣设想不周,谢父皇教诲。”
嬴政轻轻嗯了一声,面上浮起一丝倦意:“今日你也折腾许久,想必也累了,让蒙毅送你回帐吧。”
扶苏也看出了他的疲累,顺从地应道:“是,父皇也早些休息。”
说罢,他便与蒙毅一道出了帐去。
身为中郎将,章邯理当随时护卫嬴政的安危。此时见他意兴阑珊,章邯小声试探:“陛下,臣扶您上榻休息吧。”
“朕不困。”嬴政微微摆了摆手,虎口处的血迹似乎已经干涸了,凝成暗红色的小痂,“你说,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彻底地收服人心呢?”
章邯猝不及防,没有想到他会和自己议起如此郑重的话题,不免有些愣怔。
嬴政瞄了他一眼,似乎并没有打算要从他口中得到什么答案:“当年韩非说过,六国毕、天下一,六国遗民最怕的就是朕待他们不能一视同仁。世上万物,唯有法最为公平,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所以他让朕以律法治天下,求得民心的安定。朕深以为然,却又深深忧虑。六国并无法治根基,如此短时间内若是强硬适用,难免不会适得其反,引起六国遗民的抵制。仁义教化并非不可用,只是不可滥用。朕想借着这次封禅拉拢齐鲁儒士,希望他们可以为我所用,替朕缓和一下紧张的局面,然而……”
嬴政叹了口气,有些迷茫,又有些失望。
章邯见状,怕他忧心过重伤了身体,赶忙劝道:“陛下,儒家有云欲速则不达。人心不比疆土,疆土可见,可以用武力取之,然而人心不可见,更难以捉摸。天下人所处位置不同、见识不同,无法如陛下一样及时窥见天地间的大势。他们有抵触、有反复亦是正常,毕竟华夏裂土分疆已百余年,许多人虽深受战乱之苦,却也早已习惯了这分裂的乱世。陛下无须着急,只要让天下人再过上几年安生太平的日子,他们一旦回过味来,便能明白您的苦衷了。”
“再过些年?”嬴政淡淡苦笑,“以前昭彤最爱屈子,朕也看过一些,离骚中有句话让朕想来甚是心惊。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章邯心头一惊,不知他为何突然发此惆怅。
“陛下春秋鼎盛,何来这样的哀叹?”
嬴政转眼看他:“你们都长大了,蒙毅都已经成家了,朕还能不老吗?”
章邯只觉鼻间酸涩,刚要说话又被他拦住。
“朕知道,有些人在背地里说朕狂妄自大,竟敢自称始皇帝,以求二世、三世直至千秋万代。其实,朕身为人主,亲眼见证了多少宗庙社稷归于尘土?千秋万代,那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罢了。朕虽有傲气,却并不会痴心妄想。”嬴政缓缓说着,语气却比方才坚定了许多,“朕只是想告诉天下人,华夏一统乃为天命,顺应天命,万世永昌。”
章邯怔怔地望着他,脑中反反复复回荡着这句话。
“华夏一统乃为天命,顺应天命,万世永昌。”
这是秦国的宿命,亦是华夏的宿命。
说完这句话,嬴政似是松了口气,将心口憋了许久的阴郁一扫而尽。
他朝章邯点点头,扶着几案站起身:“果真年岁不饶人,还是累了。”
章邯立刻上前将他扶住:“臣扶您去休息。”
嬴政的手背如冰一般寒凉,手心里却又烫的惊人。
章邯惶恐地看过去,如此近的距离,一眼就能看清他鬓发里丝丝分明的斑白。
“陛下,您这是受了风寒。臣这就去请夏御医过来。”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