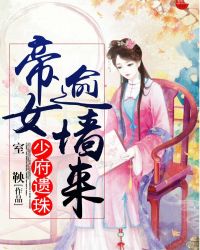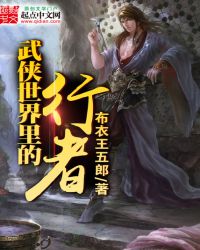第七十八章 莫若勿为
秦王二十年秋,原韩国旧都新政爆发叛乱,王翦分兵平乱,很快便将这股势力压了下去。嬴政怒不可遏,命廷尉李斯严查流放各地的韩国王室宗亲与旧臣。一个月后,李斯向他做了详尽的禀报,令他震惊的是,昔日的韩国公卿几乎个个都贼心不死,他们暗中勾结蠢蠢欲动,一心要为韩国复国。
这一次嬴政再无恻隐之心,除了曾经的韩王安之外悉数诛杀。韩安迁往陈县,被重兵监视把守,再无任何自由。
章邯心里明白,荆轲行刺的恐慌虽然过去,但嬴政对姬丹的所作所为依旧无法释怀。经历过旧友的反目成仇,他越发认清统一之路上的障碍,这些潜伏的危机远超他当初的想象。他为自己的轻敌而懊悔,并因此而加深了对六国宗室的忌惮。既然怀柔之策不能笼络人心,那么他索性对自己的敌人铁腕相向。诛杀韩国公卿,软禁韩安便是他做出的第一步改变。
也正是因为这次不成功的刺杀,令嬴政剿灭列侯的决心更加坚定。
秦王二十一年,王翦大军攻占燕国国都蓟城,副将李信一路追击燕太子姬丹,姬丹走投无路自尽身亡。李信取下姬丹首级送回咸阳,并趁胜追击将燕国境内最后一股抵抗势力彻底铲除。
燕王见大势已去,率亲兵逃往辽东,继续苟延残喘。
除韩国彻底覆灭之外,赵国和燕国皆大势已去,剩下一小撮游兵散将无法再对秦国构成心腹之患。姬丹已死,嬴政算是彻底地出了一口恶气。他重重赏赐了年轻的将军李信,志得意满地将眼光投向了南方那个最难啃的硬骨头——楚国。
楚国不同于韩、赵、燕,虽然从楚怀王之后国力就一蹶不起,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楚国幅员广袤,丘陵、河流纵横交错,其间多烟瘴之地,若想一举将它拿下,绝非轻而易举。
更何况,楚国与秦国还是世系的姻亲,眼下秦国的王后便曾是楚国的公主,而秦国的王储亦有着一半的楚人血统。华阳太后虽然倒台,但秦国朝堂上下仍有不少楚系大臣,如何安定他们的心思,不引发国中的内乱,也是嬴政在攻打楚国前必须想清楚的事情。
面对楚国,嬴政虽然信心满怀却不敢轻视大意。他亲自给王翦写了书信,征求关于伐楚的建议。王翦也认为时机成熟,便让其子王贲率领一部分大军转而南下,以图做好先期的准备。王翦行军素来稳扎稳打,绝不贸然激进。他知道南下必途径魏国,便指示王贲只挂以攻伐楚国的名义,不要惊动魏国,待魏国放松警惕时再一鼓作气顺势将其拿下。
王翦的战术得到了嬴政的认可,他全力支持这一计划。但在一件事情上,君臣二人却意外地出现了分歧。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副将李信亲自将姬丹的人头送回咸阳时,嬴政大为满意,并当庭夸赞了李信的勇武。是时正逢嬴政考虑攻楚之事,便趁兴问他攻楚需要多少人马。李信年轻气盛,又刚打了胜仗,自然意气扬扬胜券在握,当场便夸下海口,说秦军眼下士气正盛,只需二十万便可将楚国彻底剿灭。
嬴政听了这话虽然也暗自欢喜,但他不敢轻信李信的话,便又写信向王翦询问一番。没想到王翦的回复却是斩钉截铁一般:若要拿下楚国,至少需要六十万大军。
六十万?嬴政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不由拧起眉头。
虽然秦国 军力、国力乃列国之首,可连年征战,民力、军力皆有耗损。饶是天下第一强国,此刻让嬴政立刻凑足六十万大军,对他而言也有些难度。
一时之间,他犹豫不决,从本心上而言,他认可王翦沉稳的战术,也坚信六十万大军一定能彻底将楚国铲除。但王翦实在太稳了,他的用兵思路一成不变,从没有做过任何的突破。若是以前,嬴政就算咬着牙也会给他凑齐这六十万人,可李信已经打了包票,二十万足以灭楚。
嬴政有些心动,既然秦军眼下势如破竹,列国又皆是闻风丧胆,为何不试上一试?
左右权衡之下他拿不定主意,便想着再与蒙恬商议一番。章邯得了令去请蒙恬,他前脚刚走,后脚赵高便入了政事殿。
依礼行过礼,赵高从袖中掏出一副卷轴,双手呈了上去。嬴政接过卷轴,放在书案上铺开,见到上面的字不由拧起眉头:“这是什么?”
赵高低眉顺眼地躬着腰身,据实答道:“回王上,这是近半个月出入昌平君府第的人员名单,除了有朝中的楚系大臣之外,还有一些楚国王族和重臣派来的家臣。”
“楚国来的?”
“是。”赵高不敢隐瞒,但又有所顾忌,犹豫着晃了晃脑袋。
见他这幅畏畏缩缩的样子,嬴政很是不满:“说!到底怎么回事?”
赵高顿了顿,沉下一口气小声回道:“自从王上命廷尉李斯大人严查韩国公卿,将图谋不轨之人悉数斩首之后,列国之人、尤其是列国王室及朝臣,无一日不是心惊胆寒。眼下王上要灭楚国,楚国的公卿们怕国灭之后性命难保,便偷偷派人来到咸阳,试图通过买通昌平君来换得家宅平安。”
“哼!”嬴政重重嗤了一鼻,“国将不存,这些人不想着如何抵抗,却只顾自保活命。楚王有这样的臣子,楚国想不灭都难。”
“王上说的是。”赵高忙点头附和,“楚国君主荒淫无道,臣子为争私利互相倾轧,无人愿意为社稷而死,想来我秦军铁骑还未到,他们自己就亡了。”
听他这么一说,嬴政眼神忽然闪了一下,脸上多了些玩味之意:“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赵高不胜惶恐,急忙跪下谢恩,末了却又试探着说道:“王上,臣有一事不明,思来想去心中不甚安稳,可否请王上明示?”
嬴政不动声色地将卷轴合上,倚在凭具上似是慵懒地盯着他:“何事?”
赵高吞了口唾沫,又小心翼翼瞄了他一眼:“王上既然已经命蒙恬将军暗中监视昌平君,为何又瞒着他让臣去插上一手?臣愚笨,难道王上是觉得蒙恬将军会袒护昌平君吗?”
见嬴政忽然变了脸色,赵高戛然而止,猛地俯身磕头谢罪:“臣该死,不该擅自揣测王上的用意。臣该死,请王上恕罪。”
嬴政脸上的怒意一闪而过,他一手撑在凭具上,食指抵着太阳穴,眼睛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赵高。
“那你觉得蒙恬会不会袒护昌平君呢?”
没料到嬴政会将这个问题又踢了回来,赵高错愕地抬起头来,刚一对上他毫无情绪的眼神,又赶紧趴了回去:“臣……臣不知。”
“你是不知还是不敢说啊?”嬴政笑了笑,那笑意令人发毛,“你不说寡人替你说。蒙氏与扶苏关系甚为密切,王后是楚国的公主,与昌平君有血脉之亲,所以你便认为蒙恬会因为顾及扶苏而包庇昌平君?”
这一针见血的话令赵高不知如何去接,没有想清楚之前,说错一句话都会要命,他打定主意,伏在地上一声不吭。
见他不说话,嬴政收起笑意,探身向前:“抬起头来。”
赵高匆忙起身,与他对视的瞬间肩头忍不住一个颤抖。
嬴政沉默无语地看着他,想了片刻才缓缓问道:“荆轲行刺之后,是你去向赵夫人通风报信的吧?”
这虽是问话,但他语气笃定,似乎早已知晓内情。
赵高被吓得脸色惨白,呼吸也急促起来。
“臣不敢欺瞒王上,当日确实是臣去通知的夫人。夫人一心系在您身上,臣是害怕她得到消息以后胡思乱想,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找了人亲自去告诉她,说王上虽然遇了危险,但福大命大逃过一劫,请她安心。可没想到夫人还是放心不下,坚持非要来探望您,所以才带着胡亥公子赶了过来。”
赵高这话不算胡诌,但也绝非全部实话。当时他第一时间派人去告诉赵夫人,就是请她赶在王后和扶苏之前赶到政事殿,以讨好嬴政、表明忠心。那日朝臣们都聚集在政事殿,只要她能赶在王后之前,便能突显出她对秦王的关心大大超过王后,令王后和扶苏在众臣面前难堪。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计划正好触动了嬴政敏锐的神经,不仅没有让赵夫人和胡亥大出风头,反而被灰溜溜赶了出去。相反,王后芈昭彤虽姗姗来迟,但嬴政却丝毫没有怪她,更是将她留在寝殿,让她照顾了自己整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嬴政与芈昭彤越发亲密,不论实际上如何,表面上来看,他似乎不再提防这位有着庞大楚系背景的妻子,而刚刚才有些起色的赵夫人和胡亥则一夕之间被打入了冷宫一般。
事后赵高也曾细细推测嬴政的心思,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扶苏在嬴政心里的地位依旧远超其他诸子,无人可以撼动。他为自己的失算懊恼不已,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只不过在时机未成熟之时,他绝不会再将矛头直接对准扶苏。
所以,他将自己的真实意图藏了起来,并将整件事归结为赵夫人的不懂事。他心里明白,赵夫人再不济也是秦王的枕边人,嬴政素来欣赏她的单纯天真,绝不会揪着这件事大做文章而怪罪她。
果不其然,嬴政白了他一眼,言语里却没了方才咄咄逼人之意:“她一介女流,不懂前朝之事,你一个内廷秘书,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寡人遇刺,王后还未到,她便哭哭啼啼赶过来,若是传扬出去,外人还以为她是刻意要抢王后风头。后宫与前朝一样,皆有严格的秩序,你这么做就是让她坏了秩序,徒遭骂名罢了。幸亏王后性子随和,不曾介意此事,否则寡人也救不了她。”
事实上,嬴政也刻意将自己最真实的意图隐瞒了起来。这件事里令他最为紧张的是扶苏的王储之位,可他却撇开扶苏不谈,只论后宫尊卑,并大有对赵夫人的关切之意。
听他口风如此一转,赵高心里有了底,瞬间有了些信心:“王上教训的是,臣身为胡亥公子之师,却替他和赵夫人招来祸端,实在是罪该万死。”
提及胡亥,嬴政的眉头又微微拧起:“还知道自己是胡亥的老师就好。寡人让你去教胡亥,是因为看中了你满腹的才学。可你三番两次针对蒙恬,寡人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有些吃不准啊。”
赵高一愣,随即狡辩道:“王上明鉴,臣没有针对过蒙将军……”
“行了。”嬴政猛一挥手,不想再听他叫屈,“姬丹出逃之时,你难道不是故意为难蒙恬,将责任推到他身上?这次让你去查昌平君,你不一心一意完成任务,反而将满腹心思都放在蒙恬身上,还怀疑他会包庇昌平君。寡人说的这些,可有一件事冤枉你?”
赵高早就猜到嬴政已经对自己的用心有了察觉,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直白地悉数挑明开来。在嬴政身边日久,赵高早就摸准了他的脾气,这个时候抵赖是没有用的,只有以进为退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赵高伏下身去,忍不住痛哭流涕:“王上明察,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臣是个小心眼的人,自己出身卑微,若无王上赏识,不过如蜉蝣草芥。蒙将军是将门之后,本来出生就好,又与王上您交情笃深,臣又羡慕又嫉妒,所以有时会忍不住挑他的不是。臣小肚鸡肠,不配成为您的臣子,可臣为难蒙将军只是想让他难堪,绝无害他之心。臣知错了,真的知错了。”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