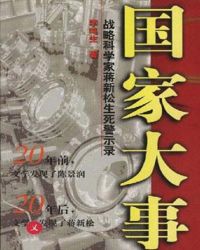第六段搞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段搞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
1958年底,蒋新松从河北农村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蒋新松尽管还是右派,但鉴于他在农村劳动改造中的“表现”,再加上他的业务能力突出,当时工厂里有许多实际的问题很需要像他这种既有才干又肯苦干的人去解决,所以他被重新分配到了控制理论和生产过程自动化研究室。
这一时期,蒋新松的脑子里装了一大堆的问题,如浮夸问题,搞饭问题,老百姓的肚子问题,等等等等。但他不敢把这些问题说出来,更不敢去质问有关部门或某个领导,而只能把这些问题偷偷存放在脑子里。每天,他依然沉默不语,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即便偶尔说上一句话,也格外的小心谨慎,如同一个在空中踩着钢丝走路的人,生怕有人会在他的背后突然再横插一竿子。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也逐渐冷静下来。他想,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让它去吧,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妥地把握好自己的今后。再说,大丈夫就得能伸能屈,当年的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才27岁,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最要紧的是要干事情,不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只要能争取到于工作的权利和机会,只要能安安心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右派这顶帽子就是戴它一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他和课题组一起,到天津东亚毛纺厂和首都石景山钢铁厂等,搞了一系列的自动化革新项目。在几十个人组成的课题组里,他的业务能力公认第一。因此,这个课题组的组长虽然不是他,但主要的科研项目,主要的好点子、好主意、好方案、好规划,几乎全都出自他的脑袋,他的手笔,他实际上成了一个最权威的技术负责人。而当时所搞的几个很有影响的科研项目,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蒋新松,始终是在受到某种监视的情况下工作的。更为荒唐的是,他所干出来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非但没有他的份儿,而且有关人士每次向上汇报工作成果时,连他的名字也不会提一下,也没人敢提一下。对此,他非常清楚,也很有感觉,有时想起来也难免涌出几分酸楚。但他总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说:自己是个右派,能让干工作,就不错了,就该谢天谢地了,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计较个人的回报和他人警惕的目光呢?所以他每天只管干活,千好活就行了,至于名利之类的事情。他从不考虑,从不计较,也从不在乎,好像那是别人追逐的事业,与他无关。
1961年后,对蒋新松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起来。到了后来,有关方面还发出指示:像蒋新松这样的右派分子,不宜到科研现场去工作。蒋新松便因此而闲置起来。
可蒋新松是一个从来就闲不住的人。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两天两夜的书,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不让我去工厂搞技术革新(可能是怕他这个右派分子搞破坏),那在家搞搞理论研究工作总是可以的吧?于是他便找到当时的室主任童世璜,要求搞点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童世璜主任觉得蒋新松确是一个人才,便给了他一个自动控制理论方面的研究课题,让他自己去研究。据童世璜先生后来介绍,这个课题在60年代初期是自动控制理论领域中最前沿的一个课题,有很大的难度,在此之前有人搞过,但一直没有搞出来。
此后,蒋新松便一心扑在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上。
1962年,鉴于蒋新松几年来态度端正,服从“改造”,工作出色,生活俭朴,既没有任何“反动言论”,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打现行活动”,所以经过组织审批,终于为他搞掉了压在头上整整5年的右派帽子。
尽管这时的蒋新松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冷静而清醒的认识,但宣布给他摘帽那天,他还是感动得流泪了。
一旦搞了右派帽子的蒋新松,犹如推翻了压在心上多年的一块石头,有一种突然走出了监狱大门的感觉。他流着惊喜的泪水,把这一消息马上写信告诉了母亲,告诉了妻子。母亲和妻子接到信后,欣喜万分,来信叮嘱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
此后,他在学习和工作上,更加积极了。不久,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终于写出了他所搞的那个研究课题的论文。
他将论文交给了童世璜主任,童世璜看后非常高兴,认为很有价值,并和他一起又重新写了一稿。论文最后定稿署名时,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排在了前面。
这篇论文以室的名义,很快报到了自动化研究所。刚从美国回来的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杨家墀看了后,大加赞赏,并向国外有关部门做了积极推荐。后来,这篇论文被国外一些专家普遍看好,通过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决定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计量学会年会上进行宣读。
蒋新松得知这一消息后,犹如一个长年生活在阴风苦雨中的人,有一天出门时突然望见了一轮鲜红明媚的太阳,这太阳让他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感到晕眩,以至于竟不敢相信这跟前的太阳到底是不是真的。
的确,他自被打成右派那天起,似乎就再也没有感受过“太阳”的“温暖”以及“组织”的“帮助”与“关怀”了,同时也再没人敢说他是“国家的人才”,更没人把他当作“国家的人才”了,他个人的人格、价值、荣誉、尊严等,仿佛全都随着“右派”这个莫名其妙的字眼的出现,统统被一扫而尽!可现在,他写的论文居然得到了国内外专家们的承认,而且还要代表中国站在国际讲台上去向世界宣读,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扬眉吐气的大事情啊!5年来,他总算可以用手摸着自己的良心,长长地出上一口气了。因此,他又急忙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了母亲,告诉了妻子,并幻想着自己即将登上国际讲台的种种豪迈情景。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由于他是“摘帽右派”,不但没有资格站到国际讲台上去理直气壮地宣读自己的论文,而且论文署名时连他的名字也不能排在前面。后来,尽管他的这篇论文最终也在国际讲坛上作了宣讲,可站在大洋彼岸讲坛上的,却是另一个身影。
空高兴了一场的蒋新松这才恍然大悟:搞了帽子的右派,其实还是右派,只是不再叫右派而叫“摘帽右派”而已。一当他明白了这点后,就像有人在他本来未愈的伤口上又撤了一把盐,令他不寒而栗!
显然,像这类的事情搁在谁的头上,谁都会想不通,谁都会感到很冤枉,很窝囊,很不公平,会因此而生气、愤恨,甚至暴跳如雷,死也要去讨回一个公道。蒋新松当然也因此而生气,而愤恨,而暗暗骂过娘,甚至在得知此事的当天晚上,还气愤地扯着自己的头发质问苍天:命运啊,你为什么对我总是如此不公?!然而,在那个年代,诸如此类的事情千千万万,多如牛毛,不正常即正常,奇怪即不奇怪。再说,他一个?“摘帽右派”,即使有理,又找谁说去?能找谁说去?敢找谁说去?因此,几天的痛苦过去之后,他便开始平静下来。他认为,在这个世上,千奇百怪的故事每天都会出现,应该这样而常常又是那样、应该公平合理而恰恰又不公平合理的事情,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如果什么事情都公平合理了,什么事情都完全符合个人意愿了,那么专供人类生存、折腾的地球或许就不存在了——这,说不定正是这个世界的复杂与微妙之处呢!
一当想通了这点之后,他很快又从低迷的状态中恢复了正常。他的论文虽然自己没去国外宣读,但毕竟已经被人宣读了,毕竟对自己的价值是一次证明,毕竟让全世界有关的专家们听到了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迫切心声!于是,5年来他第一次有了一丝欣慰的感觉,同时也使他更加自信。他很快将此事忘于脑后,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并干好什么,至于那篇论文的事情,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元气的逐渐恢复,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又被列入了议事日程。出于工作的需要,蒋新松又被派往兰州炼油厂,参加由国家科委主持的一个自动化试点工作。
兰州的日子是难过的。兰州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还有那依然对他暗中进行监督的冷冷目光,都令他感到极为不适。
但蒋新松还是蒋新松,只要让他工作,只要让他干活,他就高兴,他就兴奋!而且,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不谈报酬,不计名利。所以到了兰州炼油厂后,他经过实际考察和分析研究,又对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测试问题提出了有独创性的见解和改革方案,并亲自担任了现场副总指挥。
1965年初,他提出的使用伪随机码进行测试的方案终于获得成功。这是国际上最早在大型工业对象中使用的一个最先进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使兰州炼油厂向着自动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且比日本早了两年。
但搞了帽的右派毕竟还是右派。他的才干一旦得到显示,马上就有人看不惯,想不道,很难受。于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听群众意见”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又一顶一顶地扣在了他的头上。有人还给北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写信,向党组织不时地反映他在兰州的“表现情况”。甚至,除了一两个月对他定期“帮助”一次外,有人还组织现场批判会,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
面对这些,蒋新松的选择是:除了工作,就是沉默。
1965年10月的一个夜晚,蒋新松扛着沉甸甸的书箱和简单的行囊,从北京火车站路上了去沈阳的列车。
也许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也许蒋新松是摘帽右派,总之,有关部门做出决定:蒋新松从北京中国科学院,调往东北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即后来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临行前,有关人士找他谈话,问他从北京调到东北有什么想法?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什么想法,只要让我工作,去哪儿都行!”
是的,身为一个“摘帽右派”,他能有什么想法呢?再说,他又敢有什么想法呢?即使他有什么想法,他的想法又会被谁当作一种真正的想法去听去想去办呢?留北京,去东北,对他这种早就被社会、被生活、被同类所抛弃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北京,当然是他从小就神往就景仰的地方,而今也依然令他梦牵魂绕,难舍难分。然而,从1957年那个黑色的日子起,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抗战”过去了,偌大的北京对他这个“小右派”来说,难道还有一点点与之相关的实在意义吗?去东北,对他这个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来说,那刺骨的北风、飘飞的大雪、粗糙的口粮以及半热半凉的炕房,虽然肯定极不适应,但一旦躲开了北京政治的旋涡,不也少了几双监督的冷眼,多了几分东北的热情吗?更何况,那儿还有事可干,有事让干。既然如此,去又何妨呢?
列车呼啸着行进在北方广袤的平原上。这是一个寒气提前到来的秋天。坐在车上的蒋新松如同每天上班一样,不急不躁,自然正常,除了身边的书箱和行囊,看不出一点出远门的样子。他上车后,就捧着一本砖头厚的外文资料独自看着,既不向身边的人打听什么,更不首先谈起什么,甚至,他连目光也懒得扫视一下,似乎整个车厢除了他自己,别的人统统都不存在;而他身旁的人见他一副冷漠异常的样子,自然也就不好主动和他说话了。
这样一来,坐在车上的蒋新松反而倒感到很正常、很和谐了。因为8年来,冷漠的眼光他见得实在太多了,以冷漠对待冷漠,用无视对无视,他认为半斤八两,公平合理。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一人独居一隅,从不主动与人说话,从不主动与人接触。他不愿意再去搭理这个世界,也懒得再去搭理这个世界,更不想再去惹怒这个世界。当然,他也不希望这个世界再来惊吓他,骚扰他,整治他,坑害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8年如此,他早已从不自然到自然,从不习惯到习惯。
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直到列车服务员热情地送来了开水,蒋新松才将埋在书本里的一张瘦脸抬了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他的对面坐着几位年轻人,看样子,是刚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去的大学生。他们个个朝气勃勃,踌躇满志,仿佛东北那辽阔无垠的黑土地上,尽是等着他们去挑去拣的希望与金子。
“和我当年一个样!”蒋新松冷冷地在心里叹了一句,便快速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他忽然想起孔子“三十而立”的话来。是啊,人生如梦,光阴似箭,掐指一算,自己已是34岁的人了。可叹的是,自己不但没有“立”起来,反而早就被打倒在了地上。现在,命运的列车又不知将他抛在何处,扔向何方?
想到这些,蒋新松不免多少有些怅然。他偏过头,隔着玻璃窗望出去,深秋的北方,天朦朦,路朦朦,连空气也尽是一派朦朦胧胧。他禁不住感叹一声,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车到沈阳后,蒋新松行囊一放,便去东北自动化研究所报到。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刚报完到,所里有关领导便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参加科技攻关小组,准备去鞍钢报到。”
蒋新松一听,既感到受宠若惊,又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知道,鞍钢是国家重工业的中心,是全国重工业的“龙头”,能在那儿工作的人,个个都是思想红、觉悟高的“红五类”。而自己刚到一个新单位,又是个“摘帽右派”,还是个“嫌疑分子”,怎么所里领导就对自己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呢?怎么就把这样一个建功立业、大显身手的机会直端端地送到手上呢?拖思来想去,最后也没闹明白,这次去鞍钢,到底是被重用,还是被利用?
其实,早在1965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就决定将鞍钢冷轧钢板厂的设备完善化、自动化列为国家科委和经委直接控制的重点攻关项目,并将自动化部分列为国家科委技术发展10年规划项目。如此一来,全国各路科技名将纷纷云集鞍钢,很快拉开了鞍钢科技大攻关的战幕。而东北自动化研究所对蒋新松在自动化方面的突出才干早就有所耳闻。尽管他们也知道蒋新松是个“摘帽右派”,但蒋新松的业务能力和近几年在北京、天津、兰州等地所做出的成绩,他们是心中有数的。更何况,研究所已经领受了鞍钢冷轧钢板厂自动化的研制任务,倘若蒋新松这样的骨干不去,又让谁来担当如此重任呢?
就这样,蒋新松第一次闯进了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鞍钢。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