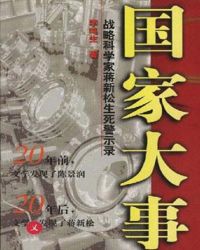第七段10年鞍钢,10年尴尬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七段10年鞍钢,10年尴尬
鞍钢,1917年始建于日本人之手,但28年后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又被它的创建者日本人几乎捣毁成一片废墟。
据说,日本撤离鞍钢时,一位日本工程师曾叫嚣说:“现在,鞍山烧钢铁的炉子都留给中国了,让他们去种大豆、种高粱吧!”
1949年,一位外国专家来到鞍钢,当他沿着鞍钢的厂房转了一圈后,也当场断言道:“鞍钢想要恢复生产,至少需要15年!”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理睬日本人的狂言乱语,也未在意外国专家的草率断言。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鞍钢便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鞍钢那日夜飞溅、光芒耀眼的钢花,曾照亮了中国工业的半个天空。现在,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前进的步伐。国家又组织了科技界的精兵强将,在鞍钢拉开了科技攻关的大幕,凡被选派到这儿的科技工作者,无一不想在此大展身手,为鞍钢、为历史留下光彩的一笔!
蒋新松当然也想。
那天,当他第一眼望见鞍钢那一排排雄伟壮观的高炉时,就被那生龙活虎般的场面震撼了。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后,尽管依然心怀天下事,“不敢忘忧国”,但他的名字毕竟被人从“国家”的花名册上一笔勾销了,国家大事也因此而与他越来越疏远了;他如同一个“失恋”的“恋人”,多年来只有苦苦地“单相思”。现在能让他来鞍钢,对他无疑是一种信任,至少说是一点小小的安慰。因此,当他面对鞍钢那热气腾腾、大干快干的火热场面,面对站在炉火前认认真真地挥动着煤铲的工人师傅,一颗压抑多年的心一下就被感动了。在那一时刻,他追求功名、渴望拼搏、渴望成功的激情又开始在心中涌动起来,不知不觉中又把自己和国家的大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后来说,不管怎么讲,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国人,毕竟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毕竟还有生存、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权利,甭说自己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就是作为共和国一个普通的公民,也有责任有义务为鞍钢的建设出上一把力!
当然,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毕竟是个“摘帽右派”,毕竟是个被临时启用的“人才”,不可能与其他科技人员相提并论,一视同仁。因此,他住进鞍钢后,无论说话还是做事,既不大张旗鼓,也不锋芒毕露,想,也只有偷偷地想;干,也只能夹着尾巴干。为了强行压制自己的个性,管住自己那张嘴巴,以便在鞍钢站稳脚跟,他还特意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
第一,只干不说;
第二,干了也不说。
而后,便一头扎进了鞍钢冷轧钢板厂。
冷轧钢板厂是鞍钢很重要的一个厂。这个很重要的厂有一台很重要的设备,叫1200可逆冷轧机。1200可逆冷轧机是中国用相当昂贵的价格从苏联进口的一台轧钢机。这台轧钢机不光对鞍钢来说是十分金贵的“独生子”,对全中国而言也是唯一的一台“国宝”,若是它一旦闹点情绪,发点脾气,突然来个“大罢工”,不仅对鞍钢是致命的一击,对全国冷轧钢板的生产也会造成瘫痪!多年来,这台设备为鞍钢、为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鞍钢的重要“功臣”。但它的尾部自动安全停车问题,却始终是个问题,长期以来全靠工人师傅们用人工操作的办法去处理。这种人工操作的办法很不科学,也极不安全,还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工人师傅们每次操作处理时,都非常紧张,非常小心,心理压力非常大,久而久之,对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当年,苏联的专家对此曾经做过多次调试,只因在一次调试中险些闹出大事故来,以后便再也没人敢去问津了。
蒋新松去后不久,这个问题便引起了他的注意,并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攻克这个难题。他外表看上去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暗中却开始了积极的行动。经过一段时间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后,有一天他终于对1200可逆冷轧机的自动停车装置问题,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改进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不仅提出了总体的设计思想,而且还创新地提出了用引进速度提前量的控制原理,去研制自动准确停车装置问题。
这个方案提出后,得到了鞍钢和研究所的肯定,也得到了同事们的积极支持,于是蒋新松一头扎在了这个方案的思考与设计之中。
这段时期的蒋新松,虽有幸获得了一份工作的权利,日子却依然过得很不轻松。他刚去鞍钢时,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使用的一律是自带的被褥,生活与工作条件都很艰难。据当年和蒋新松一起在鞍钢工作的张文洁女士说,在鞍钢那段日子,既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又是一段很苦涩的日子。他们每天上班,都要先从住地走上十多分钟的路程,然后坐20分钟的无轨电车(电车上十分拥挤,每挤一次电车,衣服扣子都要挤掉好几个),下车后还得再走上20分钟的路才能到达厂里。刮风下雨,天天如此。他们每月30斤粮,厂里再给补助8斤,但还是不够吃。尤其是蒋新松,家里有了一个女儿,自己的胃口又比一般人强,粮食总是闹饥荒,所以每个月20号剐过,他就老是催促组长说,“该去领粮票了吧,该去领粮票了吧!”蒋新松的组长叫张启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同志,他和同事们不仅在政治上不歧视蒋新松,在工作上支持蒋新松,而且在生活上也总是关心帮助蒋新松。有时一看蒋新松没粮吃了,他就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部分粮票以“借”的名义变相地送给蒋新松;每当月末,为了解救蒋新松以及家里的饥饿问题,他还总是提前一天或者半天去把粮票领回来,然后再第一个优先发给蒋新松。
就在这粮食本来就不够吃的日子里,蒋新松的小儿子偏偏张着饥饿的大嘴哭喊着又来到了这个世界。有了女儿,现在又有了儿子,蒋新松自然十二分的高兴。可儿子刚出生不久,便患了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蒋新松家在沈阳,工作在鞍钢,儿子和工作对他当然都是头等的重要。可按当时的规定,他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为了能照顾上孩子,又不耽误工作,他有时只好晚上下班后从鞍钢赶回沈阳,第二天一早再从沈阳赶回鞍钢。而他所搞的自动停车装置方案,就在他如此拼命的来回跑动中伴着他儿子一天天的成长日渐完善起来。
然而,正当这项研制工作加紧展开之际,骤然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对于这场空前的、突然而至的“大革命”,鞍钢的工人师傅和刚去鞍钢的技术骨干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情,正埋头苦干的蒋新松同样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曾一朝被“蛇咬”的他虽说不是见了草绳就怕蛇,但面对那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史无前例”、不可一世的“大革命”,也难免心有余悸,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更不可能高枕无忧,而总要在自己的脑子里对一些问题画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尤其每次在上班途中,当他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听着那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口号声时,很自然地便想到了1957年,想到了1958年,想到了“大鸣大放”,想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于是,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他,面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只好采取了一种极其冷静的态度:凡“革命”之事,不表态,不参与,不外出,不串联,更不去煽风点火,上蹿下跳,而是每天一言不发,只顾埋头干活。
由于这时的“革命”已压倒了一切,鞍钢有许多人都积极投身到了“抓革命”的“洪流”当中,有些生产自然也就停了下来。蒋新松所在的课题组,不少人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正研制中的数字准确停车装置的几千个晶体管和上万条线路,从焊接到组装,总得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总得有人用手去焊接那一根根的导线,总得有人去把铆钉一颗颗地铆起来。于是,那成千上万根导线和成千上万颗铆钉的焊接工作,就只有靠蒋新松等部分技术人员每晚拼着老命加班加点地干了。
后来,随着鞍钢“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武斗愈演愈烈,蒋新松们的研制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新松只好从鞍钢回到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面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沈阳方面自然也不会闲着。蒋新松回到沈阳时,沈阳方面正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活动。所以他到家的第二天,一张张的大字报使劈头盖脸地扑向了他这个“摘帽右派”。
面对善良的人们炮制出来的一张张恶狠狠的大字报,蒋新松只能一笑付之。有什么办法呢?荒唐年代,派生出来的总是荒唐的逻辑:昨天还是技术骨干,今天就成了批判对象;而无论是让你当技术骨干还是叫你做批判对象,又同样都是“革命的需要”。
蒋新松对此虽然也感委屈,可在政治这条跑道上,他毕竟是一位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听过枪响、摔过跟斗的“老运动员”了。面对眼前的一切,他很冷静,不言不语,不卑不亢,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技术书随时带在身边,鞍钢的自动化工程照想不误。你批你的,我想我的,你革你的命,我干我的事,甚至在一些大批判的会场上,他脑子里还照样想着鞍钢的事情。
后来,就什么事都不让他干了,连技术书也不能看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成了一个活着的“闲人”。但每天看着像河水样哗哗流逝的时间白白耗去,他又实在不忍心,于是便开始自学“毛选”。
“毛选”是那个年代对《毛泽东选集》一个通俗的叫法。有过这段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学“毛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政治景观”,或者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时髦”。其热情,其真诚,其为了一个目的置任何事情于不顾,就像今天的孩子们沉迷于踢足球、玩游戏机或者热衷于学电脑。学“毛选”运动开始之初,应该说全中国的人几乎都是真诚的,认真的,都是自觉自愿的当作一项很神圣的政治任务去执行去完成的。到了后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少人学“毛选”都是图形式,走过场,装模作样,胡弄领导。但蒋新松不是。他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真学,一篇一篇地看,逐字逐句地读,而且钻研得还相当的深。当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叶强后来回忆说,蒋新松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改造世界观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最自觉的。他很用心地重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正因为他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后来才逐渐成熟起来。蒋新松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毛选”一卷、二卷,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了。毛泽东的许多哲学思想,对我影响非常之大,我后来不少重大问题的决策,就是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启发。他还说,当他通读完“毛选”一卷、二卷之后,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最深刻的一点,体会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闻出一条路来,创建了新中国,那么今天的他即使命运再坎坷再曲折,也比那个时候好得多,怎么就不能闯出一条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
到了1967年11月,大概是“革命”革得有点累了,也该促“促生产”了,上面便有指示说,鞍钢的研制工作又可以进行了。于是蒋新松又被通知去鞍钢,组织1200可逆轧钢机准确停车装置的试验。
到了鞍钢后,一看厂里的形势,蒋新松心里就非常清楚,现在搞停车装置试验,由于生不逢时,秩序混乱,具有很大的风险;1200可逆轧钢机全国只有这么唯一的一台,在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日子里,倘若一旦出了事故,他这个“摘帽右派”即使不杀头,也会被抓去蹲大狱的。但他既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又是正被“革命”的对象,如果他不干,岂不又成了铁的罪证?所以他愿干得干,不愿干也得干,别无选择。
好在蒋新松对此有着充分的自信,他对同事们说:“你们就放心地干吧,有事我兜着!”听了他的话,大家很受感动,一个较年轻的技术干部还说:“老蒋,你是结了婚的人,而且还有孩子,万一出了事,我是光棍一条,就让我去蹲篱笆子吧!”而鞍钢方面的师傅们也愿意积极配合,甚至还有人拍着胸脯站出来,主动提出为他分担责任。
面对这么多、这么好的支持者,蒋新松很受感染,多年来在众人面前从不多说一句话的他,那天终于说了一句从1957年打成右派那天起就一直想说的话:“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证明,我是无愧于我的祖国,无愧于我的人民的!”说这句话时,蒋新松仿佛不是在说,而是在喊,像是把10年来的劲儿全都甩在了这句话上,因而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段时间过去后,蒋新松等人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使1200可逆冷轧机自动停车装置试验获得成功!
1200可逆冷轧机自动停车装置试验获得成功,蒋新松在鞍钢名声大震。该装置投放到生产运行当中后,既保证了工人师傅的人身安全,又大大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刺激,使鞍钢的生产率和合格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后经有关专家鉴定,此项工程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其设计水平还堪与国际上60年代末期的同类设备媲美。
略感欣慰的蒋新松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为国家做出的第一件大事,而且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还有幸躲过了一场劫难。
然而,幸与不幸,总是结伴而行。
正当蒋新松在鞍钢的研制工作取得成功之际,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却又开始了。蒋新松因此而接到通知:马上回研究所,参加“清队学习班”。
1968年8月27日这天(这是蒋新松29年后仍能准确回忆出来的一个日子),蒋新松不得不从鞍钢又回到了沈阳。蒋新松的家在沈阳,妻子和孩子在沈阳,回到沈阳,就意味着回到了温暖的家,就意味着将和妻子、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然而,“意味”并不等于。那天,他刚一跨进研究所的大门,就碰上了已经“恭候”他多时的“造反派”。“造反派”见他如期而至,喜出望外,其中有人还上前与他点头打招呼。他以为是因为他在鞍钢干出了成绩,所里派人迎接他来了,心里好一阵感动。可就在他“感动”之际,一块早已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右派分子蒋新松”的胶合板牌子,“咣当”一声使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然后,他被送进了批判会场。
接着,就开始了对他的批判。
有人说。他骄傲,他自满,他目无党的领导;
有人说,他是老右派,是新反革命;
有人说,他对党有不满情绪,时刻都在想着翻案;
还有人说,……
批了两天,批到后来,轮到他说了,他只顺便问了一句:有证据吗?
有人马上便把他在鞍钢当众说过的那句话端了出来:“你要用一生来证明,你是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都在这句简单的话里吗?他哭笑不得,无言以答,也懒得回答。
在鞍钢干出了成绩不但无功,反而有罪,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不过,他心灵的伤疤早已由血红变成了紫黑,面对政治的风风雨雨,他不惊不诧,习以为常,甚至在坦然中也带着一种冷酷的漠然。你要批就批,要斗就斗,不管怎么批来斗去,他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以不变应万变;即使白天刚批了他,晚上他照样偷偷钻研技术,学习业务。他的生命仿佛只有在同这个世界不断的碰撞、较量、抗衡与搏斗中,才能激起血情,蹦出活力,才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英雄本色。为了宽慰和激励自己,他还把作家海明威的话每天在心里默默背上两遍:“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一个人可以被打败,僵决不会被消灭!”
然后,就在心里冷冷地想:历史,难道是凭几个小丑就说了算的吗?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的高潮,蒋新松被定为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一天傍晚,他刚走出会场,一名工宣队的代表便找到他,正式通知他说:“根据组织决定,明天你们全家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你马上回去收拾收拾行李吧!”
毫无心理准备的蒋新松一听,很是震惊。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他始料不及,也痛苦至极。去农村劳动,他并不惧怕,而他一直最怕也最担心的,是让他离开研究所,离开他深深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在他看来,不管给他戴上什么帽子,无论给他加上什么罪名,只要让他搞科研工作就行。可现在突然要他离开研究所,要他放弃正在进行之中的科研工作,他实在难以接受。尤其是鞍钢的一些自动化项目,他心里非常清楚,有些技术问题是离不开他的,一旦离开了他,一些正在组织实施的研制方案就会拖延、搁浅下来,甚至一旦有误,国家还会蒙受很大的损失!然而,面对刚刚开始就要结束的命运,面对“组织”不可抗拒的决定,身为“摘帽右派”的他,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点了点头,便拖着疲倦不堪的步子回家去了。路上,他的心情很复杂,很矛盾,也很沉重,就像一个运动员,突然被宣布取消竞赛资格,退出赛场。前功尽弃,一切都化为乌有,一切都索然无味,只剩下了空虚、屈辱、无聊、麻木与苦涩。他后来回忆说,回家的路其实并不长,可那天他像走了整整一个世纪。
好在长期的苦难,使他早就练就了一股韧劲儿。这种韧劲儿,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毅力,更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一种坦荡无畏的人生品格。有了这种精神、这种胸怀、这种品格,人生的旅途上无论刮起何种凄风苦雨,他也会坦然相对,无所畏惧。
他回到家后,心情已完全平静下来。他见了妻子,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随意地说了一句:“明天不用早做饭了,我不去上班了。”
“怎么了?”妻不解地问。
“让我们明天离开研究所。”
“离开研究所?”妻子脸色陡变,吃惊地望着他,“又出什么事了?”
“没事。”为了让已经深受伤害的妻子不再受到伤害,他口气显得格外平静,尽量装得没事一样,“所里通知,让我们全家到农村去,换个地方过日子。”
“什么?到农村去?”敏感的妻子还是一下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们的心也太狠了!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你,你究竟有什么错?!”
蒋新松什么也设说,只歉疚地望了妻子一眼,便自己动手,开始收拾东西。只一会儿工夫,他便将几箱子书和一个铺盖卷全部收拾完毕。接下来,他开始做饭、炒菜,吃饭、刷碗。等把一切家务收拾妥当,他才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书房”里。
这是1969年一个普通的夜晚。天渐渐黑了,喧闹了一天的沈阳开始沉寂下来。此刻,两个孩子睡了,家里没有一点声响,只有妻子刘稀珍坐在饭桌前闷闷地织着毛衣。刘稀珍平常是不太爱织毛衣的,她此刻拿起毛衣,不过是想借此掩饰一下内心的伤痛而已。本来,丈夫好不容易搞了右派的帽子,前不久又在鞍钢干出了成绩,她心里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可现在,不知是哪股祸水,又突然冲了过来。她知道,丈夫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科研工作岗位的;若是这次去了农村就不再回来,那丈夫的后半生将不可想象!
不知过了多久,刘稀珍忽然敏感到了什么,忙放下手中的毛衣,偏过头去,想看看丈夫是否已经睡了。可看到的情景却令她大吃一惊:丈夫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在一盏自傲的8瓦的小台灯下,正趴在床板上专心致志地修改着鞍钢的自动化设计方案。身旁,是一本本砖头样厚的自动化理论书。
她的心被深深震撼了。作为妻子,她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如此坚强的丈夫而骄傲;可作为历史的证人,她又无法容忍眼下如此悲哀的现实。最后,她还是禁不住走过去,一下哭了起来:“新松,你、你明天就要离开研究所去农村了,怎么还……还要搞这些?”
蒋新松望着苦泪涟涟的妻子,心里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久好久,他才说道:“我不搞这些,又搞什么呢?我干工作,不要我干;我学习业务。不让我学;我在鞍钢搞自动化革新,现在又不让我搞。”他越说越激动,“你说,我不搞这些,我又干什么?难道要让我去杀人,去放火,去铁路上拦截火车,去天安门呼喊反动口号?!”
说到这里,气急败坏的蒋新松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用双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一下坐在了床板上,两滴深浊的苦泪,从干枯的眼里顿时一涌而出。妻子再也忍不住了,一下扑在他的怀里,失声地痛哭起来……
片刻之后,蒋新松渐渐平静下来,他安慰妻子说:“放心吧,历史决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说了算的。去农村劳动,我又不是第一次,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生活上苦一点。但生活上的苦,对我来说算什么?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我已经把遭受苦难当作了精神享受,每经受一次苦难,我就像被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反而越加兴奋,越加来劲,越加自信。想想吧,这么多年来,我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样的打击没有经受过?既然最苦的12年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作家海明威的话我早就给你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我虽然被打倒了,但我还活着,我还存在,我的脑子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还在思考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起来的,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科学家的!”
“可这么多年来,你为科学院,为鞍钢,干了那么多工作,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你?这、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妻子愤愤地说。
蒋新松却轻松地笑了:“记住,这个世界本身就不是公平的,历史也从不谴责成功者。所以我只有咬牙坚持下去,做一个成功者,才会最终逃脱历史的谴责。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证明,我是无愧于我的祖国,无愧于我的人民的!”
这。晚上,蒋新松和妻子谈了整整一夜。而妻子,则为他抹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眼泪。
第二天一早,蒋新松全家都做好了去农村的准备。可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工宣队的一位同志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通知蒋新松说:
“不去农村了,马上去鞍钢!”
“为什么?”
“叫去就去,不叫去就不去,甭问为什么。”
原来,鞍钢不能只“抓革命”,还得“促生产”。“三结台”革命领导小组马上要成立,像蒋新松这样的“技术骨干”不“结合”进去,鞍锕冷轧钢板厂的自动化技术改造就无法进行。再说,工人师傅们也不答应。于是有关部门决定:蒋新松必须马上重返鞍钢。
如果说,蒋新松第一次去鞍钢,仅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无奈,那么第二次去鞍钢,则是为了事业和感情的需要。
蒋新松第一次去鞍钢后,像在鞍钢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事业的试验基地,同时也和鞍钢的工人师傅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鞍钢给了他一种“家”的感觉。但鞍钢这个“家”待他再好,他毕竟是“寄人篱下”,何况他每日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因此,为了吸取教训,他这次一到鞍钢,便再次提醒自己:只要行动,不要空谈,只有行动,才是世间最好的语言;自己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为鞍钢做点事情,为国家做点事情,同时也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证明自己的价值,也证明自己的正确。
于是,一到鞍钢,他便提出,为了提高可逆冷轧机张力系统的自动控制能力,提高可逆冷轧机的工作效率和确保生产的可靠,应该瞄准自动化控制领域最先进的前沿,搞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
该项目确定后,他便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由于该系统由四个大的机柜组成,每个机柜都有数以万计的复杂线路,每条线路都有成千上万的元器件,每个元器件都得靠人一点一点地焊接起来,所以几年时间里,蒋新松多半时间都是蹲在厂里,既当设计员,又当技术员,还当采购员。一套工作服穿得满身是油,也顾不得换一换;一双胶鞋被机油浸泡后,跷起来像两条破烂的小船,他每天穿着它照样东奔西走,上班下班。
一次,他和几个同事到北京的一家工厂去组装控制柜。由于机柜的外壳和控制板相距十几公里,这就需要把机柜的外壳运到另一个地方,二者才能进行组装。这时的他已离开北京多年,一无亲戚,二无朋友,怎么办?找汽车帮忙,不可能;租车吧,又没钱。最后,实在没法子了,他只好向那家工厂看大门的老头儿说了半天的好话,希望能借给他一辆小三轮。那看大门的老头儿见他心诚,便让他写了一张借条,答应了他的请求。他骑着好不容易借来的小三轮,一路摇摇晃晃,吭哧吭哧,穿过十几条胡同,行程十几公里,最后才总算把机柜的外壳运到了另一家电器厂。可当他从三轮车上下来时,连站稳脚跟的力气都没有了,竟醉了似的一头歪倒在了路边上。
由于长年的加班,长年的疲劳,再加之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极无规律,蒋新松不幸患了肾炎。
肾炎,对一个男人而言,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但对曾经患过肺结核并从死亡的悬崖边上苦苦挣脱出来的蒋新松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治病期间,他仍坚持看书、看资料,病情刚好一点,他便硬挺着身子进了车间,甚至有时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也照样一边用手扶着腰,一边坚持修改图纸,或者焊接导线。
蒋新松为国拼搏的敬业态度、高深精湛的技术水平以及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让鞍钢的工人师傅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领导、同事深受感动,敬佩不已。因此,他不仅赢得了沈阳自动化所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尊敬,同时还赢得了鞍钢有关领导和工人师傅对他的信任。
鞍钢的主电室是厂里最为关键的一个部门,建厂以来一直由门卫严格把守着大门。按厂里规定,凡在主电室工作的人员,必须是三代清白;非本室人员若有事要进,必须经过有关保卫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入内。然而厂里居然对他这个“摘帽右派”进行了特批:可以随时出入主电室的大门。蒋新松后来说,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对他是最大的鼓舞和安慰。
1974年5月,蒋新松设计的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几经磨难,总算全部组装完毕,只等接机试验成功,便可投入生产。但如此重大的试验,风险很大,一旦失败,谁也担当不起,所以必须经上级批准。奇怪的是,蒋新松他们的接机试验报告送上去3个多月了,却迟迟不见批复回来,直到4个月后的一天,才接到电话通知:可以试验。但到底什么时间试验?由谁来组织试验?并不清楚。
蒋新松得到通知后,非常的高兴。也许他只一心想到工作,也许他高兴得忘乎所以,在束请示任何领导的情况下,他居然火速组织起人马,连夜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是艰难的。但几经周折,蒋新松们的接机试验还是终于获得成功!成功的那天晚上,现场的工人师傅们高兴得都跳了起来,有人还流下了眼泪。
正当蒋新松也想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欢呼、庆祝时,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一下又紧张起来——他忽然发现,今晚的试验现场上,竟然没有一个领导!
“是谁批准今晚试验的?”他急忙问了一句。
“不知道,”有人答道。
“是谁接的电话通知?”蒋新松又忙追问了一句。
“不太清楚。”
不祥的阴影很快驱散了成功的喜悦。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醒悟到问题的严重性:今晚的试验虽然成功了,但要是上面追查起来,怎么办?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这几天太累了。”蒋新松说,“今晚的实验如果上面不管,就算了;万一追查起来,就说是我蒋新松让干的,责任由我承担。”
“不,我们大家一起承担!”工人们齐声说道。
谢天谢地,由于试验获得成功,上面并未追问此事。蒋新松们虽然没功,却也无过。
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很快投人生产运行之中。
经实践检验,蒋新松设计的这台自动化控制设备,达到了国内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而且,从技术指标的运行情况来看,还超过了60年代末期中国从西德和日本引进的同类自动化控制设备。
紧接着,蒋新松又接受了鞍钢第三个大的自动化工程:研制可逆冷轧机的厚度控制系统。
蒋新松更加勤奋了。他除了注意研究国内自动化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外,还对国外自动化领域的新动态、新情况、新技术想方设法进行考察和研究。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除了工厂,从不去任何地方,哪怕有一点时间,他也要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门心思钻研自动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几乎每晚都要看书学习到凌晨一二点,甚至有时还连续伏案工作三十六七个小时!
就在蒋新松埋头苦干之际,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蒋新松的研制工作自然又受到了影响和冲击。并且,为了搞到蒋新松这个“摘帽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上级有关部门还派专人来到鞍钢,对他进行实地“专访”,秘密调查。鞍钢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得知此事后,纷纷表示极大的愤恨。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上面派来的人硬是被鞍钢的师傅们给轰回去了。蒋新松这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1975年底,蒋新松设计的可逆冷轧机厚度控制系统再一次获得成功。经过生产试验,质量完全合格,其控制原理和控制方法均达到70年代同期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不仅被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立为教学研究的课题,而且还受到了日本和西德一些专家的好评。
可笑的是,这一成果竟被有人说成是“批邓反右”的“伟大胜利”,是“改造右派”的好典型。为此,上面还派来一位革命干部,专门找到蒋新松,要求他连夜写一份经验总结。
“蒋新松同志,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你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你抓紧写一份经验总结,好好总结一下,我们好向上面报一份你的典型材料。”来人说。
“我没有什么好总结的。”蒋新松说。
“你干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为‘批邓反右’献上了一份厚礼,怎么会没什么好总结的呢?”来人望着蒋新松,很是不理解。
面对这位“上面的人”,虽然蒋新松不失礼节,话中却带着惯有的傲气:“对不起,我只懂技术,其他事情我是外行。我每天只老老实实地上班干活,别的事情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也没有兴趣。再说,那些事情不是我干的,是大家干的,是大家用血、用汗拼出来的!”
没办法,那位革命干部只好去找到鞍钢的工人师傅,问:“那些科研成果到底是谁干的?”
“是蒋新松干的!”工人师傅们异口同声。
是的,从1965年到1975年,蒋新松在鞍钢默默干了整整10年!10年来,从沈阳和他一起去鞍钢的技术骨干都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去,唯有他一人坚持了下来。10年中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鞍钢的工人师傅们心里最清楚。所以,当他付出的心血得到了鞍钢师傅们的理解和认可时,他竟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等待他的到底是祸还是福。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