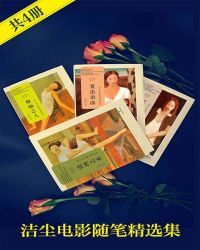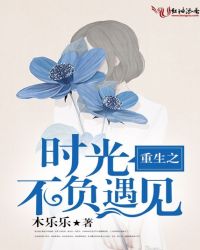非洲和亚洲的爱情回忆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非洲和亚洲的爱情回忆
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好影碟可看时,重看一遍《走出非洲》是比较明智的;如果想再打一次心灵的寒战,就重看一遍《情人》。
在爱情题材里,经得起反复观看的那些片子,需要具备一种基本的素质:激情,被很好地控制住了的激情;如果要被称作是爱情大片,激情的背后还需要有壮阔作支撑,自然的壮阔或者是时代的壮阔。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晦暗的优美的阴影。没有阴影的爱情味同嚼蜡。
《走出非洲》是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一部重要的作品,不是最重要的。在这部电影里,斯特里普饰演的女主角卡伦,相对于她一贯复杂的角色来说,要容易概括得多。如果习惯了斯特里普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苏菲的选择》中那种分裂和恍惚,《走出非洲》中的那个任性却又理性的卡伦,让人感到有一种可以触摸的光辉。她不是一个让人震惊的角色,以斯特里普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杰出演技,无可挑剔地驾驭这个角色。这也是《走出非洲》让人舒服的一点,观众随着电影情节柔和地推进,一路清淡地感动,没有意外发生。
意外都在《情人》里了。这部影片那种古怪的、冷峻的感伤,那种炎热的脆弱,那种别致的、不堪的青春,都是意外的。意外不能复制,于是,女主角简·玛奇空前绝后,她在《情人》里定格。我曾对一个影碟同好者说,简·玛奇不能再演什么了。果真,她后来演的全是《夜色》这些烂片,行尸走肉一般。她的灵魂被《情人》拘住了。
从形式上说,《走出非洲》和《情人》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殖民地、破产、怀念、告别以及一个女作家从容的叙述。
我一向喜欢一个老了的女作家回忆她的爱情,这些故事是透过皱纹看过去的,光滑、细腻、伤感,但并不滥情。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和丹麦女作家艾萨克·丹森的《走出非洲》是其中的上品,据此拍摄的电影也因其厚重扎实的文学品质而成为爱情影片中的佼佼者。但是,《走出非洲》和《情人》之间有一种质的差异,这个质,是指爱情的质。一个淡雅、疏松、精神的、唯美的;一个黏稠、收缩、肉体的、官能的。一个是,非洲,长天浩风,清白无辜,两个恋人驾机翱翔,欲醉欲仙;一个是,亚洲,雨季,畸恋,一对情人躲在晦暗的屋里,在大汗淋漓和电风扇鬼似的转影里毫无杂念地做爱。它们都很纯粹,很坚定地维护了它们各自应该坚持的爱情类型。
《情人》
丹森的爱情类型是典雅的,有合适的暗。就像卡伦在恋人丹尼的葬礼上所比喻的,一种桂花的馨香,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
杜拉斯的“印度支那时期”的爱情类型是什么呢?她在她的随笔集《物质生活》中说,爱一个人“理由可以是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其中必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为理由,去爱一个人,这样,就已经是爱情了。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公开宣告,无疑也没有被认知,在这样的场合,也应属于爱情的范围。这种类型的爱情,只有到了死,才会宣告表白出来”。杜拉斯说:“有人问:是什么把我牵系在那个中国情人身上的?我说:是金钱。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汽车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个客厅。还有司机。汽车、司机,都可以自由支配。还有柞丝绸那种性感的气息,还有他的皮肤,情人的皮肤。这些都是相爱的条件。”
杜拉斯对爱情的看法真是精彩。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实话。世间最简单与最复杂的事情其实是一回事,比如爱情。一个人因为钱、因为美貌或者因为体味而爱,很多时候与因为思想、因为才华、因为品行而爱,是同样的真挚诚恳,说不定更甚。
心情平淡时看看《走出非洲》是明智的。在公共的美好里感动,是一种享受。
心情太好时,好得没有阴影,好得令自己生疑,那就看看《情人》,看看那种见不得人的爱情,那种美丽之至的绝望,那种十五岁就开始老了的人生,然后,就踏实了。
1999/6/7
《疾走罗拉》 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