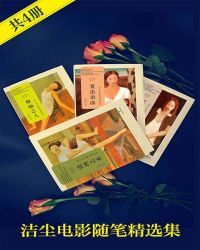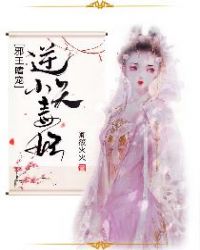面具和面孔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面具和面孔
有时候,我觉得郁闷,就会集中看一些情感类的片子,特别是法国的情感片,看那些古怪阴郁的法国人如何一团乱麻地诗意盎然。法国电影里的法国人习惯于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让我等自然认同他们的情感困境。有时候,我喜欢看韩国和日本的风格主流健康的片子,很有认同感,这种时候多半我正在阅读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对同样在东方审美范畴里的作品很是心仪。有的时候,我倾向于一种我完全陌生的粗鲁的嬉闹风格,南美的或者中欧的,这个时候一定是我非常开心的时期,胃口相当好,自然也就能体味一番遥远的情趣。
但我记得我看《黑猫白猫》之前郁郁寡欢,却拎出这张碟子看。我经常毫无缘由地郁郁寡欢,习惯了。看《黑猫白猫》的那个晚上,真是芳心大悦,所有阴霾密布的情绪一扫而空,像夏天的劲风吹散了乌云。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比喻,很刘白羽杨朔,但《黑猫白猫》给我的效果似乎就是专门印证这个比喻的。记得那个晚上是和先生一起看的,看得他也是乐不可支;要知道,先生很少和我一起看影碟,他嫌我那些碟要不憋闷得紧,要不无聊得慌。末了,他夸道,咦,你的碟子里面还有这么又好玩又高级的东西?
这部《黑猫白猫》,谁看了都会开心吧。导演是艾米尔·库斯杜力卡,关于他,影碟上有这样煽动性的广告:“十八年共拍六部电影,中奖率维持100%,六度连庄六座最大奖,包括一次柏林影展最佳导演,二次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及最佳影片,三次坎城(戛纳)影展最佳导演或最佳影片,电影史上至今仍找不出第二人。”其中,《黑猫白猫》获1998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奖。
可以说,这是当下世界影坛的第一牛人。看过他的《爸爸出差时》《地下》,领教过他的化古怪为神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黑猫白猫》中臻于化境。很牛的导演,拍出来的片子一部比一部复杂,或者说庞杂,应该是自然现象。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回归简单。不,应该说,他们中很少有人继续拥有简单的力量了。远的不说,看看陈凯歌吧。但库斯杜力卡依然拥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他能够在全然简单中间不动声色地提炼出人生最重大最本质的东西,然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厚重的滋味和分量出来。
《黑猫白猫》的故事喧闹、愚蠢、滑稽和无耻,里面充满了黑道上的欺诈故事,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人物也是既边缘又古怪,情绪无常的一口烂金牙的黑社会老大、痴情的侏儒、用屁股拔钉子的歌女、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的中年混混以及许多的神经病……还有一些超现实的元素:会吃汽车的猪、一直跑在车头前的成群的白鹅、目睹一切洞悉一切的黑猫和白猫,它们既代表好运,也代表厄运……这一切都很有张力,分贝也很大;库斯杜力卡把这些噪音合成出来,居然很和谐;再配以巴尔干半岛上吉卜赛人的绚丽服饰以及南斯拉夫音乐特有的既放荡又贞洁的配乐,整个片子有一种饱足感,真能让观者心满意足。而这一切的高超之处是,我们看不到导演的思考痕迹,他把自己彻底地藏起来了,这让他像一个菩萨。我真的是把《黑猫白猫》当作了菩萨心肠的作品——对芸芸众生的全然接纳和无限悲悯。
如果把《黑猫白猫》放到它发生的环境——战火连连的南斯拉夫去思虑,那么,这种狂欢故事就有了一种寓言似的意味。人其实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微笑,可以欢乐的,也是可以在微笑和欢乐之下尽情悲伤的。库斯杜力卡在《地下》时已经给我们讲述了一遍这样的道理,在《黑猫白猫》中,他讲得更好,更完满。我想起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当我们尽最大可能地减轻无谓的奴役,避免不必要的苦难的时候,为了使人类的英雄主义品德始终保持着,一系列真正的灾难,死亡,衰老,不治之症,一厢情愿的爱情,遭拒绝或被出卖的友情,比我们的安排更狭窄、比我们的梦想更乏味的平凡生活,总之,因事物不可思议的属性而引起的所有的灾难,仍将继续存在下去。”
库斯杜力卡显然将这一真知灼见了然于心的,不过,他用的手段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无厘头。他把人化装成小丑,饰演者和观看者一起哈哈大笑。同样作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天才导演,马其顿导演米尔乔·曼切夫斯基(其作品有著名的《暴雨将至》)在其新作《尘土》中,就把他的重心倚靠到了英雄主义身上。严峻的英雄主义,散漫的玩笑意识,哪一种都不能彻底滋润那片血淋淋的土地上的种种人性的干渴和焦虑,但是,后者,也许更容易,更亲切吧,虽然它更难。你相信吗?小丑的面具总有一天会成为面孔的。
2003/10/13
《黑暗的习惯》 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