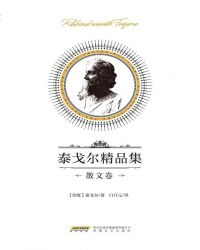西行日记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泰戈尔精品集.散文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西行日记
一
上午八时,天空乌云密布,细雨中的地平线模糊不清,季风像一个烦躁的男孩,怎么也安静不下来。凶猛的海浪扑向港口的石堤,激起阵阵轰响,像是要揪住谁的头发,把他扔进海里,但始终抓不到他。如同心儿在梦中受到惊扰,在胸中奋力挣扎,憋在喉咙里的声音想化为号啕大哭,倾泻出来。这喷溅着白沫的哑巴似的海涛的咆哮,让人听了觉得,雨雾中白茫茫的大海,是一个深不可测、迷茫无助、充满忧愁的噩梦。
踏上旅途之前,这种恶劣天气常被视为不祥之兆,令人心情沉重。但我们的看法是成熟的、现代的,对气候的变幻满不在乎。然而,我们的血液却是幼稚的、原始的,它的忧思超越争论,颇像石堤上四溅的愚顽的浪花。理智躲避大自然那无言的暗示,踅回到逻辑的城堡里。而血液在理智的栅栏外流动,映着云影和海浪的起伏;风笛诱它翩翩起舞,从光影的暗示中发掘丰富的寓意;当天空显露不悦的神色,它再也无法平静。
我多次出国访问,提起沉入心湖里的锚,以往并不太费力,可这次它却牢牢地抠抓着岸堤。这使我感到,我已步入暮年。不想出访反映心灵的吝啬。积蓄日益减少,支出时必然犹豫不决。
不过,我心里清楚,客轮渐渐远离海岸,将我往后拽的无形的纽带将慢慢松开。在大路上阔步向前的年轻人(此处指作者自己。)有一天曾经吟唱:“哦,我心潮起伏,我渴望远行。”这首歌难道驾着逆风飘回去了?难道对揭开大洋彼岸不熟悉的女性的面纱一点不感兴趣?
蚕从茧里钻出来是它的特性。追求物质利益者强行从茧中抽丝的时候,蚕的处境极为悲惨。跨过中年以后,我曾访问美国。他们先拉我去发表演讲,之后才给我自由。从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到会场,发出正义的呼声,我诗人的身份退到了次要的位子上。作为民间人士,我在人世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度过了五十年,按照古代哲人摩奴的观点,我这个人已到了该隐居森林的时候,却常常出现在社会需要的会场上。所以有些团体想方设法劝我去做官方工作,我从此陷入何等苦恼的境地,是可以想见的。
不管你是诗人,还是文学家,都得服从人的意志——皇上的圣旨,君主的指令,由形形色色的发号施令者组成的群体的要求。文人不能完全避开旨意的进攻。其原因是:他们在书斋膜拜文艺女神,但在客厅不得不尊奉财富女神。文艺女神召唤他们进入琼浆的宝库,可财富女神领他们步入粮仓。生长白莲的天堂与生长金莲的财神的宫宇不是毗连的。他们要到两个地方纳税,结果是一处高兴,另一处经济上拮据,常常使他们十分为难。时间花费在谋生方面,精神世界的工作又难免停顿。企图在铺电车路轨的地方修花园,那是很荒唐的。有鉴于此,通往办公室的道路与花园达成协议:园丁提供花卉,电车公司的老板提供粮食。但可悲的是:提供粮食者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赏花的爱好斗不过满腔的饥火。
人的工作有两个领域:生活需求的领域和艺术领域。需求的动力来自整个世界,来自匮乏;艺术的动力则来自心灵,来自情感。外界的订单使日用品市场异常兴旺,而心灵的渴望使艺术创造生动活泼。
所谓大众,顾名思义是指许多人。他们的需求是强烈的、大量的。对他们来说,要满足的需求的价值极高。因此他们漠视艺术。人挨饿的时候,茄子比素馨花价值更高。为此,我不能责怪饥饿者。但假如有人命令素馨花扮演茄子的角色,那么,我定要批驳这种无理要求。上苍让素馨花开在饥饿者居住的地方,素馨花本身毫无办法。它唯一的责任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别人是否需要它,它照常到时开花,照常到时枯萎凋落,照常让人把它编成花环,如此而已。
任何小人物也拥有称作本性的财富。他自由自在地把本性的财富珍藏在弱小的身躯中。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姓名,或许还曾经被人贬低过,但他的姓名保存在心灵主宰的宫殿里。谁坠入贪婪的陷阱,出卖自己的信仰,如再敲响他人的宗教的铜鼓,那么即便在集市上名声显赫,在他心灵主宰的宫殿里也将销声匿迹。
我这样说自有我的道理。不能说我从无过失。沉重的痛苦中,我体会到我的过失造成的损失和悔恨。我为此变得非常谨慎。狂风暴雨的时候,由于见不到北斗星,人会迷失方向。在不同的时候,外界的喧嚣使人昏昏沉沉,听不清楚本性的自白。那时,许多人异口同声地高喊“职责”,在他们的叫喊声中,我迷茫了,忘记了并无什么称为职责的可隔绝的东西。我的职责是指对我来说应尽的义务。赶车是一种普通的职责,但在危急关头,马如果说“让我来代替驭手”,或者车轮说“让我履行马的职责”,那么,这种职责是可怕的。民主时期,这类变幻无定的可怕职责随处可见。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是人们所期望的。可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战车有很多部件——劳动者有劳动者的驾驶方法,贤人有贤人的驾驶方法。只有双方协作,互相帮助,战车才驶向前方。双方的职守混为一谈,势必造成停车事件。
在目前的年龄,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是:虽然我生来是个森林隐居者,但工作地点的煞星,却把我改造成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我在书房伏案写诗,不知哪一天,天帝的意志的渡船把我送到人海的码头。现在,我的时光在诗歌创作的书斋之外消度,我置身于民众的活动场所。当鸭子在陆地上摇摇摆摆走路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的脚掌生来不适宜陆地上的行走,而适宜水中游泳。同样,“可恶”的习惯和天帝赐予的写作的兴致,使我在民众的活动场所迈步的姿态至今不十分优美。在这里我没有当“主语”的资格,我所说的“不变格”的事情,我做起来也毛病百出。当义务工作者的年龄已经过去了, 但每逢灾年,我仍不得不手持募捐本到富豪关闭的大门口转悠,落下的泪滴比捐款的数字多得多。随后,有人请我作序;著书者寄书给我,请我评论;有人责怪我不复信,信中附寄邮票,强迫我写回信;年轻夫妇在信中请我为他们的新生婴儿起名字;出版社的编辑来函催稿件;即将结婚的恋人请我为他们谱写新歌;还有人来信请教我是怎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人来信责问我,在振兴民族方面,为什么与报刊专栏撰稿人的观点不一致。在他们激情的夹击下,我不得不积攒这些无聊之事的垃圾,好在岁月的清道夫擅长清除垃圾,我有望得到天帝的宽恕。
经常有人请我去主持会议。当我沉浸于诗境的时候,我没有这种烦恼。不会有人犯糊涂,恭请放牛娃端坐在皇帝的御座上,所以,他有时间坐在榕树下吹笛。但是,假如有一天把他召去,他用鞭子当君主的节杖来挥舞,那牧牛和国王的统治均受影响。我是诗歌女神的侍者,可在混乱的环境中,却无奈地戴着富翁的议事厅里的徽章。结果,诗歌女神常常把我抛弃,而富翁掌握的宣传媒介也千方百计找我工作中的岔子。
我缘何素无躺在指令的箭榻上的愿望,上面做了说明。此外,我做了申辩,讲清楚在众人合力劳作的地方,我已为卖掉的所有“闲暇”的牛犊按时纳税;我为何采取文明或不文明的不服从的方针;我未能躲避那些恳求,是我性格软弱所致。这世上大人物个个是板着脸的心硬似铁的人,在获取神圣财富的道路上,在中意的地方,以恰到好处的坚定口吻说声“不”的能力,是他们的盘缠。为了保护神圣的财富,他们在自己周围的地段,能够构筑“不”这咒语的工事。我不如他们那样崇高,做不了那种事。我脚踩着“是”和“不”这两条船,摇摇晃晃突然落进无底的水中。因此,我今天真心诚意地祈求:“哦,‘不’这艘船上的船夫,请用力把我拉到你的船上,然后把我一直送到河中央。无事的码头在等待我,不要让我在犹豫中浪费宝贵的时间!”
哈奴纳马德号客轮上1924年9月24日
二
今天,太阳不时从云中朝下窥探,但它似乎仍被关在牢房的铁窗内,没有自由,似乎仍没有摆脱恐惧的阴影。身着雨霖之国的黑色制服的云团,在它四周巡逻。
阳光隐匿,我情感的江河里潮水哗哗退落,涨潮要等到阳光重现。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我看到大部分青年对父母的依恋之情正在消失。可在我们国家,这种依恋之情仍然存在。同样,我也看到,在那个国家,难以深切地感受到人与太阳在心灵上的联系。在这个阳光稀少的国家,人们为了阻挠阳光射入屋内,有时拉上一半窗帘,有时甚至把窗帘全拉上。我认为这是一种蛮横的行为。
人难道不与阳光息息相关?太阳的光在我们的动脉中流动。我们的生命、灵魂、富于情感的容颜,都源自那个巨大的星球。太阳系未来的岁月,在它的火雾中飘荡。我们身躯的每个细胞都包蕴它成形的能量,它的光华与我们思维的波涛一起奔腾。在外部世界,太阳光里的颜色,使云彩、草叶、鲜花和整个世界的容貌色彩斑斓;在内心世界,太阳的能量与心绪交融,为我们的思维、情绪、痛苦和爱情染色。这阳光是如此五彩缤纷,如此婀娜多姿,如此引人遐想,如此令人回味。这阳光使一串串葡萄成熟,酿成一滴滴美酒。也正是这阳光为我的每首歌谱写优美动听的曲子。阳光像沉寂的梵音凝集在树木的枝叶里。从我的心灵喷涌的、在语言之河中漂游的思绪,难道不是阳光的一种有意识的活跃的形态?
哦,太阳,在你能量的火泉畔,地球隐秘的祈祷化为草,化为树,往空中生长,高喊:“夺取胜利!”呼唤:“揭开厚幔!”这揭开厚幔是它生命的游戏,是它花儿、果实的绽露。地球祈祷的泉水从远古的微生物中流出,流到今时人类的中间,从生命的码头流向心灵的码头。
哦,神圣的太阳,我高举双臂对你恳求:“请开启你金杯的盖子!我身上潜藏着真实,让我在你中间看到这真实的灿烂面貌,让我在阳光中袒露我的一生。”
1924年9月26日
三
东方晨光熹微,太阳尚未升起。静谧的海水像杜尔迦女神脚下蜷睡的狮子,一动不动。陶醉于欢迎旭日喷薄而出的仙曲中,两行诗脱口而出:
呵,大地,你为何每天
阅读诉说不满的信件?!
我恍然省悟,每首诗在脑海中形成之前,复沓的诗行首先浮现出来。复沓的诗行常常像飞翔的种子飘落在我的心田,但我并不是总能看清。
遥远的海边,大地铺展五彩的轻纱,独自面东而坐,看似一幅画。从上空不知何处掉下的一封信,落在它的膝盖上。它拾起捧在胸前专注地阅读,黑棕榈往后拖曳的浓荫,好似从头上散落的蓬发。
我诗中重复的诗句说,每天都是一封信。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信件,它如此宏广,如此朴实,能轻易地包容天空。
大地世代读着这封信。我在心里望着它阅读。天国福音通过世界的内心,通过喉咙,变成奇特、丰繁的形象。于是森林里有了树木,鲜花有了芳香,生命有了律动。那信中只有一个词——阳光。那是美丽,又是恐惧;它在笑声中闪耀,在哭声中垂泪。
读这封信本身就是创造之流,其中交融着布施者和受纳者的交谈,交融中涌动着形象之浪。交融的所在名叫分离。因为,若无远近的区别,河水就不流动,信函无从传递。在创造的泉眼里涌出奇迹:一泓清溪分成两条细流。设法让幽居的种子分裂,从中引出两片嫩叶,种子才有语言,否则它是哑巴,是吝啬鬼,不会享受自己的财富。原始细胞是单一的,裂变后成为雄性、雌性两部分。此后,两部分的空隙里设立“邮局”,通邮永不停止,分离造成的空隙是一笔财富,否则一切都将沉默、湮灭。这空隙中间腾起期待的痛苦和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在欲施与欲纳的问答的此岸、彼岸之间往返运动。其间汹涌着创造的波涛。创造的季节发生嬗变,有时是夏季的苦行,有时是雨季的洪水泛滥,有时是冬季的犹豫,有时则是春季的恩惠,称它为虚幻不算为过。因为这封信的文字是模糊的,语言充满暗示,它的呈现与消失的全部含义并非每时每刻都能领会。不可目睹的热能不知何时沿着苍天之路潜入土壤,我想准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不久,有一天我看到幼苗顶穿泥土之幔,引颈寻找他世的熟悉面孔。热能遁逃的那天,谣言四起,说热能遁入地下的黑暗,坐在熟睡的种子的门前,举手叩击。如此这般,看不见的充满暗示的无量热能,进入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之间空隙的暗室,与谁窃窃私语,无从知晓。又过了几天,帷幕外面传来新奇的声音:“我来了。”
一位同行的朋友读了我的日记说:“你读大地的信,也读凡人的信,似乎把什么搞混了。迦梨陀娑的名作《云使》清楚地感受到遭贬谪的药叉和他的爱妻彼此思恋的痛苦,可在你的作品中,弄懂哪是隐喻,哪是直抒胸臆,越来越费劲了。”我说,迦梨陀娑写的《云使》,反映的也是世界的事情。否则,遭贬谪的药叉怎会住在罗摩山,而他孤寂的妻子怎会住在阿罗迦的天宫?天堂、人间的离情充斥所有的文学创作。用梵语的韵律写的世界之歌正在演奏。分离的空隙中,分子、原子每天传递的看不见的信件,就是创造的梵音。男女之间,无论是通过眼睛、耳朵、心灵,还是使用纸张,那交换的信,是世界之信的一种特殊形式。 泰戈尔精品集.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