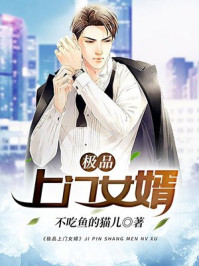红叶之泣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一入再入之红:日本文学行走随笔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红叶之泣
红叶之泣
《源氏物语》的第七回“红叶贺”,写的是光源氏十八到十九岁这一年的事。其中有一段朱雀院行幸典礼的描写,先是描述盛装的光源氏如何美艳,用的还是《源氏物语》中一贯的“反打镜头”的手法,说凡是见到光源氏的人,无不因之美艳而震惊,连他的政敌弘徽殿女御也被撼动得恨恨说道:“定是鬼神看上他了,叫人毛骨悚然呢。”
紧接着,就是关于“青海波之舞”的那段文字了。这段文字从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抄录,后来反复又抄录过好几遍,从美学意义上于我有深远的影响。我有一本书取名为《美得不寒而栗》,就是出典于这段文字。容我在此再抄一遍:
高高的红叶林荫下,四十名乐人绕成圆阵。嘹亮的笛声响彻云霄,美不可言。和着松风之声,宛如深山中狂飙的咆哮。红叶缤纷,随风飞舞。《青海波》舞人源氏中将的辉煌姿态出现于其间,美丽之极,令人惊恐!插在源氏中将冠上的红叶,尽行散落了,仿佛是比不过源氏中将的美貌而退避三舍的。左大将便在御前庭中采些菊花,替他插在冠上。其时日色渐暮,天公仿佛体会人意,洒下一阵极细的微雨来。源氏中将的秀丽的姿态中,添了经霜增艳的各色菊花的美饰,今天大显身手,于舞罢退出时重又折回,另演新姿,使观者感动得不寒而栗,几疑此非人世间现象。
(丰子恺译本)
2016年12月,我和几位女友一起去了京都,我们将这个小组合自命为“京都红叶赏”。在京都的那些天,在初冬清艳的蓝天和绚烂的阳光之中,红叶随处奔扑入眼,联想到这是光源氏出入流连的场所,多年来耽读《源氏物语》的那些绵密的细节汇成一片回忆的织锦,兜头罩下,让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恍惚的境界。虽说他是小说中的人物,但现实和虚构的壁垒在此全然消失。按说可以进退自如,其实,完全不能,进入之迅捷令我惊讶,退出之艰难令我更是难堪。
特别是在龙安寺的林子里。
在辉煌且柔和的冬日阳光中,大片的红叶和黄叶,还有些许的绿叶,各自发出玉润的光芒,交织缠绕,静默迫人。
偶尔有风,红叶随之飘飞,翩然落下。
我抬头仰望良久。
当晚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龙安寺仰拍红叶的照片,说那时候想起《源氏物语》中“红叶贺”的这一段文字,绚丽如彼,璀璨如此,令人晕眩欲泣。
红叶之泣。大片的红叶和黄叶,还有些许的绿叶,各自发出玉润的光芒,交织缠绕,静默迫人。
我是不好意思说,事实上,当时我的眼泪直接冲出了眼眶,啜泣随之而来。我赶紧走到一边,在无人处,用力深呼吸,让自己平复下来。这个时刻,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么强烈和唐突的情感,我能怎么解释?
那几分钟,近乎崩溃的状态。面对自然的美,愉悦和惊喜当然是经常体验的,狂喜得嗷嗷乱叫的时候也是有过的,但哭泣(不仅是流泪,就是哭泣),是第一次。
为此,我有点羞愧,但同时也有点喜悦。
在女人中,我算是少泪的人,因为天性羞涩,不喜浓烈的表达,在人前的状态始终希望把控得比较恒定,其实,这样的人往往会在某一个点上突然失控。记忆中至少有两次严重的失控。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公交车上,突然听旁边看报纸的人说,咦,三毛自杀了。探头一看,报纸上的大标题赫然,我瞬间泪流满面无法自持,周围人相当错愕,我自己狼狈不堪。这种突然的溃堤来自哪里我一直相当费解,其实当时我早就不看三毛了,而且对她作品的文学品质也颇有微词。想必是少女时代那些耽读三毛的日子深埋于心,其情结之强烈是我完全不自知的。另一次是2014年岁末,在成都轻安看陈浩和宁远主演的话剧《情书》,结尾处音乐一起,我泪如雨下,把周围的朋友都给惊着了。又是一次当众的失控。戏好,表演动人,这肯定是一个因素,但后面更隐秘的因素来自哪里,我自己完全不明究竟。
就是一种累积和交缠吧,其内在的作用和反应一定会在某个无法预测的点上释放出来。《源氏物语》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完整地读过三遍,更有太多的零星抽看某一章节的时候,而“红叶贺”更是我在审美立场上的一个深陷和出发,它让我对美这个危险的对象,享受的同时十分警觉,随时注意到如何撤退。
在美这个问题上,如何迎接侵袭但阻止耽溺,从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三岛由纪夫说,“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美。”这是一句谶语,作用于所有同质的人。
清水寺的燃烧
2017年11月27日,近晚时分,其实也就是下午不到五点,我和同行友人急促地走在清水坂上。要不是人太多,我们肯定会跑起来。走得急,这才意识到清水坂真是陡峭,很快,背就湿透了。
一个接一个地超过那些身着和服、脚踏木屐的人,他们大都是中国游客,到了京都,到了祇园,游客喜欢换装体验一番,换好后就在附近转悠。穿上和服后,因下摆的约束,走起路来自然就成了小碎步。在冬天,和服的外面有披风一样的外套,搭在腰上系着的小枕头外面,从后面看鼓起一大坨,背影像个罗锅。我觉得这一点很遗憾,不知道别人是否和我同感。和服很美,但冬天的外套与和服那个枕头之间如何协调才好呢?
清水寺,历来是京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游人必到,游人如织。人这么多,当然不好,但人这么多,也的确说明此地必有特出之处。在深秋初冬时分,清水寺的夕阳红叶,堪称京都绝品。所以,人再多,也难以阻挡我们奔赴前往瞄上一眼。
有些对象,反复端详也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有些对象,瞄上一眼,就惦记上了,甚至会魂牵梦萦。
冬天,清水寺,夕阳,红叶,是值得在人潮中冲上去,探头一观,然后随人潮连同天光一起退下的,渺小、软弱、满足、伤感。因渺小和软弱而获得的满足和伤感,这种相悖的情感体验,一般情况下很少能够体验到,但我在清水寺的夕阳红叶中获得过,有点上瘾,有点一而再的向往。很可能会再三且再四……
日本冬天的夜降临得很早,差不多五点,天幕就会黑下来。
龙安寺仰拍红叶。绚丽如彼,璀璨如此,令人晕眩欲泣。
我们是在中午吃了高野山的豆腐之后,乘车前往京都的。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了后赶紧入住位于祇园附近的酒店,放下行李就跑出来了,然后就朝着清水寺紧赶慢赶。
紧赶慢赶,就为了追赶清水寺的夕阳。急促的行走中,我清晰地记得,2016年的年末我也是如此朝着清水坂的高处疾行,渐渐地,清水寺大门处的橘红色大鸟居出现在眼前,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不同,当橘红色大鸟居出现在面前时,我反而更紧张了。因为大鸟居的背后,天光已经开始沉了下去,晚霞浓厚,同时色调温润低沉,所有炫目的感觉已然消散,如同有所领悟的老年行将开始。晚霞也有青年、中年和老年之分。我看着鸟居背后的天光,知道到达最佳观赏点——清水舞台对面的山道时,最后的中年就将坍塌,瞬间就会堕入老年的沉郁之中。
就在前几天,我清晨醒来,在手机上记下一段文字:
现在是2017年11月20日早上五点三十分。
我对大自然的爱慕历来是比较冷淡的,但红叶是例外。还有五天,又将前往京都。红叶的画面充满在脑子里。奔赴的激情,近乎恋情。恋情如炽。
有一天看朋友圈,正好看到一前一后两位友人发九宫格图片,他们发的都不是自己拍的,是从网上集纳的,一个发的是澳洲的蓝花楹,一个发的是京都的红叶。一蓝一红,都是规模性的美景,梦幻且冲击。我反复扒拉着看了很久,特别想确认自己更喜欢哪一种。蓝和红,历来在我就是最为工整的对仗,韵脚俏丽且讲究,我想在这样的对仗中找出一种差别,实在是很难为自己的事情。但最后我还是确认了,我更爱红叶。
去年去过一次京都,在随处可见的红叶美景之中,最具冲击力的是在清水寺。那天,夕阳下,辉煌的晚霞衬在天际线上,里面绞裹着各种程度的白、蓝和红色,夕阳拥有非常强烈的光亮,把清水寺舞台前面的大片红叶全部点燃了。我趴在栏杆上,不知该如何是好:是该多用肉眼去看,还是不停地拍?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镜头都非常的凌乱和贪婪,狂喜万分又悲切无比,冰火两重天的心境之中又有一种对贪婪的警觉和羞惭。
最后,我拍到了一张全景照片。拍得相当好,好到我在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反复欣赏这张照片。还是很庆幸当时狂拍了一阵,留下了这张足以回味的记忆定格。
买票进门,穿过正殿和清水舞台,我没有停留,径直走到清水舞台对面的山道上,走向往外凸出一点的平台,抬眼望去:右手边的清水舞台正在修葺,施工用的帷幕把舞台下的木头支架全给遮挡住了。左边,红叶在迅速下坠的晚光中依旧浓艳,但没有了被夕阳点燃的那一瞬间的透明感。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阵子,夜幕就在几分钟之内从左手边的天空铺展过来,一阵冷风和寒意也跟在后面嗖嗖而来。
我没有指望2017年和2016年的这一幕是一样的。2017年眼前的这一幕其实让我还有点满意,降了几个色度,跑了一点音调,有了几个笔误,也是恰好。后面的指望因为这个小小的降落地带而必然有所抬升。2018年,2019年……后面我还会再到清水寺吧,一期数会,夕阳红叶。
夕颜之幽艳如锦
清水寺始建于一千二百多年前,比京都城还要古老。在我的阅读中,它也存在了很久了。这也是一个跟《源氏物语》相关联的场所。
在《源氏物语》中,夕颜这个女子,其命运的凄惨,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光源氏在十七岁那年结识夕颜,与之一夜欢情。就在同一个夜晚,夕颜被妒火炽烈的六条妃子的生灵所害,当着光源氏的面,暴毙而逝。光源氏从身心相悦的顶峰瞬间滑入爱侣死亡的深渊,魂飞魄散,茫茫然不知天地之别。
《源氏物语》第四回最后,夕颜死后停灵在清水寺旁边一座苍凉的尼姑庵,光源氏趁着夜色去见她最后一面。
年轻的光源氏与随从行到贺茂川畔时,周围暗黑,火把在夜色中黯淡无光。到达东山,月亮升至半空,遥望鸟边野(平安时期京都的火葬场),景象异常凄惨。东山中,各个寺院的诵经都已完毕,惟有清水寺还有很多灯光。在其附近,有一所板屋,旁边建着一座佛堂,在此修行的老尼姑为逝去的夕颜念经超度,微弱的灯光从室内漏出来,一并漏出来的还有夕颜的侍女的哭声。光源氏晕头转向进入停灵处,握住夕颜冰凉的手……回程路上,“夜路载道,朝雾弥漫,不辨方向,如入迷途”,光源氏恍惚至极,元气全消,从马上滑落下来,几欲倒毙,全靠忠诚的随从们连裹带背,才将光源氏弄回了二条院。这场诀别对于光源氏来说,是其少年时代的一个极大的心灵创伤,终生念念不忘。
清水寺,红叶在夕阳中燃烧。
“夕颜”这一回,非常悲楚,也相当优美。其时令恰是初冬红叶季,紫式部描写在二条院慢慢恢复的光源氏,用的是借景的手法,“暮色沉沉,夜天澄碧。阶前秋草,焜黄欲萎。四壁虫声,哀音似诉。满庭红叶,幽艳如锦。”丰子恺的译文,这一段堪为华彩。
我前后去过清水寺四次。它有一种凄清险恶的美感,很凌厉。
前面两次去,都在夏天,分别是2008年和2014年。
清水寺的寺名源起音羽山的瀑布,人们来此供奉千手观音,依山而建,据此成寺,寺中长年清水长流。这座寺庙始建于公元798年,是平安时期的代表性建筑。之后清水寺多年遭受祝融之灾,现在的样貌是1633年由德川家康捐资兴建之后才有的。
走过前面新修的门廊类的建筑物,拾级而上,完全木质结构的呈深褐色的寺院本体让人感觉古远、优美和寂寥。清水寺的正堂建在悬崖边,由一百三十九根立柱支撑,宛如巨型舞台,所以又称清水舞台。清水舞台的下方就是音羽瀑布以及祈求分娩顺利的子安塔。站在清水舞台上,景观开阔,气象不凡。这里四季观景都有说法,说是春天的樱花、夏天的瀑布、秋天的红叶和冬天的细雪。
前两次去清水寺,夏天的瀑布我领略到了,清灵凛冽,荡尽暑气;松尾芭蕉有一俳句,将音羽瀑布和松风清水以及内心相联,我以前读过,但后来记不清楚,一时也查不到了。但相比之下,在我的口味里,樱花、红叶和细雪,从意境上讲似乎更为精致有品。
在清水寺,我又一次遭遇了美在彼而我在此的问题。但是,在清水寺遭遇的另外一个也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清水寺是一座观音寺庙,寺门前有很多求子的牌符;与之相对照的是,由于清水舞台建于断崖之上,而周围环境又十分优美,因而成为自杀者的首选之地,每年都有不少人从清水舞台一跃而下,死法决绝且意境高超。
对生与死的双重渴望,构成清水寺十分吊诡的特色。我想,当同时面对人生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时,它们的叠合方式又是那么的陡峭且完整,几乎没有任何疑虑溢出其外,这个时候,真就不是问题了。生和死,坦然接受好了;渴望生和渴望死,顺其渴望罢了,只需要依四季轮转分别赏赏樱花、瀑布、红叶和细雪。
北野天满宫之红叶苑
我的第二次京都红叶狩,狩获的红叶盛宴是在北野天满宫的红叶苑里。所谓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庭院,而是围水绕山而行的一大片区域。
进入北野天满宫,绕过北野神社,进入红叶苑。入口处就是一大棵槭树,拼了命的红,艳红,浓红,红得要死,红得不似真物。在这样的红叶面前,人会发痴恍惚。
从这棵中了邪的红叶前挪开脚步(真是命令自己挪开),行于缓坡上行的山道,山道两边继续全是红叶,参差交错,天空洒下的阳光在红叶间跳跃,眼睛被一阵一阵突入的红色强光所刺激。我在山道中途的休息处坐了一阵子,又开始那种徒劳的强行命令式记忆,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一切,以为可以将瞬间转为永恒。很快,我的眼睛就不行了,强光和浓烈的色彩让我疲惫不堪,最后只好颓然闭上眼睛。
继续漫步,山道随后逶迤而下,沿石台阶下到溪边,过大红栏杆的小拱桥,转入溪边道路。溪水极为清澈,倒映蓝天,波光盈盈,各种红叶,枫、槭、樱……伸展在溪水之上,叶与枝形态各异,浅淡交错。要说的话,北野天满宫之所以在京都也成为观赏红叶的翘楚之地,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条蓝光盈盈的溪水,有了它,就有了色彩更为丰满的比对,还多了几分清寒之意。
北野天满宫,也叫北野天满神社,供奉的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菅原道真,日本平安时期的公卿、学者,学识渊博,长于汉诗,学问之神的称谓由此而来。曾经被选拔为遣唐使,但因故未能成行,后来被奸臣所害,流放偏远之地,含恨而逝。据说死后成了雷公,专劈心怀不轨之人,后人为了平息他的怨怒之气,修建了北野天满神社,供奉至今。现在北野天满神社是妈妈们为希冀孩子聪明会念书而去的祈愿之地,也是与文墨事务以及求取功名相关的各种仪式的不二选地。
菅原道真化身雷公的故事,是记在《今昔物语》中的,我对这个故事的了解走了个捷径,是通过谷崎润一郎的《少将滋干之母》。菅原道真在平安前期的醍醐天皇时期官升右大臣,权倾一时,但有个政敌,即身为皇子的左大臣藤原时平。《今昔物语》中描述藤原时平“堂堂仪表,风采过人,浑身熏香,空前绝后”。时平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成功搞掉了政坛宿敌道真。道真幽怨而死,之后化身雷公,找往日政敌复仇,落雷于清凉殿,在满朝文武大臣惊恐慌乱之时,时平凛然拔刀指天,大声呵斥道:“你生前不是位于我之下吗?纵然成了神,既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就理当尊敬我!”雷公被时平的威势吓到了,雷鸣随即消失。谷崎润一郎说,世人倾慕道真的学问,同情他的遭遇,因而时平的历史形象不佳,其虽为恶臣,但颇具大和魂胆,令人敬畏。
《少将滋干之母》是谷崎润一郎的一部佳作,相当幽玄美妙,是我最喜欢的谷崎小说。这部的主角之一就是藤原时平,故事重点是香艳的男女情事。我在北野天满神社前,想到这部小说,想到里面幽怨狂怒的雷公。记得小说中,高僧尊意法师曾经劝过菅原的魂灵,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你的遭遇并不罕见,好人因小人遭灾也非足下一人,世间难免无道,如像你那样耿耿,未免失之浅薄。……菅原的魂灵脸色为之大变,尊意以为他口渴,递上一个石榴,菅原的魂灵接过石榴,一口吞下,嘎巴嘎巴咬碎,又一口啐了出来,石榴渣吐到了门框上,随即化为一条火龙凶猛地燃烧起来。读谷崎的这个小说,对菅原道真的印象实在是不太好,其死后的魂灵多次作祟,把以藤原时平为首的政敌们一一咒死,连子孙也不放过,实在是过于狭隘阴毒了。想到这里,我赶紧冲着雷公牌位的方向拜了一下。此神易怒,不想招惹。
一颗中了邪的红叶。
我最早看到北野天满宫是在寿岳章子女士写的书里。她写的是京都市民们熟悉的大型集市,这个集市每月21日在东弘法寺,每月25日在北野天满宫,一连串的摊位,售卖书、人偶和各种老式日用杂货。跟寿岳章子女士长期合作的画家泽田重隆先生,画了大量有关东寺和北野两个集市的速写,生动有趣。我仔细看过,相当喜欢。
可惜我没有遇到这个集市。当然,现在离寿岳章子教授写那篇文章的年代也有一定的距离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传统。不过,在京都,老风俗老习惯老物件老字号什么的,有个几百年的时间还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每月这两个集市的传统不太可能消失。
在北野天满神社前,我和同行友人随意聊着什么,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凑了过来,仔细听的样子。
日本人习惯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何况是陌生人,这个情形让我多少有点诧异。在日本,胖子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见,尤其是胖老头儿。日本老头儿大多干枯严肃,而且白发葱茏,收拾齐整后俨然一川端康成,而这个胖老头儿脸蛋红润,神态憨厚,很像中国北方老头子,看上去很是亲切。我对他笑,他突然开口用中文问:“你们从中国哪里来的?”我一愣,随即回答:“成都。”我不会误以为他是中国人,毕竟口音一听就是日本人,但老先生会说中文,还是让我很惊喜。他告诉我,成都他去过的,还从成都去了九寨沟。然后老先生掰着指头数他去过的中国城市,南北东西,很是不少呢。我表示惊讶,问他是不是在中国工作过,他说不是,就是去旅行。“我去过十次中国。”他把两手张开,相当得意。在学校学过中文?我再问。老先生说,不是,是自学的,跟着收音机学的。聊了几句后,老先生中文不够用了,自己笑,重复说,我是跟着收音机学的,表情无奈且相当可爱,意思好像是收音机的中文档次不行,不怪我没学好咯。
跟老先生告别之后,我想了一下,迄今为止我到日本的次数跟老先生到中国差不多吧。我们都对异域文化有强烈的好奇心,相对来说也比较专注和深入,是同一质地的一种人吧。
我没好意思告诉老先生,我会一点点日语,是看日剧学来的。
后来,我花了两百多块买了一个打折课程,在手机上学日语。课程飞快,我追得跌跌撞撞,而且记性不好,单词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反复无数次,怀疑自己早老痴呆。反正就这么学着吧,没有压力,也不在乎结果。
北野天满宫的门票是七百日元,含茶水和茶点。出口处设有简易茶席。
“马路边上有张折凳,上面铺着绯红色毡子。游客坐在上面喝茶。”这是川端康成在小说《古都》中对平安神宫赏樱处的一段记述。我记得以前看的时候,对“绯红色毡子”这个东西相当在意。怎么会是绯红色呢?不太好看吧。
生活在成都的人,对于茶文化的舒适、随意且雅趣,是相当熟悉的。第一次红叶狩到京都,在金阁寺,出口处的简易茶席一下子跳入我的眼睛里:果然是绯红色毡子,很突兀,而且简陋。没有折凳,红毡子铺就的低矮桌子,同时也是坐席。那次,我和同行友人歪着身子坐在上面,要的是淡绿色的抹茶。在这个地方,我讲了一堂课,关于三岛由纪夫和他的小说《金阁寺》。
二一六红叶苑。入口处就是一大棵槭树,拼了命的红,艳红,浓红,红得要死,红得不似真物。在这样的红叶面前,人会发痴恍惚。
北野天神宫的出口处也设有简易茶席,还是绯红色的毡子,但有折凳。一人一份含在门票里的茶食,普通的煎茶,两片脆薄饼。吃完喝完走人,就纯粹地歇个脚,不会久留,也算相当合适了。
哲学之道,红叶和瞬间
京都的哲学之道,这个名字来自日本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京都大学教授西田几多郎。据说西田教授生前每日漫步在京都大学旁边的这条小径上,沉思冥想。“每日”这词多半是因为听上去稳定持久,给人很安妥的感觉,就成了个模糊数词了,等同于经常。
西田几多郎与哲学之道的关系,对于京都人来说,其形象和寓意,堪比格尼斯堡居民与康德散步。西田几多郎1945年去世,哲学之道一直在坊间口口相传,1972年,这条小径被正式命名为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从若王子神社到银阁寺,全长两公里,途中连接慈照寺、南禅寺、法然院、禅林寺等多个著名寺院。随路而行的,始终蜿蜒着一条小溪,溪水两边都有适合漫步的小路,路边有不少小店,还有好些门扉紧闭的人家。溪岸遍植樱花,还有不少紫阳花,另外间种了不少种类的红叶植物。樱花以关雪樱和染井吉野樱为主,初春微风中,樱雪飞舞,实为胜景。我没有在樱花季到过哲学之道,自然没机会遇到“樱雪”,但我在哲学之道的一家小店的橱窗里看过照片,相当惊艳,樱雪中,春装的人们被满天飞舞的樱花瓣给裹住了。“世间若无樱,何以渡春心?”《古今和歌集》里有这样美妙的句子。
我前两次在哲学之道游逛都是冬天,天气都差不多,晴空澄碧,空气清冽,偶有小风,吹拂过来的微寒,大围巾就足以抵御了,脚和身子都很暖和。虽然相比樱花季,哲学之道的红叶并不那么显赫,但也相当饱满了。
几次漫步都对溪边的一户人家很在意。这户人家邻溪,但门前没路,散步走到这里,得稍微从桥上绕一下才能继续往前走。每次到这里门都是紧闭的。围墙不算矮,有着大遮檐的门的下方均匀分为三个部分,左边是玻璃格栅,可以透窥院内小景,红叶灌木丛和满地的红叶,中间是木门,右边是绛黄色的墙面,嵌一名牌,上书“世光”二字。遮檐之上,围墙之内,院内的几棵红枫相当高大,携临空之势招展烂漫,与紧闭的大门所透出的清冷谨肃的味道倒也一点不违和。2018年夏天,我和伊北、晚姐又去逛哲学之道,满眼青绿,遇几丛即将凋谢的紫阳花,酷热中人和植物都有点蔫蔫的,但凌霄小小的红花攀援绽放,让人一振。这趟我又去看了看“世光”。依然紧闭的门,门前台阶的苔藓颇为厚重。这扇门,明显已经很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进出了。
不知道“世光”里面是谁?好神秘的宅子,真是好奇啊。
哲学之道的溪边,有一块大青石,上面磨平,刻有一段文字。我第一次见是在雨后的冬日傍晚,石头的四周堆满了落下的红叶,石头上粘着几片湿漉漉的红叶。铁青色的石面上,红叶有了凛冽之气。我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对那上面的文字有了了解的兴趣,就把照片拿给伊北看,请他翻给我听,是这样的一段话:“‘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走过的路我不会再走。’这首歌是西田几多郎老师晚年的作品,于昭和十四年亲笔创作。他希望,这作为指明人生方向的硕学的传授,能为传播哲学之道的人们所传颂。顺带一提,寸心就是老师的居士号。昭和五十六年五月。”我对伊北说,这段话后面有点不通,但意思是明白的。伊北说,石头上的字有些已经模糊了,就这样吧。仔细想想,“我走过的路我不会再走”,当然明白这是精神层面的道路,但仅从字面意思来看,将之与西田教授在哲学之道上反复往返的身影做个叠加,颇有点喜剧效果。
不知道是否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其实不用多想,肯定是有的),哲学之道的气韵似乎相当形而上。后来当我回想这条小径,无论冬夏,我都在溪边的咖啡小店里喝过拿铁。这种味觉的记忆与某种形而上的思考,发生在哲学之道,似乎颇为相得益彰。
对于我来说,几乎可以确认了,自然之美的顶峰体验,是红叶。我确认过一次,然后又去确认了一次。后来在夏天再去了一次,在对比与回想中确认。也可能还会再去确认,当之前的确认开始漫漶散逸之后。
红叶,热烈的单一的色彩,从绿色、黄色,径直冲过去,红色。深红,殷红。这是恋情,恋情的方向是集中且纯粹的。为什么不是樱花?樱花让我晕眩且开心,红叶让我疼痛而喜悦。喜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兴,也不能称作开心,高兴和开心的滋味都过于明确和甜美。喜悦是一种很淡很复杂的情绪,有涩味,有泪意,有酸楚的脆弱,还有沉静的力量。
叶比花有力量,叶比花隐忍。红叶与花心十分匹配。花心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惶惑,是自身不可抑制的转变带来的。这种转变有一种轻飘飘的喜悦,逃逸的喜悦,刷新的喜悦,也有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境地的喜悦,但惶惑如影随形。这是与永恒这个东西分离所带来的。当人热爱上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投射出了对永恒的期待和渴望,但不由分说地,永恒的水流退去,润泽之地逐渐干涸,绿荫变成沙漠。
后来,我每每回想,红叶的规模和细节,都鲜明地进入了我的脑子。太鲜明,逼真,不像记忆,像正在发生的现实。关键是,我知道它们是记忆,但它们不给予记忆的暗哑的色度,对比度和饱和度都太高。
突然感觉瞬间这东西好可怕。时间就是掩埋自身的流沙,而瞬间则是突然抖落流沙,站了起来。然后再次被掩埋。
伊北七岁时写过一篇《有一天》:“有一天小朋友们吃饭了;有一天小朋友吃了西餐;有90天在下雨;有一天有29个人用写话本写日记;有一天有两个人迟到;有一天何阳伦还往一边跑;有365天和舅婆出去玩了30分钟;有一天有两个小朋友从沙子里出来;400年前有一个人天天出去运动;有一天有41条小鱼在河里吃小鱼;有一天有11个人用小字本写日记;有一天有400个人从沙子里出来;有一天有9个人用拼音本写日记;有一天有7个人去了一个地方;有一天的生活太好了。”
不知道“世光”里面是谁?好神秘的宅子。
我非常喜欢这篇短文。小孩子的脑子和语言真是有魔力啊。有一天,有两个人从沙子里出来。有一天,有四百个人从沙子里出来。好厉害的意象。我把这段短文让现在二十岁的伊北看,他说,小孩子的脑子没逻辑嘛,有了逻辑就有约束了。 一入再入之红:日本文学行走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