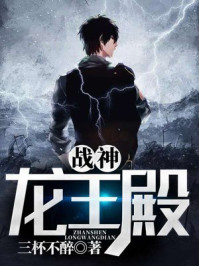10 午夜来客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十方界2:非人往事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10 午夜来客
废墟地是荒凉的,过度的寂静让人想起了一些过度喧嚣的往事。
悬空的全息屏幕上,右下角雀跃地飘荡着一条红绸带,提醒用户明天就将是新一年的1月1日,又一个元旦。
晴天还在睡着,桑绪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出神。
五十年前,上海市曾在浦东外滩举办过一场蔚为壮丽的庆元旦跨年烟火晚会,那场晚会的璀璨光华闪映在记忆里,伴着另一段回忆里的怒声质问:“元旦那天你到底在哪里?!”
质问的人穿一身刑警制服,制服皱巴巴的,领子翘着角,他被连环杀人案折磨得筋疲力尽,现在像处在暴怒边缘的野兽,扭着桑绪的脸对准电视屏幕。屏幕里是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黑色的人影从楼顶摔下。然后是另一段视频,同样的地点,时间稍早,监控拍到桑绪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走进亚细亚大楼。
监控视频反复地播放,桑绪则一遍遍地回答:“那天我没去看烟火晚会,我没到过外滩,更没有进过亚细亚大楼。视频里的人不是我。”
于是审讯进入死循环:“不是你,是谁?”
“我不知道。”
“那元旦那天你到底在哪里?”
“我在给一个朋友扫墓。”
“朋友的名字?”
沉默。
沉默的结果是桑绪无法——或者说拒绝提供不在场证明,警方则没有直接证据来定罪,双方陷在一大堆间接证据里拉锯,互相折磨。
桑绪无法告诉刑警,不光元旦,所有的节日,他都和那位墓碑上的“朋友”一起度过。
那是一块造型小巧的大理石墓碑,四边雕刻着活泼的花朵和藤蔓,已不像刚落成时那么光亮,几十年来却被维护得很整洁。墓碑上的照片是一个还不满八岁的小姑娘,不像大多数小姑娘,她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眼神水一样清,也像水一样没有内容,但在这张照片上,她另外有一点自在和温柔的意味,因为拍照的是她为数不多的信赖对象之一。
桑绪不能告诉警察,陪他跨年的墓主人叫做“桑迩”,是被他亲昵地称作“小耳朵”的妹妹。因为桑绪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妹妹出生在遥远的2008年。这是2056年,桑绪的外表看上去顶多三十岁。
他无法向警察解释,他曾经是人类,有家人,有朋友,有熟悉的旧时光。后来他被迫成为了非人,在时光的洪流中青春永驻,孑然一身。
全息屏幕转亮,闹钟跳出来,提醒用户他预定的日程安排。
这间屋子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饭桌、衣架、收纳箱,房子的角角落落都喷了杀虫剂,几乎是个能让儿童健康成长的家了。自从逃脱黑雾的追捕已经过去了十多天。
桑绪看了一眼晴天,女孩子安稳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这实在是个离奇的女孩儿,他想起她出现在雪地里,那样子实在很难说不是在等他,但又的确是偶遇——他匆匆地逃亡,走这条胡同还是那一条,都是临时决定的。但还是离奇,他有过一个自闭症的妹妹,有不说话的嘴巴和过分干净的眼睛,现在一个如出一辙的女孩出现在他身边,出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于是他做过各种试验,面对面的,偷偷观察的,但她的表现始终如一,无法沟通,并且拒绝离开他。
桑绪知道自己在犯蠢,他有很多种选择,听任晴天留在身边是最蠢的一种。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冷的冬天,人在雪地里行走,即便没有火炉,一点虚幻的光也好——何况雪地上没有太阳,天是黑的,他在夜里。于是他说服自己,晴天从没有害过他,而且在意他受到的任何伤害。
万物休憩的子夜,离天亮还很早,是个适合人行动而免于被追踪的时刻。
桑绪坐到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量子外接处理器,便携式,使用太阳能电池,是这片废墟的遗留物,东拼西凑,费心地找了许多零件来让它起死回生——活过来,去见一个已经相见不相识的故人。
林九微面前是几十张脸,分成上下两排。
上一排是一百年前的十六名死者的证件照,加上桑绪,就是“意识模块”技术的核心研发团队,钩沉系统没能找到所有人的死亡现场照,有的证件照底下是一张尸体横在血泊里的照片,有的只是一个空缺。
下一排是新死亡的五个人,四个人死在北京,一个人死在上海。
五十多年前的连环杀人案,要说远也不远,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忆犹新,旧的流言同新的案件纠缠在一起,像粉尘爆炸,掀起漫天的流言蜚语,海量的信息里真正有用的却很少,这也很离奇,好像被人特意遮掩过。
但无论如何,没有证据的联想总是最富有刺激性,人们想象桑绪就是新杀人案的主谋,不光如此,他背后还有一个团伙,所以人才会北京上海天南海北地死去。还有人说杀那五个人只是序曲,真正的屠杀还远未上演。
面对着一张张横死者的照片,林九微被两股截然相反的情绪拉扯消耗着。
现在桑绪案和爆头案都由国家公安部直接领导,北京市公安局主持侦查。作为桑绪案中一个普通的侦查刑警,林九微希望桑绪被抓捕归案,但不是被公安部或者公安厅的侦查专家或特警,而是被她。这绝不是想独占什么功劳,而是不知哪里来的,极端可怕的念头:她想亲自逮捕桑绪,只是觉得桑绪也许是无辜的。她亲自逮捕了桑绪,而一旦桑绪能够自证他的无辜,她就会放了他。
这个想法深深地楔在脑子里,她想摆脱,却只能恐惧地颤栗。
幸而没有人看穿她的心思,戴濛以为她是为了在案子中的地位下降而失落,还劝她说这是好事,人多力量大,他们的负担变小了,抓捕桑绪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站了一会儿,林九微决定打个电话。
戴濛打着哈欠出现在屏幕上,一副还在梦里的样子:“几点了,你还没睡啊?”
“我想问你,”林九微说,焦躁地撸了把头发,“齐安为什么认为人类屠杀过机器人,这和她被开除有什么关系?”
“我就觉得你迟早会问这事儿。你知道的,你来之前,我的搭档是齐安,她也是我师父。”戴濛揉揉脸,清醒了一些,“我觉得你挺像她的,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你们心里好像都有种特别拧的东西,什么也阻挡不了的感觉。齐安是‘自然生’的,她有个母亲,齐安的母亲叫齐雪,我和齐安搭档一年多的时候,齐雪死了。”
“齐安就是从那时候起……”
“嗯,齐雪是历史教授,智能技术史方面的权威。她们家是单性亲缘家庭,齐安的父系基因来自国家精子库,她没有父亲,所以母亲去世对她来说可能根本没法接受。那时候侦堪系统判定齐教授是自杀,但齐安不相信,她偷偷把系统结果给改了,改成他杀。还记得我说过,齐安认为桑绪不是唯一的一个吗?她觉得母亲的死跟这个有关。负责这案子的刑侦支队过了两个月才发现侦堪系统被人为篡改过,最后查出来是我们支队干的,齐安就被开除了。”
戴濛起身泡了一杯咖啡,氤氲的水汽蒙上他的脸,使他的眼睛看起来湿漉漉的。他盯着咖啡看了一会儿,抬头对林九微笑了笑:“篡改侦堪系统用的是支队的公用云端,没有留下个人痕迹,齐安真的是个天才。你猜齐安是怎么被揪出来的?”
林九微忽然想到戴濛和齐安在车里那种微妙的气氛,“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她说。
“不说就能代表不存在吗?”戴濛脸上蒙着一层苍白,很难说是睡眠不足还是别的,他说,“是我告发齐安的。我还觉得那是在帮她,我觉得她是走火入魔了。其实我才是真的蠢。我跟闻怀山说那天只有我和齐安值班,有段时间她特意把我支了出去。你知道吗,其实我在不在,对她来说完全没有影响,只是万一事发,我在的话会吃个‘工作疏忽’的处分。”
林九微没有说话。
人可以安慰他人的伤心,却无法安慰愧疚。她想起那第二个梦,那个痛苦的声音在梦里问她,“你怎样才能原谅我?”
水汽升腾,戴濛的脸在屏幕里变得模糊了,林九微的视线一花,一刹那间,戴濛消失了,桑绪出现在屏幕上,向她点头致意:“林警官,晚上好。”
林九微惊得说不出话来。
桑绪的脸出现在屏幕的右边,屏幕左边是他涉嫌杀死的人,坠楼死的十六个,头颅爆裂的五个,桑绪的表情却出奇的平静。
他说:“你不用报警搜索我的位置,找不到的。我已经出了北京市。”
林九微向屏幕上那第五名死者一瞥,死者死在上海。
桑绪说:“我只想和你聊一聊,弄清一些事情。或许也能帮你弄清一些事情。如果你报警,我会立刻消失,这样我们谁都了解不到更多的真相。”
“什么真相?”林九微问,脊背上冒着寒气。
“关于你究竟记得些什么。”桑绪问。
“什么叫‘究竟记得些什么’?”
桑绪说:“你应该记得我的,但你不记得了。”
那些梦境在眼前鲜活起来,林九微蓦然意识到自己被桑绪牵着走了,她闭了闭眼睛,说:“既然是为了我们两个都弄清点什么,那么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桑绪笑了一下,脸上忽然有种林九微无法理解的亲切:“好的。”
林九微正悄悄报警,看见他的表情不禁一愣。
她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记忆力一向很好,该记得的都记得。你为什么说我应当记得你?”
桑绪的嘴唇抿起一点。他的表情总是这样,变化很小,比林九微想象中的所谓“人工智能”还要冷淡,但这变化很小的表情却表达出很复杂的感受,以至于实时情绪分析系统可以像分析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分析他的表情。
“你不坦诚的话,”林九微说,“我看我们很难交流。”
“不是我不坦诚,林警官,而是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我还没能弄清楚具体是什么,但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
林九微吃了一惊:难道桑绪知道她那两个梦的事?!
这时闻怀山的声音切进来:“小林,我们这边只能看到你,看不见桑绪,也听不见他说话。他肯定用了什么办法,技术部那边正在解决。定位专家正在搜索他的位置,你要拖住他,套他的话。”
林九微不动声色地问桑绪:“你的问题问完了,该我问了。你人不在北京,那在哪里?”
桑绪笑了笑,竟像是相当了解林九微:“林警官,看来你还是报警了。抱歉,我的位置暂时还不能透露给你。”
林九微追问:“‘暂时’是什么意思?”
“也许你会想起……一些东西,到那时也许我们能真正见上一面。”桑绪说,“林警官,我不光能看见你,也能看见你摊开在云端上的那些照片。你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是认为那些头颅爆炸的人也是我杀的?”
“难道不是吗?”
“你屏幕上的所有人,都不是我杀的。”桑绪说。
“那是谁杀的?”
“关于那场连环杀人案,我的确知道一些信息,”桑绪说,“但作为交换,我希望你也能告诉我一些东西。”
“告诉你什么?”林九微问。
“你的生平。”
林九微愣了:“为什么?”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最好先解决目前的问题。”桑绪说。
闻怀山那边听不到桑绪的声音,见林九微表现古怪,提醒道:“小林,不要被他挑衅,稳住心态。”
林九微也觉得这只能是一种挑衅,否则她的生平对于他的逃避追捕或脱罪能有什么帮助?
“我的生平你不是黑进公安局全看过了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她问。
桑绪并不否认:“那么,家校、警校这些都是真的?”
“不然呢?”林九微感到匪夷所思,同时一丝隐隐的不安浮上心头,那种折磨人的直觉又来了,她直觉地感到桑绪并没有挑衅的成分,他所说的,和她讨论的,都是认真的。
“那不可能。”桑绪说。
“什么不可能?”
“不可能是你真正的人生。”
林九微感到微微的眩晕,她吩咐机器管家:“小耳朵,我要擦把脸,再给我倒杯水。”
热毛巾立刻递来了,林九微收拾了一把,问桑绪:“你那话是什么意思?”
桑绪却若有所思地盯着林九微的机器管家,迟了两秒才回答道:“林警官,之前我还不是百分百确定。我想你也许和她有关联,但未必就是她。”
“她是谁?”林九微问。
桑绪不回答,只说:“但现在我觉得,你只可能是她了。只有她才会什么都不记得,却还记着‘小耳朵’这个名字。”
林九微焦躁起来:“‘她’到底是谁?”
“她是我认识的那个林九微。”桑绪说。
林九微愣住了。
好像一瞬间被抛到外太空,无重力,无空气,只感到窒息和飘忽。
无数个念头挤在脑子里打架:桑绪在胡扯,桑绪在试图激怒她,桑绪……“技术部已经发现了他的入侵路径。”闻怀山的声音把她拽了回来,“公安部那边指示,问案子的信息,两个案子。”
林九微看了一眼受害者们的照片,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问桑绪:“连环杀人案你知道些什么?”
“16个死者死的时候胸口都有六个洞,”桑绪比划自己左胸的位置,“上三个,下三个。”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林九微说。
“人工智能里有一个大类是服务型产品,”桑绪说,“就和你的‘小耳朵’一样。服务型产品会和人类长期、近距离接触,安全性要求比普通的功能性产品要高。所以它们体内都有一个东西,专业的名称是‘稳态报警器’,用来监控人工智能的逻辑运行状况。报警器一共有六盏报警灯,上三盏,下三盏。位置和16名死者胸口的血洞一样。”
顿了顿,桑绪说:“林警官,我不光看了你的履历,还看了你们组的案情分析记录。有一条你们分析得没错,案子的确很像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报复性行为。”
“但是?”林九微问。
“对,是有这么个‘但是’”桑绪苦笑一下,“但是——凶手不是我。我不是唯一的‘非人生物’。”
“证据呢?”林九微说。
“我认为杀人也是个人工智能,能够变化成我的样子,当时好几个死亡现场附近都拍到了我的脸,但我并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而警方也没能在现场找到任何和我有关的直接证据。”
“这只是你的说辞,不算是证据。”
“的确不算,”桑绪说,“所以当年警方也不相信我的话。”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直被关押着。”
“你被关了多久?”林九微问。
“半年多。”桑绪说。
“一直关着?”
“没有直接证据能够定罪,我又不是人类,直接放人也不合适。”
“之后呢?”
“之后就下来了决定。”
“什么决定?”
“把我深冻、用于科研的决定。决定宣布的当天,我就被深冻了。然后我睁开眼,就到了现在。”
之前痕迹科的鉴定结果出来时戴濛很惊讶,虽然2057[75]号档案的解密时间被改动过,但纸质文档上的内容,尤其是“解档后作科研之用”这行字,鉴定的结论是没有改动过,是原版。
办公室里曾讨论过,假设“解档后作科研之用”这行字也是改过的,那原先会是什么内容。戴濛觉得应该是“解档后立刻销毁”,但想想又不对,如果要销毁,当年就应该销毁,不需要再把桑绪的头颅保存30年。
托桑绪案的福,现在重案二组的刑警们聊起五十年前的人工智能时代,熟悉程度都堪比历史学家,也知道网络上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些谣言,或者说狂想——也许是受科幻小说的影响,有一种阴谋论认为,取消意识模块事件很可能就是一场被精心掩盖的针对机器人的屠杀。以人类的屠杀本性,从人工智能时代平稳过渡到机器智能时代是不可能的。
屏幕里,桑绪问林九微:“林警官,深冻之前,我被告知深冻时间是三十年。那时候是2057年,今年是2110年,我一共被深冻了53年,这个数字显然不符合任何保密规定。你问了我很多问题了,而我想知道,解密时间为什么会被推后23年?”
“这个问题我们也正想问你。”林九微说。
“小林,”闻怀山说,“我们这边已经能看见桑绪的脸了,定位也快要出来了,继续吸引桑绪的注意力。”
但林九微说不清现在到底是谁吸引了谁的注意力。
她真希望桑绪那种亲切真诚的表情和语气都只是她的错觉,是他装出来迷惑警方的。
她想问桑绪,新的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但看着屏幕里的脸,一出口问的却是:“你怎么会认识一个‘林九微’?”
桑绪看着林九微,他想两个人同过生死那不光是五十年,而是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了,他们的过去要追溯到古老的2016年。但对他来说一百年是许多事情的超出想象,对于她来说则是完全不记得。
他也在犹豫,要不要说,说出来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到底是被命运的翻云覆雨手随机殃及的两条池鱼,还是精心设计的局里的两颗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
身后忽然有动静,晴天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坐在床上,盯着门口。
门是关死的,门后垒了很多重家伙,以防不速之客。
这边桑绪不回答,林九微便听到闻怀山说:“拖住他,定位还有不到三分钟就能完成!”
然而林九微刚张嘴,猝不及防地,桑绪就从屏幕上消失了!
闻怀山恼恨地锤了一记桌子。
桑绪蹑手蹑脚地搬开门口的重物,打开门,门外只有穿堂呼啸的风。
他们住在这栋废弃大楼的四楼,一个可以俯瞰整片废墟地的房间。窗玻璃幸运地还存在,桑绪挂上了窗帘。此时晴天下了床,走到窗边拉开帘子,定定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泼墨一样的夜,像凝固的黑色冰块。
桑绪关上门。晴天回头看了他一眼,仍旧定定望着窗外。桑绪顺着她的目光,看到黑蒙蒙的深远处,隐晦的光亮一闪。他的心跟着一跳。光亮消失了,像一个错觉,但几秒钟后,又是一闪,这次近了不少。
桑绪立刻把晴天推到床下,盖下床单遮严实。再看窗外,闪光不出现了,只剩混沌的夜。
悬浮的全息屏上跳出警报,绿色光点刺目地一跳一跳,像一个恶毒的幽灵。
警报来自于废楼里原有的声感报警器,桑绪凭借过去的经验修复了线路,关联到自己的量子电脑上。这些线路同剥蚀的墙皮一样老,电线有一多半显眼地暴露在墙根外,不速之客却没有去掐断它们,任由光点在桑绪的全息屏上通风报信。桑绪盯着绿点,仿佛看见那人踏着冷酷的步伐,他的脚步轻极了,空旷的走廊里听不见脚步声,只看见屏幕上绿点一步步逼到门口,停住了,定定地闪着。
一秒钟,两秒钟,时间像皮筋,在不安的心绪中被抻到无限长。
桑绪听见自己喉结吞咽唾沫的声音。
没有敲门声,也没有曾见过的银色雾气无声地飘进来。虚空里仿佛有一个膨胀到极点的黑色气球,挤压着人的呼吸和心跳,但门内外的两个人谁也不去戳破它,都等待着。
桑绪贴在门框边,举着刀。
门板呲啦响了一声。
响声从低处传来。
一声之后静了片刻,又是呲啦一声。
接着又是一声。
桑绪举着刀,另一只手伸出去,握住门把手,一点一点拧开,然后猛地拉开门!
门外,一匹狼无声地静立着,它半边身体皮毛朽烂了,露出黯淡生锈的合金肋骨和塑料罩下的电子元件。
它抬起只剩半边脸的头颅,眼睛磷火一样闪着蓝绿色的冷光。它咧开嘴,发出的声音破碎喑哑,伴着丝丝的电流声:“桑……绪?”
垂死般的声音和发着异光的独眼,像地狱的信使。
不见回答,狼的烂头颅歪了歪,慢慢地仰起来,盯着人:“我找……桑……绪?”
桑绪问:“你是谁?”
“我找……桑绪。”半死的机械产品像在镇静地发着疯。
桑绪探身张望,长廊依旧黑暗,没有一个人。
他盯着狼,盯了半晌,说:“我是桑绪。”
“有……一个……口信,”电流声时轻时重,像随时会短路,“等我……找你……,带上……”头颅忽然低下去,长长的尖牙反复切着,发出“嚓嚓嚓”的锉响,听得人脊背发凉。
“带上什么?”桑绪问。
狼强直起脖子:“带上林……九微……时间不……多……了。”
“什么时间不多了?”
狼嘴半张着,不回答。
“什么时间不多?”桑绪又问。
仍是不回答,獠牙突出着,又说:“等……我找……”
“你是谁?”
蓝色的电流炸开来,机械的畜生倒在地上,一个劲抽搐,一会儿就僵了。桑绪找了跟木棍拨了拨,没反应。他蹲下来查看,发现自己认错了,这不是狼,是条像狼的狗,一条哈士奇雪橇犬。它脖子上套着脏污的项圈,把项圈上的名牌翻过来,狗的名字就像一根刺戳进桑绪的眼睛:烛九阴。
愣了愣,桑绪忽然摇晃起机械狗,晃得那么厉害,狗身上的零件哗啦啦作响。但那支棱着狗牙的长嘴里也再吐不出一个字,虽是无生命的东西,这时也死透了。
一只纤细的手伸过来,轻轻触着狗的皮毛。
桑绪这时忘了晴天是不通人言的,从项圈上揪着名牌,对女孩子说:“这只狗,我以前认识的。”
他像哭又像笑,但既不是哭也不是笑地那么咧着嘴。
一些事,久远的,又浮上心头。
他想起那个遥远的2016年的国庆节,海南的碧海蓝天与金色阳光下,他、小耳朵、骆沉明和林九微面对一桌子芳香的水果大快朵颐。在这无比愉快而惬意的时光中,曾有一丝惊悚针一样扎进桑绪心里。
现在,昨日之日风流云散,桑绪才恍然了悟,这是因为那一刻的幸福太过饱满,饱满得都不真实了,太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梦,使人害怕璀璨的阳光之外包裹着浓厚的阴影,下一秒,入口的琼浆会变成硫酸,美景尽化为灰烬,睁开眼,空空荡荡,异时空的荒原上没有星光也没有月色,只剩他一个。
桑绪将狗抱进屋,放置在墙角。全息屏仍亮着,他安抚了晴天,让她继续睡觉,然后回到全息屏前——他找林九微并不光是为了言语的刺探。
“……那个核心专家组连桑绪一共17人,连环杀人案的16名死者全是桑绪的同事。确定桑绪为重大嫌疑人的间接证据是在几个案发第一现场附近的监控里他都出现了,而桑绪认为真正的凶手是能够冒充他外表的人工智能。”林九微总结道,“死者的胸口都有六个血窟窿,而五十年前的服务型人工智能产品体内有一个稳态报警器,也有六盏灯,二者的数目和位置一模一样。”
“这些全都是桑绪说的?”闻怀山问。
林九微点头。不全是桑绪说的,有一半是齐安和钩沉系统的功劳,但也只能都算到桑绪的头上去。
“还有,桑绪也不知道为什么档案解密会延迟23年。”林九微说,“我觉得桑绪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他骗我们没有意义。无论他是否凶手,我们现在都是要通缉他的。如果假设他不是凶手,那么连环坠楼案和爆头案的部分疑点就有了解释。”
“我认为他也没有同伙,”戴濛补充道,“否则他在医院里不用自己冒险逃脱,他应该等同伴来救,这样更保险。”
“不要预设任何立场,我们的职责是发掘线索,仔细侦查,只做有证据的推断,”闻怀山说,“还有一件事,小林,你最后问桑绪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林九微一愣。
闻怀山问她:“什么叫‘你怎么会认识一个林九微’?”
那些梦和奇特的直觉,会议室里的同事除了戴濛没有人知道,那些感觉盘踞在她心里,掀起不安的浪。她说:“桑绪说他认识我。”
“什么叫‘他认识你’?”
“也许因为一开始就是我负责他的案子。”林九微思索道,“桑绪黑过公安局的网络,查看我们通缉他的进展,他还特意看了我的资料。”
会议室里有种悚然的感觉,许多关切的目光投过来,感到穷凶极恶的逃犯必不会放过女刑警,但林九微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她想,桑绪是个会冒险的人,但他不是个赌徒。他更像是个拆弹专家,深入最危险的地方是为了安全地摘走一只威力巨大的炸弹。他冒着被搜索定位的风险出现,和她互相打探,这就结束了?他的收获仅止于此吗?
“我觉得,桑绪找上来不光是和我说话这么简单,他也许还有别的企图。”林九微说。
技术部立刻去查,很快有结果,被林九微说中了,桑绪复制走了脑爆案的所有相关资料。
老房夸她:“我们小林是活的侦堪系统!”
闻怀山若有所思地打量她。
闻怀山也憔悴了,他平时镇默少言,有些严厉,但从不焦躁。现在他的胡子也不修出气派的形状了,剃得短短的。林九微看着这被潦草对付的胡须,想到开会前老房悄悄散布的小道消息,他说不光公安部和公安厅直接调查爆头案,现在连国安部也加入了进来。“可是爆头案再可怕,也不至于威胁国家安全吧?”戴濛问。老房神秘地摇头,国安部不是随着死者的增多而加入的,而是在得知公安部请历史专家调查2055年取消意识模块事件后才出现的。
另一名同事问:“取消意识模块那事儿有内幕?”
“谁知道,”老房摇着头,“我上网查了查,没查到什么靠谱的。不过你看,55年取消意识模块,56年桑绪开始杀那批专家,57年被抓,这几件事没关联?不可能。”
“老房,这消息你又是从哪知道的?”有人问。
老房向闻怀山的办公室瞥了一眼:“我正好听到闻组在跟同学打电话,他以前一个警校的校友在国安部。”
等到会议结束,林九微悄悄找戴濛:“我们出趟外勤?”
戴濛会意:“你找安姐查什么?”
“意识模块。”林九微说,“我本来想申请权限去国家档案馆查,但国安部一掺和,肯定申请不下来了。说不定所有资料都已经转移到国安部里了。”
但当晚他们谁也没能迈出刑侦大楼,消息从云端爆出,飓风一样席卷:重庆死了两个人,杭州一个,齐齐哈尔一个,全部爆头死亡。
“这非得是作案团伙不可了,”老房脸上挂着掩饰恐惧的不自然笑容,“我怎么感觉……像在玩那种杀人游戏?”
像杀人游戏吗?人们面面相觑,感觉更像是瘟疫! 十方界2:非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