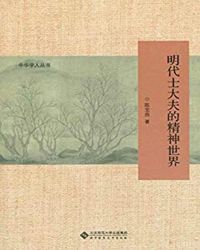三、士大夫的生死观及其转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三、士大夫的生死观及其转向
(一)生死观念举隅
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大抵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论之:
其一,人终究不免一死,但揆之人之死状,却有等第之差。如明朝人李贽,写有一篇《五死篇》,将人之死分为五等。第一是程婴、公孙杵臼、纪信、栾布、聂政、屈平之死,这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死。第二是临阵而死,死得英勇,但不免带有不自量力、轻视敌人的冒进之弊。第三是不屈而死,死得忠义,却未免有受制于人之恨。无论是临阵而死,还是不屈而死,死者均可称得上是“烈丈夫”,其人不属于“凡流”。第四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国之伍子胥、汉代之晁错。这些人的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不能真正理解君主,而其行为则应归于“不智”。第五为功成名就而死,如秦之商鞅,楚之吴起,越之文种。这些人的死,属于“不知止足”,而其行为亦应归于“不智”。无论是尽忠被谗而死,还是功成名遂而死,虽次于第二、第三两种死法,然从他们死于君的行为来看,当然也是虽死犹荣,既可成就天下之大功,又能立万世之荣名。上面五种之死,虽各有差等,但无不是一种“善死”,不失为“英雄汉子”的行径。除此而外,诸如病卧床榻之间,徘徊妻孥之侧,这不过是庸夫俗子的常态,并非大丈夫的死法。尽管如此,这尚能说是一种顺受其正,自然而死。最为让人瞧不起的是下面一种追求虚声之死,如一些人在临终之时,扶病歌诗,杖策辞别,借此表明自己不怕死,又对生无所顾恋。这在世俗之人看来,未免会被夸奖为美谈,称之为“考终”,然其好名说谎,实在令人怀疑。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变动之后,钱澄之根据当时士大夫的行为抉择,将死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二是从容自尽,即使已得宽宥,却还是视死如归;三是求生无路,不得已而死。《资治通鉴纲目》对“死”的书法有以下三种:即“死之”“战死”与“败没”。所谓“死之”,就是死节,即因保持自己的节操而死;所谓“战死”,就是功罪相半之死;所谓“败没”,则不过是因失败而死。这种分类书法,尽管基于军事行动之上,但大抵亦可概括天下之死。基于如此认识,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进一步加以发挥,将死区分为“死节”与“遇难”两种:人之死,操之在己,亦即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其志向在于一死,如田横渡海五百人之死,堪称“死节”,才可以用“死之”这种书法;人之死,操之在人,亦即决定权在别人手里,显然原本没有想死之心,如长平被坑杀之40万士兵,堪称“遇难”。由此可见,同是一死,差之毫厘,相去犹若天渊。进而言之,面临的境遇不同,死者的内心更有差异,说明士大夫对于死的抉择更趋复杂,需要加以明辨。
其二,同是一死,或死得慷慨,或死得从容,于是也就有了“从容”之死与“激烈”之死的区别。如当清兵攻下桂林之时,留守瞿式耜与侍郎张同敞一同就义,均堪称杀身成仁。然两人死时,各有不同:式耜从容,史称当大敌在前,瞿式耜关门火彻,终日召客,觞咏不辍,不谈兵事,亦绝口不言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已经洞彻国事万不可为,把以死为事看成理之当然,用不着多说,所以姑且以谈笑吟咏,聊取旦暮之愉悦。换言之,在临刑之前,瞿式耜以义命自处,从容整暇,作诗曰:“死岂求名地?吾当立命观。”而张同敞则显得较为激烈,史称他每言国事,则须鬓俱张,血泪交迸,每次酒后,慷慨悲歌,时时以得死为快。为此,当桂林被清兵攻陷之后,同敞在百里之外策马泅水入城,愿意与式耜同死。见到清兵大帅,甚至倨骂以激。这足以证明,张同敞以得死为快,所以不容不激烈以求速死。
这就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容”之死,是否稍逊“激烈”之死一筹?二是式耜若不得同敞激烈以佐之,是否真是“未必死”?对此,钱澄之提出了两条反驳意见。首先,他认为,所谓“从容”,是指其心有死无二,平常之时,所抱者此心,临事之时亦是此心,适得其常,所以不必激烈。其次,同敞终日言死,人们相信他必死而死;式耜绝不言死,人们就未尝相信他能死而死。两者相较,都可以称得上是不负其志而已,无高下之分。换言之,从容、激烈,各有性情,不分轩轾。众所周知,瞿式耜是吴人,而张同敞则为楚人,性情不同,死法则异。究竟如何看待两者不同之死,以及面对死亡的态度?熊开元对钱澄之所说的一段话,显然可以作为两人不同死法的注脚。熊开元认为,楚人唯能忍得住嗜欲,耐得住劳苦,岸傲愤激,而后能死。而吴人平日里自奉甚厚,园林、音乐、诗酒,今日自管极意娱乐,明日让他去死,却亦能怡然就戮。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可怪的事情。这段话是就此两人之死而发,堪称善于论定人物。
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到了明朝人戚继光那里,这句话就演绎成“慷慨易,从容难”。同是一死,两者相较,似乎尚有难易之别。对此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剖析。从容就义的另面相就是“笑谈辞世”。清初颇负盛名的遗民和尚弘储,曾与士大夫遗民徐枋讨论过“笑谈辞世”问题。在弘储和尚给徐枋的书信中,论及周玉凫谈笑辞世时,弘储认为“故臣遗老当此之时,谈笑而逝,似不相宜”。徐枋认为弘储之论,为“千古所未发,实千古所未曾见及也,天地之内不可无此语”。这当然是一种客套,其实在论及死生之际的状态时,徐枋却又有别解,明显不同于弘储。徐枋认为,死生之际,人所难言,人的根器不齐,且识趣各异,这就不可一概而论,应当详细考察此人生平所言、所持,借此观察其临命一息的表现。假如其人真是忠臣、孝子、圣贤、佛祖,那么在临命之顷,无论是啼哭,还是笑谈,都未尝不可。如或不然,则笑固不可期,哭亦未为得。反观周玉凫其人,天真粹白,瑜不掩瑕,忠孝皆本自然,胸中绝无一物,丝毫没有矜持名迹以行仁义之行。当易箦之时,能笑谈辞世,这是一个至性之士的正常反应,无足为奇。究其原因,凡是至性之人,若是哀乐过人,就会出现笑而悲恨甚于哭泣的场景。这就是说,所谓的慷慨、从容,并非是凭借一身而比较迟速。正如黄宗羲所言,为国尽忠而死,有时很难“从容”为之。人一旦具有扶危定倾之心,就会感到一日可以未死,自己的力量也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然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所谓的“不容已”,必须长留于天地之间。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将其藐为说铃,然在圣贤看来,无不都是血路。所以很多忠臣,如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张煌言,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毫无“从容”之态,反而倒让人觉得有慷慨赴死之感。
基于如此争辩,于是出现了调和之论,主张当忠臣面对死亡之时,应该慷慨与从容兼具。徐枋就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徐枋举出以下三个人的例子加以证实。一是杨继盛。杨继盛入狱之后,自知不免,于是在桎梏缧绁中自作年谱。如此之态度,堪称精气神明充塞天地,昭示今古。二是周顺昌。周顺昌对狱之时,相当慷慨,其词激烈,闻者毛竖;而当他濒行与亲友诀别之时,则意气和平,若无事一般。三是殷汝劼。当周顺昌被逮之时,殷汝劼奋不顾身,奔走后先,几及于难。迨乎明清易代,则又不降不辱,全而归之,皭然以死。尤其是他死于荻溪之时,却匕不御,全其肤发,琅琅话言,千古如在,慷慨从容,确乎兼而有之。
其三,人固有一死,但很多人的死,与“气”有关,无关乎“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家士人之死,倒与侠士杀身以成事颇有相近之处。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假如不能旷然超于其外,就不能进入其中,进而转圜其轴。无论是王者起事,还是臣子为君谋事,理应在未举事之前加以慎重谋虑,一旦已经举事,则应坦然忘机,这就需要他们不仅具有智慧,而且必须具备勇气。
这种勇气,其源头既可以是儒家所谓的“正气”,又可以是英雄的“侠气”。就前者来说,正如明代学者高攀龙所言,当天下有事,匹夫若能执干戈、捍寇贼,即使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念之正气。普天之下,唯有正气不可磨灭。天地之常运,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所凭借的都是“气”。高攀龙在论生死时有言;“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对此,刘宗周称高攀龙“心与道合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可以称之为“无生死”,但绝不是佛教所谓的“无生死”。洵为不刊之论。
就后者来说,则可以侠士杀身以成事为例加以说明。明代思想家李贽最为看重的是侠士,但侠士的可贵之处,也不仅仅在于他们在死面前的不加畏惧,能够做到“死事”,而是在于他们并不轻易去死甚至送死,而是在于“成事”。李贽认为,“侠”之一字,并不易言。只有自古以来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才当得起“侠”的称号。李贽对宋儒之见,多所不屑。以荆轲为例,宋儒王半山认为“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李贽断言,半山之见相当丑陋。他认为,相知在心,宋儒之见,根本不知英雄之心。荆轲作为一个英雄,必定看重成事,若要成事,不得不杀身以成之。否则,舍不得自己的性命,则如何能成得大事。显然,在李贽看来,英雄无不杀身以成事。所以,他专门写了《咏荆卿》一诗,对荆轲的英雄之心有所称颂。诗云:“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
当然,所谓的“气”,在生死成败上尚有豪杰与凡民之别。在王夫之看来,有勇方可直面死亡。当然,王夫之所谓的“勇”, “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也”。换言之,勇并非逞一时之气。生死成败,均属理势之当然。豪杰与凡民之别,在于面对生死成败时,豪杰能够做到不动如出、决机如水,亦即“守气”而不动心;而凡民所凭借的仅仅是介然之勇气,最终必会面临再鼓而衰的窘境。
进而言之,匹夫匹妇之气与圣贤之气,迥然有别,且有大小之分。圣贤之气,无不精一,能够浑合无间。反观匹夫匹妇,尽管出于正气,可以做到一念秉正而死,然他们的心却并非精一之心,所以其气并非充塞之气。举例来说,妇人女子,通常因为一言之忿,就会引绳吞药。但真的遇到暴客,心知身辱名丧,反而贪生不能自全。这是何故?究其原因,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魏禧所言,死是人所共同畏惧的,之所以不再畏惧,全凭借的是气。当忿之所激,气因而强,气强则轻生;威之所逼,气因而怯,气怯则畏死。凡是凭恃自己有才之人,才能用多了就会衰竭;凭恃自己之气的人,时间一久就会衰竭。换言之,靠着自己的血性去做事的人,时日一久亦会衰竭,甚至变其初心。只有明理精义,通过补充学问,或者说师友的夹持,方可使气积而日生,用而不穷,久而不敝。
其四,人能直面死亡,尽管与“气”有关,但必须上升到“道”的高度,使之成为“殉道”“殉节”,才不枉一死。换言之,按照明代士大夫的看法,以身殉道与以道殉君之间,其实并无差别。
这就需要对君子与众人的生死加以辨析。按照方孝孺的观点,无论君子,还是众人,无不都要面对生死。所不同者:君子是生而有益于世,死而无愧于心,而众人并非如此。这就是说,人尽管能饮食、养生,但如果于事无补,纵然有乔松之寿,犹如无生一般。相同的道理,人如果不能奉天下之道,尽人之本性,使自己之身达到无过的境界,纵然谈笑而亡,也可以说不得其死。就此而论,君子理应不以生死为意,只是修养自己的无愧之道。
人生世上,终归一死,或死于寿数,或死于忠节。有些人见身而不见仁,有些人见仁而不见身,差别仅仅在此。面对生死,人自然会产生分化:一部分人看重得失,甚至超过自己的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却不能忘情于百金之产。另一部分人,当城陷被执,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还是毅然弗慑,杀身以成仁。
人之生死,却又关乎“仁义”,更是体现了“节义”精神。按照王廷相的看法,死合天理称为“仁”,死尽人道称为“义”。如比干剖心,申蒯断臂,弘演纳肝,豫让吞炭,都是为了尽仁义之道。至于那些偷生苟免之人,尽管可以苟延倏忽之命,但一息之差,万世之谬,既失忠贞之节,终抱忸怩之耻,生时无颜,浩气不扬,与死何殊!当然,当义与死需要人加以轻重掂量之时,那么就必须审慎。舍生取义,并非难事,死而于义为善,则更难。所以微子去辛纣之乱,不害其仁;子路赴孔悝之难,卒伤其义。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当自处于贵贱贫富之交、死生之际,必须精求审处。只有在平常之时,讲之精而处之审,才能做到面对万钟千驷之富而不顾,面对三公之贵而不易,面对饥寒颠仆之贫而不悔,面对编氓一介之贱而不移,乃至面对刀锯汤火,视之如归,不动声色。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在生死观上已经悟道。
李贽作为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显然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忌恨,甚至不乏人欲除之而后快,在经过好友焦竑多方斡旋、分剖之后,此事才得以暂解。但李贽本人对生死看得很透彻,甚至在求友无得的境况下,大有生不如死、死于中国不如死于塞外胡地之感。他说:“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同是一死,李贽更是别具见解。李贽认为,除了默默无闻乃至自然的生老病死之外,儒者之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名而死。如世人之忠孝节义,就是为名而死,甚至死后有“重于泰山”之说。李贽自己承认是一个“不怕人”“不靠势”的人,甚至“不畏死”。他深知,人生总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但比起无名而死来,“有名”而死大概可以说是智者的一种选择。另一类则是为道而死,甚至是殉道而死。道本无名,何以死为?李贽以何心隐为例,将其比拟成为道而死的典范。一般说来,人莫不畏死,但心隐不怕死,于是有人认为,心隐之死,“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但李贽不以为然。他认为,心隐不是不畏死,而是任之而已。作为一个诵法孔子之徒,孔子之法,有易有难。孔子之道,其难在于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所以,心隐之死,并非是欲求死以成名,而是殉孔子“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之道,是死得其所。
综上所述,生死与道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之:一方面,如王夫之所言:“人臣当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机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不死者,时之不偶也;蹈死之机而死者,下愚而已矣。”这是追求一种蹈死的正道。另一方面,却又如黄宗羲所云:“不有死者,无以见道之界。不有生者,无以见道之大。贤生贤死,返之心而无害。”尽管殉节而死为“道”之终极要求,但生者的存在,正好证明了“道之大”,并非狭隘。生抑或死,最终的选择还是由自己的心决定。
(二)生死观念的转向
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除了上述儒佛道趋于合流之外,尚有以下两大转向:
其一,对“不死”(甚或“怕死”者)的重新论定。人之怕死,也是常情。正如明代学者唐枢所说,寿至百岁,说着死,还是怕,由此足证人没有餍足。道理尽管如此,但如果仔细分析明代士大夫在死亡面前的害怕心理,甚至自己做出不死的选择,其中尚有复杂的原因。换言之,士大夫在平日可以高谈名节,但一旦面临变乱之际,很多人尽丧其平生。这倒不能说他们并无悲歌慷慨之性,其真正的原因,正如黄宗羲所云,还是因为“平生未尝置死于念,一旦骤临,安能以其所无者应之于外”?这在历史上可以找到一些事例。如宋代陈亮替陈氏二女所写的传记,其中长女伸颈受刃,次女受污。后有念之者说:“若独不能为姐所为乎?”次女惨然,连言道:“难,难。”士大夫怕死,其实就是畏难情绪的反映。又陈了翁云:“吾于死生之际,了然无怖,处之有素故也。若处之无素,骤入苦趣,无安乐法。”可见,究士大夫怕死的原因,还是因为平日缺乏道德的修养。明清易代,一些士大夫遗民尽管并不卖身新朝,却亦并无以一死殉节。其实,这也有特殊的原因。以侯岐曾为例,他在给好友杨廷枢的书信中,已经道出了他忍辱不死的原因,亦即为了“奉母母在,保孤孤全”。尽管如此,侯岐曾却并不抱着死事易、成事难,甚至自夸“吾为其难者”,而是对自己的晚死,终究抱有一种羞愧的心态,坦然承认自己已是“生而死”,无法面对那些持高蹈之义的故友,只有他们,才称得上是光日月而重泰山。陈确所抱的心态大致相同。他在一首诗中说:“邨居无一事,胡马日纵横。晚死惭师友,宵征戚母兄。”根据陈确的自注,诗中所谓的师友,师是刘宗周,友是祝开美,同时死节。面对如此师友,陈确对自己的晚死,才不免有羞愧之情。
值得关注的是,明代士大夫对于“不死”甚或“怕死”,已经不再一味指责,而是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给以理性的分析。如高攀龙在给刘宗周的书信中,对死的理解并不是一味不怕死,而是对怕死与不怕死做一个辩证的理解。作为一个理学忠臣,高攀龙看到小人、奸臣当道,深感痛愤,极容易以生命表明自己心迹。这是一种“尽道而死”,并非“立岩墙而死”。较之刘宗周,在生死观念上,高攀龙的观点显然灵活得多。他在给刘宗周的书信中道:“大抵现前道理极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明季东林正人君子与阉党相争之时,像刘宗周之流,人在极其痛愤之时,不过是抱着一死以尽忠的态度,但对自己一死所能带来的结果,却未加深思。在高攀龙看来,死不死并不是大事,尽道而死原本就是一个儒家学者的本职,高攀龙更看重的是自己所抱的“千秋之业”,若是天假良缘,可以成就“世事”,怎能当面错过?轻率一死,不过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死”与“不死”的选择上,确实存在着难易之别。正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所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当国家尚可挽回、事业尚可责成之日,绝不能以一死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对于生、死的难易,祁彪佳、张煌言均有相同的看法。如祁彪佳在死前有一番感慨之言。当时清朝的贝勒已经派遣使者到了绍兴,无非是向祁彪佳劝降。祁彪佳死意已决,跳入池水中,端坐而死。他留书于几,云:“殉节易,图功难。以难者俟后贤。”尽管祁彪佳选择了易者,将后死图功之难留给了“后贤”,但对其中的难易,却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张煌言来说,当然明白地知晓,舍生可以取义,而求生则会害仁。作为一个大丈夫,理应冰视鼎镬,慷慨从容,原无二义。自被清兵所执以后,张煌言视死如归,这绝非好死而恶生,而是为了继承文天祥的衣钵。这就是说,一方面,张煌言深信,“义所当死,死贤于生”;另一方面,张煌言又深知,“义所当生,生贤于死”。生死选择,视时机而定,并非一味地好死而恶生。
当然,在死还是不死的选择上,明代士大夫存在着一些争论。如王小兰,曾任广东南韶兵备副使,在南韶自缢殉节。他死后,而“贼”未至,有人替他惋惜,说:“人臣之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盍从容镇定,待贼至死之未晚。”对此,吴伟业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死者人之所难,只能健于决、成于果,否则就会败于犹豫。当北京初被李自成的义军攻陷时,道路所传,无不以为崇祯帝已经出狩。马世奇打算自裁,有客人止之,道:“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万一君存国复,可若何?”庆幸的是,马世奇毅然就义不顾。马世奇死后,当时同僚中有些人稍为濡忍,为义军所捕获,一到此时,即使再想自行引决,亦无可能。就此而论,马世奇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又以邓伯道之事为例,沈芳扬与张履祥同样存在着争论。沈芳扬认为,“事当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为看得死太重,所以踟蹰于全子、全侄之间,不得不为伯道。若当死而死,身且不顾,父为子死,子为父死,兄弟亦相死,岂不光明正大?”针对这一说法,张履祥有所疑虑,提出了较为平和婉转之说:
窃疑当死而死,在君父之难无惑也,如不由此,则死乌得不重?至于可以不死,而势不能两全,则计较于全子、全侄之间,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当时挈侄以逃,是也。但所以处其子,非其道耳。当时置之而去,其能随与否,听之可也。必系之树而去,则非矣。然其一念爱弟之诚,则亦可哀也已。 注释标题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3《记疑》,658页。
可见,当天理与人情发生冲突之时,张履祥提出了较为理性的看法,即区分“当死而死”与“可以不死”。
争论、冲突、交锋,如此激烈,其结果则使部分士大夫的生死观显得更为理性,随之而来者,则是对忍辱不死、“念死难”、不轻死者的谅解。如杨循吉通过吾衍自杀一事,发表自己对死的看法。事情的原委如下:吾衍年已四十,尚未娶妻。其友替他买下一位酒家女为妻。此女是有夫之妇,其丈夫死时,事情牵连到吾衍,为此吾衍只好逃走,最终投水自杀。吾衍是杭州人,世人称其学问博洽,善于古学。然面对小辱,则以自杀了却一生,与其学问若出二人。对此,杨循吉深不以为然。杨循吉将死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像颜杲卿辈,慷慨激烈而死,为世“所壮”;一类是像屈平之辈,幽囚抑郁而死,为世“所悲”;一类是无赖妄庸以死,为世“所笑”“所鄙”。而吾衍之死,“不足壮”,“不足悲”,而是令世人“足笑”。何以言此?这是因为,士不同于一般的常人,区区里巷之辱,在一般世人看来,可能是奇耻大辱,但在士的眼里,不过“若飘虻飞尘之不足为轻重”。换言之,小辱小忿而死,不免贻讥于世人,取笑于豪杰。至于君子,理应念垢忍辱,借此成全终身之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贽也对“念死难”之说作了理性的分析。人一旦“念死难”,必然会“薄志节”。这一观点,是李贽在读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之后所得出的论断。李贽承认,蔡文姬流离鄙贱,朝汉暮羌,尽管有着绝世才学,却亦并不足道。但他同时又指出,自己将《胡笳十八拍》详录以示学者,确实是因为从中看到了生世之苦,人处于这样一种人生境地,不能不发出一些悲叹哀伤之言,即使圣人也很难避免。当此之时,只有一死才能求得快当,但文姬却有“薄志节兮念死难”之吟,这在李贽看来,确实也是“真情”。所以,李贽断言:只有圣人才能“处死”,但也不以“必死”劝人。从蔡文姬的例子中,李贽所要说明的是,尽管儒家圣人主张“朝闻夕死”,但在必死之前,确实也不能不允许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苟活。钱澄之承认,古人以身许人,“未尝轻用其死,必死以济其人之事”;事情一旦不济,“则死之”。然田光、侯嬴之死却不尽相同,其谋刚定而身先死,既非以死济事,又非因事不济而死。尽管如此,两人也有不得不死的原因在,这就是遂志而死。其言外之意,还是强调一种“不轻死”。
所有这些,无不为了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忠臣并不一定以死殉节,而是不耻其身之不死。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姜垓。史载姜垓听说北京被李自成义军攻陷之后,痛不欲生。他的母亲日夕守视,凡是池井处,都让人堵塞其门。其妻傅氏更是乘间规劝,道:“君即死,妾有老姑在,不能从。虽然,君官小,又不在位,即无死可也。且闻之,忠臣不耻其身之不死,而耻仇之不报,君奈何以一死塞责乎?”通读儒家圣贤书的姜垓,在生死问题上只能拘于殉节之说,反而不如其妻子傅氏的眼界开阔。这就是说,一死只能塞责,真正的忠臣,并不以不死而耻,而是以仇之不报为耻。由此可见,所谓的不死,并不是简单的怕死,而是通过隐忍不死而有所作为。如钱谦益自己承认“不忠不孝,惭负天地”,不敢腼然执笔替节妇写传记,但他还是想借助于节妇之死与不死,为“不死”作一些辩解,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不死”乃至“偷生”“苟活”,实是有所期待。王夫之在生死问题上,也并非一味肯定士人殉节而死,对为了图存社稷的“隐忍”,同样给以理性的肯定。一方面,王夫之断定,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这已经是人臣的极致;另一方面,王夫之又不得不承认,士人一旦身已受辱,即使有了盖世之功,也很难再将这段屈辱掩盖。
其二,在生死观念上,明代士大夫开始抛弃简单的生与死的选择,而是主张“得中”,求得一个中庸之道。如吴廷翰、王廷相,通过对方孝孺的重新论定,谨慎地确立他们生死观念上的中道之论。如吴廷翰尽管承认方孝孺忠义激烈,百世之下,生气凛然,但又不得不指出,方孝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圣贤的“中道”。在吴廷翰看来,当方孝孺面对“师驻金川门,宫中自焚”的形势,其实有两条较为理性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假而可图,不害潜生”,即不死潜伏,以待东山再起;二是如其不然,就像周是修之辈那样的死,亦足以自靖。而方孝孺并不如此,最终造成一忠成而十族戮的惨局。这是典型的“忠义有余”。而在王廷相看来,这是“忠之过”,是“自激之甚”。王廷相认为,同样是忘身殉国,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从容就死,根本用不着像方孝孺那样,“激而至于覆宗”,固然取了“义”,却失去了“仁孝”。这是典型的轻重失宜。
这就需要对士大夫行为的“狂狷”与“中行”加以适当的梳理。若是崇尚中庸,诬蔑节义,自然会导致世道日卑。然若揆诸清初士大夫遗民的行为,确实还是以“得中”最为符合实际。如黄宗羲认为,尽管遗民属于天地之元气,但亦应该尽自己的本分。士各有分,作为“朝不坐,宴不与”的读书人,其本分“止于不仕而已”。就此而论,在生死观念上,还是顾炎武之说堪称通人之论而显得较为平实。他说:
天下之事,有杀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圣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节,他日事变之来,不能尽如吾料,苟执一不移,则为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于通人矣。 注释标题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李中孚书》,载氏著:《顾亭林诗文集》, 82页。
这就是说,杀身既可成仁,亦未必就能成仁。士人应该选择的是“时”,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这是“时中”说在明末清初的翻版。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