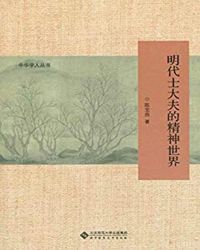二、生死观:儒佛道之辨及其合流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二、生死观:儒佛道之辨及其合流
在生死观念上,儒家最为典型的说法,就是孔子所谓的“未知生,焉知死?”究其含义,就是说对于生死,既不能恋生,也不能惧死。这一说法的发展,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亦即所谓的“朝闻夕死”之说。这一说法的根本内涵,已经道出了儒家的最终追求,就是“闻道”。一旦闻道,那么生死即可置之度外。相比之下,佛氏之徒所谓的“无生”,究其本质,还是“畏死”;而老氏之徒所谓的“不死”,其实质也是“贪生”。
(一)儒佛道生死观之辨
在生、死面前,应该如何应对?这不能不提到儒、佛、道三教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为示说明,不妨引用明末清初两位士大夫遗民即黄宗羲与金堡的争论,作为这一问题讨论的起点。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遗民汪沨作如何评价。从史料记载可知,遗民汪沨,字魏美,入清后不与人相交,妻死不再续娶,又将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弟弟,行事往往与宋代遗民郑思肖相类。对此,道隐和尚金堡评论道:“尽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轮,皆炽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寿,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无身,则俟君仙后,尚当与予求必死之道。”细玩这段话的主旨,其实是在指责汪沨讲究调息长生之非。金堡所谓的“炽然而生”者,即轮回之说;所谓“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死了烧了之说。而黄宗羲的生死观正好相反。黄宗羲认为,天地生气流行,人们因为富贵利达、爱恶攻取之心“炽然而死之”,导致“轮回颠倒,死气所成”。所幸者,黄宗羲看到了汪沨的忠孝至性,与天地无穷,就好像“食金刚,终竟不销”,绝不会与“尸居余气同受轮回”。正是在这一点上,黄宗羲与金堡开始发生歧异:金堡所看重的是佛家的轮回之说,诸如万起万灭之交感一类;而黄宗羲所看到的,则是儒家所谓的忠孝至性,认为假若断绝了忠孝的种子,那么乾坤就会几乎熄灭。这是生死观念上典型的儒佛之辨。
在金堡、黄宗羲争论的基础上,再以清人袁枚与彭尺木之间的讨论为例加以剖析,无疑对于进一步了解儒、佛两家生死观念的差异将更有裨益。他们两人争论的焦点还是落实在儒、佛两家之辨中,即究竟哪一家更能悟得人的生死,并使人参透生死或在临死之前无所畏惧。彭尺木认为,禅学无疑可以让人了却生死,他的依据是文天祥的诗句,断言假若文天祥没有遇到楚黄上人,便不能了却生死。而袁枚的见解则基于下面两个事实:一是儒家所谓的生死,其实很多就是儒家学者道德践履的标准;二是佛家所谓的生死,并非能使人了却生死,而是一种贪生畏死。细究两人争辩的宗旨,还是生死观念上的儒佛之别。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其意是说,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然有事关纲常之重,而适遭其穷者,则又不得避死而偷生。所以,凡是有志之士与成德之人,当身处纲常伦理之间,唯求合乎天理,当乎人心,以成就自己之仁而已。这就是说,假如自己可以不死,而且这种不死对于仁又无危害,那么就不必轻身以犯罪。反之,若是身虽可免,而大节有亏,那么,作为志士仁人,就决不肯偷生苟免以害自己之仁,宁可杀身授命以成自己之仁。这是因为,生固可欲,而仁之可欲有甚于生,故生有所不为;死固可恶,而不仁之可恶有甚于死,故死有所不避。这就是儒家关于生死的正说,其意义相当重大,假如不是上为君亲之难而身系纲常之重,绝不肯决死生于一旦。
当然,在生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出于“私意”之说:一种是愚夫愚妇无识的行径,他们乐生恶死,生欲求东海之神,死欲锢南山之铜;而另一种则是贤知者的过分行为,他们生期速死,死期速朽。其实,无论是欲迟,还是欲速,应该说都违反了自然之理,因此在儒家学者看来,无不都是属于“私意”,并无是非高下之分。何以言此?忠臣死忠,孝子死孝,正是自然之理,并非速死之谓。当死不死,便是怖死,便属于私意。原因很简单,人有生必有死,死终化为朽壤,此则自然之理。儒家认为,若是不怖死,就会不求速死;若是不辞朽,亦就不求速朽。所以,儒家之教,生则有饮食宫室之奉,死则有衣衾棺椁之备。
进而言之,儒家所谓的生死,其实注重平常的“居室日用之间”,所以孔子有称卫、荆善于居室之言。这就是说,圣贤之学,尤为反对“苟且”二字,不但不可以“苟生”,而且不可以“苟死”。苟且而生,那么其人必定本来就是庸下之材,虽欲为之起懦而不能,不过是流俗所为;反之,若是苟且而死,当然可以称得上已有异于流俗之心,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不脱急功近利之见,亦为君子所耻。有鉴于此,明末东林党人魏大中才有了下面的说法:“天下多故,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也。”其言外之意,就是儒家学者在了却生死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死忠死孝”上,而不仅仅是通过“参道”即可了却生死。
归根结底,所谓的生死问题,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看待一个“死”字。人莫不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所趋有霄壤之别。一般平庸者之死,或死于寒暑,或死于饮食,或死于盗贼水火,或死于毒蛇猛兽,虽亦各不相同,却无多少可记乃至可辩之处,只能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浏览历史典籍,我们不难看到,能够流芳百世的死,其间也是各不相同,诸如龙、比以忠而死,夷、齐以清而死,申生、伯奇以孝而死,荆轲、聂政以侠而死。虽为死之志不同,然而神寿百世,骨香千古,无不璘璘炳炳,光耀史册。
一至国破君危,志士奋兴,以图匡复,这当然是决起一朝之事,根本无暇预先去计划自己的始终。若稍有犹豫或者思考,事情或许就不成。即使如此,其中也有不得不妥然加以思考之事。否则,大乱一起,就会不知所措。是死乎?或是弗死?死要有为而死,生也要有为而生,变乱虽生于始谋之外,但一个人的心自然还应该依乎其初。所谓人的初心,其实就牵涉到一个儒家士大夫对大义之类的看法乃至践履。明代学者罗洪先就将殉节之士称为“自靖”。所谓自靖,罗洪先将其解释为“自尽其心而后能安也”。罗氏进一步阐释道:“夫仁,人心也。尽乎心,则求仁得仁。此夷齐饿而商不仁,百世以下,闻者莫不兴起。”如靖难之事一起,练子宁能做到虽戮妻孥不避,这就是达到了“自靖”的境界。说得直白一些,忠君而死,就是“自靖”。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佛教禅师,号称勘破生死,但在临死之前,却也另有一番做作,显然还是对尘世有所依恋。正如钱澄之所揭示:“吾观古德于临命之际,作偈颂,辞檀越,集众坐化,号为 ‘自作主张’。自有此稿本留传,到头来虽手忙脚乱,惟此一事毕竟要依样葫芦;若不如此,竟不可死。有识者闻之,直得一哕。”至于那些平日高谈禅悦的士大夫,临到死前,更是别有一番景象。正如袁中道所言:“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见谭禅诸公大限到来,手忙脚乱,如落汤螃蟹,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学问,俱是口头三昧,世情实未放下,资粮实未办足故也。”
在生死观念上,尽管孔子有“朝闻夕死”之说,然究此言的立意,原本只是为那些不知“道”者而发,即所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亦即孟子所谓的“行之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其意并不是说在日用当行之外别有一物,可以生时带得来,死时带得去,一如佛教所谓的“末后一著”。可见,就儒家学说而言,生死之说亦甚平常,只是生顺则死安。若是一个君子,只要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此,颠沛必于此。任重道远,得正而毙,仅仅如此而已。所以孔子又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要求人们在生前致知力行,并在致知力行之际,讲求体验,实见得道理如此。而佛教则不同,在生死问题上讲究的是“末后一著”,重视参透顿悟。
其实,所谓的“末后一著”,并非仅是禅门独有。换言之,死生之理,犹如昼夜之故。就对死生的重视程度来说,儒家绝非亚于佛家。在儒家看来,死生是人生一件大事。若是把“生”比喻为“住”,那么“死者”就好比“行人”。人之出行,近的需要持糗糒,远的需要裹糇粮,至于衣囊幞被之类,更是需要预先有所准备而后才敢出行。而人之死亡,则好比“大行”,假若浮湛若丧,茫茫然一无所持,绝非善行之人。若是把“生”比喻为“寓”,那么“死者”就好比“归人”。人从远方回归家乡,指坟墓而悲,望国都而喜,见父母妻子,都相持而诉说劳苦。而人之死亡,则好比“大归”,假若仓皇怖恋,惛惛然而无所底止,这也说不上是一种很好的安息。反观古代儒家圣贤,他们的生平学问,无不通过死生之际加以验证。从历史上的事例来看,如反手曳杖,逍遥行歌,这算得上是超出生死而示现生死之例;曾子处其常,则启予手足,得正而毙,由此可见儒家学者临终静定之正因;子路处其变,则食焉不避,结缨而死,则更能显现春风白刃之能事。诸如此类,无不说明儒家同样看重“末后一著”。
当然,同是死生之际的末后一著,儒家、佛家与道家,其观念却各有不同。若对儒、佛两家的生死观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以下的差别:儒家认为,人一生下来,所具备的只有形与神二者而已。人生之时,则神守其形;人死之后,神就散去,不复知其有形。这是形神合一之论。佛家认为,形由四大偶聚幻成,神把形看得至轻,无所顾恋,就好像行人之视蘧庐,暮假朝弃,没有一毫顾恋之心。这是形神两分之说。在生死问题上,儒家学说开始出现分流,甚至在人死之后的丧葬仪式上更为重视“枯骨”,进而流行风水之说。这是对儒家生死学说的偏离,是将死者之神视为久而不灭,所以才百般依恋形骸,并通过冢墓而保全形骸,使其不被毁灭。尽管如此,究之儒家经典或者圣贤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如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论;在儒家的经典中,又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在《易经》中,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的说法,借此说明乾坤有时而生死;在《诗经》中,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说,借此说明陵谷有时而来去;孟子论及生死,有“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说;陶潜论生死,有“浮沉大化中,不恋亦步惧”之说。上述众多之说足以证明,从儒家的角度来看,生死去来,即使是天地也不能自主,何况是人,更是无法预测与控制。对于生死,既不能恋生,也不能惧死。但当面临生死抉择之时,那么必须做到大勇,见义而为,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与儒家“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的说法相异,佛家认为,生本无生,死本无死。又以为生有所来,死有所往。究其实,佛家此论,不过是一种贪生畏死的典型征候。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多儒家学者对佛氏的生死之说多有批判。如作为宋儒巨擘的程颢,在他的学说中就颇多斥佛之言,其最有代表性之说是将佛氏所谓的“出离生死”看成一种“利心”。
面对生死,儒家与道家亦多有不同。就儒家来说,孔子之于阳货,可以做到义不屈而身不危。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其实也无神变不测之用,不过是求诸己而已。这就是说,君子对待他人,既无所傲,亦无所徇,即使风雷之变起于眼前,也能够自敦自信。敬者自敬,信者自信,而勿论其人之暴与否。这就是儒家的气魄,是偏于“刚”的一面相。人一旦能够贞、敬、信三者兼具,那么就能做到行乎生死之途而自若,即使居心恂栗,但外在的颜色还是安静祥和。就道家来说,譬如庄周,在《人间世》中有动色相戒之说,显是恐惧已甚,与死为徙。这是舍弃自立之道,通过恐惧而侥幸免死。这是道家的常态,是偏于“柔”的另面相。然当面对生死之时,人不幸而终究难免一死,但死的样子不一:儒家讲求以正为道,“以正处死”,这是一种常态;道家则以惧而谄,以谄而死,最终不免于死,这是一种变态。上面这段关于生死的儒道之辨,是清初学者王夫之的总结之言,细绎其意,无非是主张人在死面前不应有惧,应该“义而不屈”。这是偏于儒家之论。
(二)儒佛道生死观念的合流
在生死观念上,儒佛道之辨已如上述。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晚明的学者中,颇有一些人对佛氏“出离生死”之说作了重新的认识。焦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说:
夫生死者,所谓生灭心也,《起信论》有“真如”、“生灭”二门,未达真如之门,则念念迁流,终无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离生死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则即生灭而证真如,乃吾曹所当亟求者,从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灭”、“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无身也,而不获其身,“行其庭”,非无人也,而不见其人。不捐事以为空,事即空,不灭情以求性,情即性。此梵学之妙,孔学之妙也。 注释标题 焦竑:《澹园集》卷12《答耿师》,82页。
在焦竑看来,佛氏所谓的“出离生死”,不是程颢所谓的“利心”,而是与《周易》所言的“止其所”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之一生,最难勘破者,在于贫富、生死之关。但对于那些为佛、为圣、为仙者而言,那么在贫富、生死之论上,则无疑可以殊途而同归。换言之,生死是一件大事,与文章、名誉、富贵之属相较,显然大有不同。即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为例,平生对于性命之学、死生之说,注解得盛水不漏,然晚节末路,胸中略无得力处,最后甚至索之于方士之术。从这一典型案例,明人薛蕙不得不承认,佛教倡导的“真如不灭”,确乎实有其事。所谓的超脱生死,其实不过是佛老的心学“余事”而已,佛教生死观的关键,恰恰在于“本无生死”。唯有如此,方能不为生死所动。这是生死观上的儒佛合一。
生之必有死,犹如昼之必有夜;死之不可复生,犹如逝之不可复返。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莫不欲生,然终究不能使自己长生;人亦莫不伤逝,但毕竟不能止之使勿逝。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李贽就在一般“伤逝”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伤生”之说:“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伤生之说,显然受到佛家学说的影响。李贽的生死观,毫无疑问与佛家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个“学道”之人,他对生死有下面的看法:
学道人大抵要脚跟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脚跟,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虽迟速不同,决无有不证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为脚跟,则终其身只成就得一个虚名而已,虚名于我何与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别人无能为也。今人纵十分学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为苦海,而今学者反以生死为极乐,是北辕而南辙,去彼岸愈远矣。世间功名富贵之人,以生为乐也,不待言也。欲学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为乐也,非以生为苦海也。 注释标题 李贽:《焚书》卷4《答澹然》,168页。
作为一个世俗之人,不免贪生怕死,蝇营狗苟,无所不至。而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却能做到端坐烈焰之中,无一毫恐怖。这在李贽看来,就是一种佛脱生死、离苦海的境界。
李贽的生死观念,除了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外,道家之说亦开始渗透其中。李贽认为,学道之人本以了生死为学,学而不能了生死,则显然是一种自诳。在生死问题上,他首先引用的是老子之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吾无身,更有何患。”正是从老子之言中,李贽才得以悟出下面的道理:古人以有身为患,所以希望自己能出离以求解脱。假若不出离,非但转轮圣王之极乐极富贵,释迦、老子不屑一顾,即使以释迦佛加我之身,令我再为释迦出世,教化众生,受三界二十五有诸供养,以为三千大千世界人天福田,以我视之,还是如同入厕处秽,忙着掩鼻闭目。这是什么原因?李贽还是借用佛、道两家之说加以解释,这就是有身是苦:非但病时是苦,即使无病时亦是苦;非但死时是苦,即使未死时亦是苦;非但老年是苦,即使少年亦是苦;非但贫贱是苦,即使富贵得意亦是苦。只有知道了此是极苦,所以才知道去寻找极乐。
儒家论死,必须与儒家所谓的“性”结合起来看,方能有一完整的看法。孔子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中的“道”,其实就可以用“性”来代替。此性亘古亘今,不动不变,本自为生,也就说不上死。生死有无,不过是系于一念迷悟之间。一旦悟道,朝闻道,夕死亦未尝不可;假若没有悟道,还是迷于尘欲世界,那么即使肉体未死,其精神已死,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其实,道家也有相同的学说。明末著名文人袁宗道就从老子的学说中发现了与孔子相通之处。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这句话若直接从字义上理解,不免有些矛盾。既然说“不亡”,那么“死”又从何而来?但是,如果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一层意思去理解,那么两者就有相合之处。于是,道家所谓的“寿”,也就是儒家所谓的“道”,一旦觉悟,即使死了,其精神还是不亡。
毫无疑问,忠义之士的死,是一种“圣贤家法”。人虽死,其气却浩然长留天地之间。就是这样的事实,在民间传衍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烙上神仙诡诞之说的印记。这种说法也是古已有之,如说颜太师以兵解,文天祥也因悟大光明法蝉蜕,其实并未死亡。到了明季,更是有人说扬州城破之日,亲眼见到史可法青衣乌帽,乘着白马,出天宁寺投江而死,未尝死于城中。自从有了这一说法,大江南北开始盛传史可法并未死于扬州,甚至英山、霍山义师大起之时,也全都假托史可法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显然,这是以出世入世之面目,再加之神仙家的说法,使忠义之士更趋神化,尽管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反映了在民间的观念中,生与死的问题,不仅仅是儒家的道德践履,同样与神仙家说休戚相关。
正是从这种相通之处,儒家学者在面临两朝更替的生死抉择之际,毅然选取了舍生取义这一条道路,他们所实践的同样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从明代很多著名学者的生死观来看,有些纯粹是儒家式的,而有些则显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这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明。刘宗周绝食待死之时,张应鳌正好侍奉在侧,对刘宗周说:“先生今日与高先生(指高攀龙——引者)事相类。高先生曰:‘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刘宗周却说:“微有不同,非 ‘本无生死’,君亲之念重耳。”可见,高攀龙坦然死于阉党之手时,他所秉持的是佛教的“无生死”之说,而刘宗周之死,则完全出于“君亲之念”。
“佞佛”是否会对君子的行为有所损害?关于这一点,明季的事实却证明了一种相反的论点。如崇祯年间,像蔡云怡、黄海岸、金正希等人,都是“以西竺之传讲学者”,也就是都讲究佛学,但从他们最后的行为来看,却是先后殉节。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遗民纷纷逃禅。他们尽管已经跳出世外,但内心不免仍存一种故国之思。如钱玉屏,晚年信佛,好与衲子游。但自变革以后,“动称古昔,见时流衣冠尽态,必切齿大恨”。这种个性,被钱澄之称为“佛所谓正知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佛教也逐渐侠义化,尤其是斩钉截铁式的“金刚义”的被提倡,说明佛教也在倡导一种无畏精神。董其昌从关羽死后被封“伏魔帝君”,以及享受“五帝同尊,万灵受职”的待遇中,觉得作为一个忠臣义士,关羽与曹操、司马懿、王莽、朱温这些“生称贼臣,死堕下鬼”的“偶奸大物”相比,何啻天渊之别。基于此,他发出下面的议论:“至人舍其生而生在,杀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与法华一大事之旨何异也。彼谓忠臣义士犹待坐蒲团、修观行,而后了生死者,妄矣。”其言外之意,就是认定忠臣义士合于佛教精神。这是典型的儒佛合一之论。
明末遗民在选择死之时,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正如明末著名学者傅山所言,无论是出家、在家,均有佛性,甚至“受命职官,有受命职官之佛,临戎遇贼,有临戎遇贼之佛”。傅山认为,真正学佛之人,在碰到国难之时,应该“当下承当”。究其原因,学佛可以使人“无畏”。这种佛教的无畏精神,应该说在明末已经与儒家的尽节精神合在一起。这可以从明末就已出家做和尚的人中找到例子。如李弘储,字继起,扬州兴化县人。早年出家,师事三峰和尚。入清之后,时与抗清志士有联系,并受其牵连入狱。出狱之后,还是好事如故。有人劝诫他,他则说:“吾苟自反无愧,即有意外风波,久当自定。”又说:“道人家得力,正于不如意中求之。”又说:“使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为此,吴中高士徐枋叹道:“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焉。”无论是将“汤火”视作“乐国”,还是以“忠孝”作“佛事”,在明清两代鼎革之际,儒、佛两家在忠孝节义上却走到了一起。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