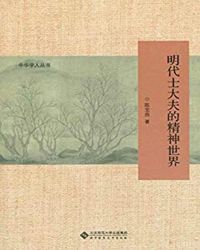四、出处仕隐观的新动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四、出处仕隐观的新动向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仕隐观念,固然是承袭历代士大夫的观念而来,然因明代士大夫深处社会变动相对较为激烈的时代,最终导致他们的出处仕隐观念,出现了诸多的转向。
(一)从出处两分到出处合一
上古之时,尤其是荐举盛行之时,出处合为一途,士欲做官,首先必须得到乡评的认可及其赞扬。一至明代,科举流行,出处分为两途,士人不再凭借居乡的行谊以求仕进,一旦仕进之后,一切考课、铨选之类,无不取决于官员自己的能力。假若官员有能力,即使是乡里所谓的“不肖”,又有几人被罢黜而去?反之,假若官员没有能力,即使是乡里所谓的贤人,又有几人能被察而用之?其结果,则是导致“吏议重”,而“乡评”却转向衰落。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洁洁自好之士”,其中又有几人不居乡借助气势而营求脂田美宅。为此,时人有言:凤有时枭,兰有时蒿。这不但是说士节容易为时风污染,更是从出处合一向出处两分转变之后的必然结果。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开始出现“藏出世于经世”的观点,最终导致“出世”与“经世”趋于合一。此类观念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袁中道。他以谢安石为例,对“出世”与“经世”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梳理与阐述。从袁中道的评述中可知,出易处难,而隐居之福,则更是很难享受。在中道看来,谢安石别有绝人之量,所以很少显示出他的“刚骨”,然谢安石的世情之腻,却与白居易、苏东坡相等。当然,谢安石用世之妙,绝非白、苏诸公所能企及。由此可知,古今事业,有的由才而出,有的从气而出。唯有谢安石,他的事业,从韵而来,至简至轻,若山光水色,可见而不可揽。袁中道进而认为,自汾水丧尧以来,别有一种玄澹脉络,春风沂水,即其流派,无事之事,不治之治,不言而综。这就是“藏出世于经世者”, 而谢安石则深得其中三昧。
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大多偏于儒家的经世精神,肯定“出”。如归庄认为,士君子生当盛世,一旦立朝进入仕途,必须“上则有补于衮职,中则有裨于世道,下则有造于乡里”。换言之,士大夫出仕,则当有益于一方;居乡,则当有补于桑梓。当士君子身处季世,则当自尽其道,至于祸福,完全听之于天。反之,若是持激亢之论,为惊世忤俗之事,为此而“扞文网,触机阱”,这就是不尽其道,理应相戒勿为。换言之,唯有勉强以行道,谨慎以守身,如此而得以免祸,才真正称得上是“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矣”。这就是说,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目中,处显然是一种不得已之举。如明人杨士奇认为,只有普通的“凡民”,仅仅追求个人一己的舒适,而不替天下生民考虑。至于士君子,既然自己已经“明道”,但只能“退食其力于幽闲无用之地”,借此自适,这无疑就是安命守义,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士人的“素志”。鉴于此,杨士奇进而认为,仁人君子的最高境界是出处合一。这就是说,真正的仁人君子,当他们处时,未尝忘记民间百姓,而一旦出仕,亦未尝忘记过去丘园栖遁之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具有“兼济”的特点,无不自得于内心,不会因为穷达而有所改变。
随着出处合一之论的风行,随之而来者,则是出处“得中”之说的崛起。这可以黄宗羲之论为例加以剖析。当丧乱之际,士大夫的行为不一,这是正常的现象。然在黄宗羲的眼中,在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出处选择中,下列两类人的行为均有失误:一类是不食周粟而死,此类死法有炫耀之嫌。如王台辅,字赞化,是国子监的监生。弘光朝廷覆亡后,台辅泫然流涕道:“吾谁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视家中仓廪,尚有余粟,道:“此吾之所树也,毕此而死,亦未为晚。”至顺治四年(1647)的某一天,家中之粟用尽,就聚集邻里乡党,濯衣幅巾,口中大呼“烈皇”,北面再拜,自罄于象山之树,聚观者无不恸哭失声。此时有一僧人路过,持鞭而指台辅道:“丈夫死宜也,恶用是弥街绝里眩耀于人乎?”其后数月,渡河过来的人说,石屋寺有一僧人僵立而死,尚有鞭在其身侧,才知僧人之言,并不妄发。对于王台辅仿照伯夷的行为,黄宗羲重新加以辨析,认为太史公称伯夷“不食周粟”,这是因为伯夷起初归周禄以养老。至隐于首阳,才不再受禄,所以称之为“不食周粟”。假若把率土之粟都视为“周粟”,那么采薇而食之薇,难道不属周家之物,与周粟又有什么差别?这是模仿过程中的一种误会。另一类是模仿桃花源之典,隐居山中。如顺治三年间,温州有一徐氏,约了自己的徒侣数十人,带了农具及所需要的杂物,登上雁荡山之顶,建了数十间房子,再塞断道路,借此模拟桃源。过去30多年之后,亦无人知道他们是否生死。对于这一类行为,黄宗羲亦别出机杼,认为所谓的桃花源,不过是陶渊明的寓言而已。徐氏模拟桃源,也是一种迂腐的误会而已。即使如此,黄宗羲还是对这种“血性”行为有所肯定,他说:“虽然,血性流行,新陈百变,古之所无,不妨有之,古之所虚,不妨实之。王、徐二子之事,不恨今人不见古人,而恨古人不见今人,抑亦可谓善学古人者矣。”
既然黄宗羲对上述两类遗民的行为不以为然,那么,他心目中遗民之正者又是如何?其实,就是出处“得中”。进而言之,遗民的行为,既不能像卑者之茅靡于时风,也不能像高者之决裂于方外,理应是“能确守儒轨,以忠孝之气贯其终始”,达到“吾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吾”这样“两不相忘”的境界,正好处于卑与高之中。在随后的文字中,黄宗羲举出一人,他就是杨时俨,以证明其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得遗民之“正”。杨时俨,字士衡,松江府华亭县人。在明末曾中生员,但在弘光朝廷立国后,就遁于荒外。不久,清兵围困松江城,城内死人无数,而杨时俨却能避开兵火之乱,人无不服其有先见之明。入清以后,他更是选择了“不出”之路,而且对自己的家产不加挂怀,任人取去。杨时俨能守遗民之正,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忘世”,亦即在自己家势兴旺之时,未尝心侈体汰;而当时移物换,自己也就不会志气销沮,即使面对飞来的横逆,也能做到无动于衷,不再与之较量盈亏。(二)“身隐”与“心隐”之辨
在隐居观念的转向上,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对“身隐”与“心隐”加以适当的辨析。辨析的结果,则是对“心隐”的肯定。
为示明晰,不妨先以明初的宋濂与刘基关于隐居的观念作为讨论的起点。就宋濂的仕隐观念而论,他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四皓”、严子陵,还是诸葛孔明、李泌,他们的才能不尽相同,但都足以表暴于一世。换言之,古人并非“乐隐”, “隐”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基于此,宋濂的观念显然偏向于出仕。但出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对此,宋濂也有自己的阐述。这就是说,宋濂主张出仕的本意,应该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不是求得个人一己的荣誉与名声。
若是仔细考察宋濂的隐居观念,显然尚有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不徒以隐为高。这可以宋濂对东汉时期严子陵的评述为例加以分析。宋濂认为,士人平日的问学,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自己所学付诸实践。假如能为贤君所用,得以实践自己的志向,本来就是君子感到高兴的事情。基于此,所谓的严子陵“不屈光武”,其实并不是以隐为高,而是“有所为”,有其特殊的原因,借此以全故旧之义。至于宋濂对陶渊明的评价,则有一个变化过程。宋濂初因称颂严子陵,而对陶渊明以酒自放有所微词。其后,经过细辨,又对陶渊明之志有所认同,认为陶渊明不过是“托酒自适”,而其根本点,则与严子陵相同。二是主张观人之道在于心,借此对“心隐”与“迹隐”加以辨析。宋濂认为,即使一个人混“迹”于朝市,但其心则不忘山林,尚可称之为“吏而隐”;反之,尽管其外在的“迹”是“滞乎山林之中”,但其内心则“艳华趋荣”,无时无刻都在思念市朝,如此很难称之为“隐”。这是典型的肯定“心隐”之说。
刘基的仕隐观大抵亦是如此。细究刘基的仕隐观念,可以从以下三点论之:一是“隐”与“市”之别。刘基认为,“隐”是为了“全身而远害”,而“市”则是商贩所集,是争利锥刀之所。自古以来,就有“市隐”之说,通过“卑贱混浊,足以自秽”,从而使自己之名泯灭。当然,所谓的市隐,并非与市人“同其行事”。二是追溯儒家原始之“隐”的含义。刘基认为,孔子所谓的“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求其志”。换言之,君子之道,遇则仕,不遇则隐。仕与隐,虽属两途,却并无“二志”。就此而论,真正的隐者,并不是“废其身”“丑其名”的市隐,而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三是对各色隐者加以辨析。在刘基看来,博徒卖浆,是“隐之侠者”;放言非圣,是“隐之狂者”;辟兄离母,是“隐之贼者”;颍水以洗耳,是“隐之矫者”;蹲窾水以待聘,是“隐之伪者”;上介山而立枯,是“隐之怨者”;沉湎于酒、不衣冠而处,是“隐之乱者”。所有这些隐者,虽有“惊世骇俗”的行为,却是“有害于道”,不是君子所选择的隐居方式。换言之,真正的隐者,遭遇时运不济,或避世,或避地,或耕或渔,或居山林,或处城市,或抱关而击柝,无所不可,但始终都能保持他们的志向。
宋濂、刘基都是在元末群雄纷争中选择了朱元璋的典型,与他们同时的贝琼,其仕隐观与宋濂、刘基颇有相同之处。明统一天下之后,下诏征召在野诸儒,而嘉兴顾贵和亦在征召之列。顾氏自忖“才不足以有为”,于是“辞于执政”,要求归养自己年已80岁的老母,得以“许而遣之”。对顾氏此举,陈基认为,顾氏并非“辟世之伦而违中害义者也”。为此,他举孔子与其弟子颜子、闵子为例加以说明。当春秋之时,孔子汲汲焉历聘诸侯之国;而其弟子颜子、闵子,均不愿出仕。在陈基看来,两者的出处高下,立能分辨:孔子是急于行道,其目的在于“化人”;而颜子、闵子两人,知时之不可仕,惧怕被人所制。贝琼仕隐观的关键,在于以“心”区分仕隐,亦即“时隐而隐,未始忘乎仕;时仕而仕,未始忘乎隐”。换言之,对于仕抑或隐,不能“泥其迹而论之”,而应“求其心而舍其迹”。
按照明代很多学者的看法,古有隐德之士。这些隐居于山水之间的高士,其高洁之韵如同秋水,其孤清之操可比寒梅。这类隐士在明代变得较为稀有。在明代,所谓的隐士,却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即史料所谓的“以其地远而心近,行凡而迹奇,非伈伈饰名誉,则偲偲规利达。”即使是那些静养枯寂之士,其实也不过是“务为长生以徼福”。为此,吴廷翰开始追求真正的隐士。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应该是抛弃名、利、寿三者之人,如“孤云野鹤”一般,达到一种“无心之至”的境界。吴廷翰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唐寅的诗歌中得到部分的印证。唐寅有一首题为《偶成》的诗,其中云:“科头赤足芰荷衣,徙倚藤床对夕晖。分付山妻且随喜,莫教柴火乱禅机。”头上结发,却不戴冠,身上穿着用荷叶织成的衣裳,一副自由散漫的打扮,随遇而安,不再为一顶进贤冠所束缚,更不为“柴火”一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而打乱了自己坐禅的“禅机”。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士,亦即生活清苦,人格却是何等的高洁。
进入明代中期以后,何心隐、吕坤、袁中道堪称“心隐”“道隐”论的典型代表。毫无疑问,从何心隐的内心来说,他把做官看成是入“樊笼”,所以,还是主张跳出这一樊笼。他认为,人若对樊笼恋恋不舍,即使能够施展自己的高才,也不过是一个“效忠、立功、耿介”的官员而已,于“大道”根本无补。但一旦跳出樊笼,何心隐也不主张做隐士,他认为隐士“无补于朝政”,是一种欺君的行为。所以何心隐最为理想的“出身”,就是像孔子、孟子一样,“出身以主大道”,并使大道趋于“正宗”, “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可见,何心隐跳出“樊笼”之后的归宿,还是“心隐”。吕坤亦有一首《心隐》诗,云:“上隐隐于心,妙诣成独悟。万古无人知,此是天乐处。”可见,在吕坤看来,“隐于心”可称“上隐”,已经达到了“天乐”的境界。
至于袁中道所谓的“以道而隐”,在晚明心学流行的时代,其实就是“心隐”的代名词。袁中道隐居观念的中心内涵,包括以下两点:一是鄙薄“寄物而隐”,追求“以道而隐”。袁中道认为,自古以来的隐君子,大多是寄物而隐,或以山水,或以曲蘖,或以著述,或以养生,都是有所寄托。所寄者为物,亦即必须“借怡于物”,而不是“内畅其性灵”。所以,隐居的关键在于“闻道”,一旦闻道,就能“心休”。唯有“心休”且不再借助外物以求得舒适,才堪称真隐。二是确立自汉以后“道隐”的典型。袁中道认为,自汉以后,以道而隐而又能自适其穷者,当数宋代的邵雍。邵雍洞彻先天之秘,观化于时,一切柴棘,如炉照雪,如火销冰,所以能与造物者为友,而游于温和恬适之乡。他不唯不借力于物,而且融化于道,可谓“深于隐者”。邵雍之后,则只有陈白沙。白沙洞明心地之后,处穷处达,无往而不适,可称真乐。
至明末清初,“身隐”“心隐”之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夫之、钱澄之可谓其中的典型。通观王夫之的仕隐观,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一是通过对陈抟、种放、魏野、林逋四位宋代徵君的评述,确立了自己的仕隐观念。王夫之认为,“夫志以隐立,行以隐成,以隐而见知,因隐而受爵;则其仕也,以隐而仕,是其隐也,以仕而隐;隐且为梯荣致显之捷径,士苟有志,孰能不耻哉?”换言之,君臣之义,高尚之节,都被君子看重。但如何加以判别,则取决于他们“志之所存”。志于仕,则载质策名而不以为辱;志于隐,则安车重币而不足为荣。可见,王夫之通过士人的志,确立了判定隐士真伪的标准,认为辱身贱行,通过高蹈之名而感动当时的君相,借此获得他们的相知,这不过是假隐士而已。二是将生死观念引入仕隐之中,确立了仕隐即为生死的观念。佛教以生死为大事。王夫之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生死之事,属于“一屈一伸之数”,这是“天之化”,非人力所能改变。王夫之认为,君子的大事,在于“仕与隐”。他将正确处理仕隐关系视为一个儒家学者的“生死”。在王夫之看来,对一个儒士来说,出仕是“义”,而隐居则是“常”。只有懂得出仕的真正含义,方可知道隐居。但对君子来说,出仕之道很多,其中最为关键者,则是“要皆以可于心者为可于道”。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看出了“仕与死相因”。既然死都不可畏惧,那么“仕以不可为之中沮”。三是在仕隐关系上,更为偏重于仕。王夫之说:“君子者,以仕为道者也,非夷狄盗贼,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以王良为例,他应汉光武之招而受禄,虽无殊猷,但凭借自己的恭俭而最后身居大位。即使如此,王夫之还是称他“于君子之道尚不远矣”。相反,他对严子陵不仕光武,却持一种完全的否定态度。他立论的依据基于自己对“隐”的真正理解。他说:“隐之为言,藏道自居,而非无可藏者也。”王夫之认为,光武帝定王莽之乱,继承了汉朝的正统,在修礼乐、式古典方面或许尚有未醇,但这也正好说明需要贤者以道赞襄光武。而严子陵却情愿隐居,也不愿出仕,这在王夫之看来,比起被孔子称为“隐者”的沮、溺、丈人之类,在对隐居的认识上更为狭隘。言外之意,王夫之还是主张严子陵应该出来辅佐光武。
从“身隐”转向“心隐”,固然是明代士大夫仕隐观念的一大转变,但随之而来者,则是从“心隐”向“忘心”的转变,同样值得引起关注。庄子有“弃世”之说,释氏有“忘心”之论。即以学佛之人而论,他们舍弃自己的父母妻子,而逃于方外。但就在这“方外”,还是难以逃脱诸如眷属、门庭、交际之类的烦恼,与世俗一般无异。无奈之下,只得又舍弃这些,逃到枯槁寂寞之乡,用茅编篱,远离世俗,与草木鸟兽狎处。时日一久,甚至相忘而不能离去。即使达到如此境界,其实还是有一个“世界”在,只是与“人间世”相比,其牵累稍为轻点而已,但还是有牵累。鉴于此,钱澄之认为,真能弃世,莫如“忘心”。当然,所谓的忘心,并非真的自己将心忘记了,而是心有所用。达臻如此境界,即使日处尘劳,而不见其为尘劳;本来清净,而不必别求清净之地。这就是说,若能忘心,甚至可以达到下面的境界:在世弃世,世本无累。这显然是“有道者”的境界。
(三)“大隐”观的崛起及其勃盛
在明代士大夫群体的仕隐观念中,最为值得关注的转向,就是“大隐”观的崛起及其勃盛。这种观念的崛起乃至勃盛,当始于明代中期以后。如按照李攀龙的观点,“避世”与“玩世”是两个层次的隐居境界。对于那些僻才来说,只能避世,唯有那些通才,才可以玩世。可见,所谓避世,就是隐居不仕;所谓玩世,就是虽则出仕,却又有玩世隐居之心。可见,避世是小隐,而玩世则为大隐。
在大隐观念勃盛的过程中,李贽堪称最为值得重视的一位学者,而且从理论层面加深了士大夫的仕隐观念。探究李贽的仕隐观念,大抵包括如下两个层面:首先,将隐者分为三个等次,一是如梅福之徒,“以生为我酷,形为我辱,智为我毒,身为我桎梏,的然见身世之为赘疣,不得不弃官而隐夫洪崖、玉笥之间者”;二是如严光、阮籍、陈抟、邵雍之辈,“苟不得比于吕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齐桓,孔明之遇先主,傅说之遇高宗,则宁隐无出”;三是如陶渊明之辈,既“贪富贵”, “爱富贵故求彭泽令”,亦“苦贫穷”, “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在这三类隐者之中,李贽最为欣赏者,则是陶渊明之流。他坦然承认,陶渊明清风千古,为自己所不及。但渊明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这一点正好与自己性格相同,所以才对渊明之隐有所偏嗜。在李贽看来,唯有像渊明之徒那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超脱”:一方面,官既懒得去做;另一方面,家事又懒得去理。其次,李贽对“身隐”“心隐”“时隐”“大隐”作了相当仔细的辨析。他认为,所谓“时隐”,就是时当隐则隐,所指即邦无道则隐。讲究时隐之人,显然具有一种保身之哲,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时隐并非难事,只要稍有志节就能加以实践。至于“身隐”,则是以隐为事,而不论时世。在身隐之中,尚可分出数等,一是志在长林丰草,厌恶尘世的喧嚣,喜欢山林的寂寞,因此而隐。二是为人懒散不耐烦,不能事生产作业,而其势又不得不隐。三是如陶弘景之辈,志并不在神仙,却又愿弃人世;如鲁连子,身游物外,却又心切救民;如庄周、严光、陶潜、陈抟之辈,则志趣超绝,不屈一人之下。即使如庄周、严光、陶潜、陈抟之辈,也不过是身虽隐,心实未尝隐。诸如此类之隐,应该称得上高绝,但尚未可称之为大。在李贽看来,只有像阮籍等,才真正称得上身心俱隐。即使像阮籍,尽管可以称得上隐居之大,但还是有“逃名”之累,尚无脱离隐居之迹。原因很简单,按照李贽的看法,真正的隐居,应该是“大隐居朝市”,如东方生之类。所以,李贽的隐居观念,其最后的归结点,还是落实于称颂“冯道之事”,断言其人“真无所不为”。这已经不是在说隐,而是在肯定仕,甚至可以出仕众姓。这是一种古怪的观点,也是一种全新的观点。
除李贽之外,当时支持“大隐”观念者,亦不乏其人,万表、汪道昆可以说是另外的两个典型。万表先是对“吏隐”一称作了重新地诠释。在过去,通常将“吏隐”解释为官员的地位清闲。这在万表看来是一种误解。他认为,真正的吏隐,应该是“以吏为隐”,正如“商隐”是“以商为隐”一样。在此基础上,万表进而断言,凡是有道之士,尽管混迹于名利之场,但他内心所存者,却是众人很难知晓的,这就可以称之为“隐”。其言外之意,就是“大隐居朝市”。尽管从道理上说,隐居莫善于山林,莫不善于朝市。但在汪道昆的眼中,区分隐居之大小,不在于具体的隐居之地,即是“山林”还是“朝市”,而在于隐居者的内心。换言之,即使隐居于山林,若是内心是为了追求“名高”,那么也不过是“小隐”而已;反之,若是内心“不为名高”,即使是隐居于朝市,也堪称“大隐”。这就是说,最终决定隐居之大小者,理应是内心必须无欲,做到内心不乱。继李贽之后,公安三袁是“大隐”论的热心支持者。袁宗道认为,一些人身怀奇才,本可大用,却因世人缺乏只眼,而不被朝廷所用,所以只好颓然放于声酒之间,以自排遣。尽管这些人隐居林下,其自奉却过于王侯,生活相当奢侈惬意。在袁宗道看来,此类人断乎应该归入“大隐”之列,不可与卓王孙这些守财奴为伍。袁宏道认为,是否隐居,关键取决于“我根”是否存在。换言之,真正的“肥遁”,不是“遁山林”,而是“遁我”。这就是说,假如“我根”尚在,即使遁于山林,亦算不得是一个隐者;反之,若是“我根”已尽,即使“遁朝廷”,亦堪称是隐者。而在袁中道的心目中,真正的隐居,是“心隐”。一旦心已隐,那么,就可以不分“烟波”,不分“市肆”。换言之,他最终还是认定“大隐居市”。
大隐观念兴盛之后,随之也就出现了“城市山林”。所谓城市山林,即是士大夫退隐之后,仍居住在城市,却同时享受山林隐居生活。如袁绳之中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正当强仕之年,原本在仕途上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却弃官而归。尽管弃官隐居,却又过着居住之处有“池台花竹之胜”的日子,同样可以享受城市的繁华,所以题其门楣为“城市山林”。此即典型个案。既然城市与山林可以和谐合一,势必导致仕隐观念上又出现新的动向,亦即选择人野相近、独处与人稠相宜的隐居生活。
(四)追求真正的“隐者”
揆诸明代士大夫的隐居实践,其实存在着一种从“有待而隐”到“有赖而隐”的转变。毫无疑问,大多数士大夫的隐居,不过是“有待而隐”。所谓有待而隐,其实他们的心不在于隐,而是时代不适合出仕,只好暂时隐居山野,等待时机,再次出仕。换言之,古人所谓的隐士,并非是伏其身而弗见,闭其言而弗出,藏其知而弗发,而是因为时命大谬,不得不息隐林下。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广东东莞人陈景辉,开始将其藏修之所命名为“南溪小隐”,并进而提出了“有赖而隐”之说。他在回答丘濬的质询时认为,自己不是“有待而隐”,而是“有赖而隐”。所谓有待而隐,就是生非其时,处非其地,出非其族,“驱逐之役日劳乎形,鸡犬不得宁也,室家不得有也,虽欲少憩以斯,须臾不可得也”。而有赖而隐则正好相反,不再有如此众多的牵绊,从而使自己可以随着意愿而隐居。换言之,同是隐居,有待而隐为小,有赖而隐则大。
借助如此转变,最终导致明代“真隐”之人的大量崛起。通观明代众多的史料记载,所谓真隐,应当包括如下三大特色:一是具有布衣诗人的本色。所谓布衣诗人的本色,其实就是“隐者”的本色。换言之,隐者本色,除了所作诗歌并无“长篇”之外,而且所作诗歌,更无“穷 极媚,多其鞶帨,以羔雉媒介当路”的龌龊之行。二是真隐可以以“色”为隐。士人之隐,各有所借。如谢安之屐,嵇康之琴,陶潜之菊,无不都是有托而成其癖。而明末清初人卫泳则认为,真正的隐者,应该是一种“色隐”。他认为,“色有桃源”,即情色之中自有“桃源”。当然,卫泳所谓的借色而隐,不过是有所托而逃,是一种寄情适兴,而不是如世之痴汉那样沉溺,整天颠倒枕席、牵缠油粉,将“桃源”变成了一个“柳巷”。果若如此,反而不能说是“买山而隐”,而是“买山而埋”。三是真隐就是“醉隐”。自古以来,以酒为隐之人甚多,却未必真是好隐。这就是说,他们或因生不遇时,或因才不遇世,只得“窜匿瓶罍,浮泊糟浆以避名而远害”,其实是“有托而逃”。而明人区大相所著《醉隐记》中的醉隐公,却是怀才不仕,无所托而逃于酒,堪称真正的隐者。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