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大夫的忠孝观及其转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二、士大夫的忠孝观及其转向
揆诸明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念,尽管所涉甚多,然究其要者,则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阐释忠与孝的关系,亦即究竟是忠孝不能两全,还是忠孝可以合一;二是梳理忠臣孝子的精神史源流,进而解释孟子所言的大丈夫“浩然之气”,与忠臣孝子之间存在着何种传承关系,以及忠臣孝子所具的侠义精神;三是忠孝的名实之辨,即从名副其实的“愚忠”实践者与名不副实的沽名钓誉者两个侧面,对忠孝观念重加论定;四是从整个明代的社会变动背景之下,进一步解析忠孝观念所面临的众多转向。
(一)忠与孝之关系
明代士大夫在论及忠、孝之间的关系时,首先通过对忠孝概念的定义而对其社会意义加以阐释。就忠孝概念的定义而言,主要集中于忠、义二字。如高拱首先承认人臣侍奉君主必须尽忠,而所谓的忠,其义就是“尽其心之谓”。人臣对君主一旦尽心尽力,那么,就会忧国如家,爱民如子,然后职业克修,事功可建。田艺蘅在论述忠臣这一概念时,将其作了大小之分,末世忠臣,不过是“承顺过而弼拂微”,这不过是小忠而已。唯有能够犯颜直谏,才堪称大忠。吴伟业又将“义”字引入其中,对“忠义”这一概念作了较好的诠释。这就是说,所谓忠,就是“不忘先朝”;所谓义,则是“保素节而出流俗”。
忠孝概念一旦论定,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对忠孝的社会意义加以进一步的阐释。正如明初学者商辂所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士君子读书学问,“所务者忠与孝而已”。可见,忠、孝二字在明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蔡靉认为,在宇宙之间,最为贵荣者,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忠臣孝子”。这些忠臣孝子,是天地之正气,躬行之君子。正如林时对所言,忠孝是与父子、君臣对应的人生大伦,与天地并列。若是舍弃忠孝不言,则“人道几或熄矣”。
基于儒家五伦关系之上的忠孝之德,与朋友之道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可以引用李贽之说加以进一步证明。李贽将忠臣与贞友并论。他说:“世未有贞友而不可以事君者也。故求忠臣者,尤必之贞友之门。”换言之,在五伦关系中,李贽将朋友之间的“贞”,上升到与君臣之间的“忠”相提并论的地位。至于人臣忠孝之道的维系,其关键更是在于人们的“廉耻”之心。而廉耻之心得以维系,则需要有刑、礼。
传统士大夫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明代的士大夫,很多亦陷于这样两难的境地。以罗伦为例,开始时因为双亲尚在,不敢以身许人,亦即出仕。但最后不得不以身许人,尽管可以找出借口,说这不是“许人”,而是“许国”。但一旦以身许国,就不再能全养其亲。而双亲不获全养,而“身将焉许”?这确实是一种两难的窘境。然若细绎“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确实已经道出了传统儒家士大夫忠孝观的精义,这就是以忠统孝。换言之,当忠与孝发生冲突时,孝道理当服从于为君尽忠。揆诸明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念,同样具有偏于忠的一面相。举例来说,如一个人父母俱存,兄弟却少。一旦出仕,遇到君主有难,死之则不孝,不死则不忠。此时又当作何选择?明代理学家吕柟认为:“当是时,君难为重,又非徐庶可比。”这就是说,应该选择为君尽忠。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忠以成孝”之论,显然已经证明了明代士大夫的最终取向,亦即以身许国。古人有“有母而未可以身许人”之说,其意是说不出仕,不食君主俸禄。至于已经出仕,父母同样享受了朝廷所给予的俸禄之养、荣封之秩,这就不能再有“未可以身许人”的借口。按照戚继光的说法,即“如以父母在堂,未可以身许人,则必不可仕。既仕,便当随寓而尽为臣之节,国尔忘家,忠以成孝,不可执古语饰非。”“国尔忘家”“忠以成孝”,这是典型的以国统家、以忠统孝。至于将忠置于孝之上的典型,则可举明末的张煌言。史载张煌言被俘之后,当时地方官员也曾请出了张煌言的父亲,由其父来劝降。但张煌言在复书中却说:“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他日不惮作赵苞自赎。”所以,在复书中自称“不孝”。不听父亲之言,虽说不孝,却是大忠。
当忠、孝发生冲突之时,亦有士大夫选择孝亲。自古以来节士,当遭逢人伦之变的时候,在忠孝的抉择上,往往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关于此,清代史家全祖望举多例如下:
赵苞势不能复顾其母,只应一死自谢,终为恨事。徐庶之从魏,先儒不以为非。然夷考之,则庶竟仕魏,无乃违其初心,岂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维自负远志,长往不顾,亦未为得。独周虓入秦,始终不可屈节,一奔汉中,再徙朔方,可谓烈哉! 注释标题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5《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东王公神道阙铭》,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831页。
这就是说,在忠与孝发生冲突之时,一部分士人确乎“忘亲为难”,有偏于孝的另面相。如汪道昆认为,“窃惟分莫严于君臣,分在则恩不掩义;亲莫逾于母子,亲在则义不胜恩”。一则分无所逃,一则心无所解,在君臣之义与母子之亲之间,并无轻重之分。士人一旦出仕,这是一种“倍亲”之举,无暇顾惜其家,亦在情理之中。这是“以忠为孝”,遑恤其家?尽管如此,汪道昆不得不承认,“忘家易,忘身难;忘身易,忘亲难”。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身者亲之枝也,亲者身之本也。本之其所自出,又焉能忘”?所以,“亲忘我非难,我忘亲为尤难耳”。明清易代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没有选择“诸君子处其易”的方式而为国殉节,反而听从其母之劝:“儿死,其如老人
何?”最后选择了“处其难”这一方式,确实如其所言,是一个“天下大苦人”, 但细究起来,还是一种全孝不尽忠的行为方式。
按照传统的见解,言忠必说“资于事父”,言孝必说“终于事君”。这就是说,服勤就养,昕夕不违,堪称孝子之行。若为君主,可以离亲出仕。瘁躬就列,险夷不贰,亦算得上忠臣之节。若是为了亲人,则可退而归隐。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出仕抑或归隐,而是必须权衡时势,而后决定缓急、去就。所惜者,爵可縻心,位能骄志。无论是耽宠之夫,还是循名之客,为了一己的名利而辞庐不返,冯轼忘归,即使“亲有蒺藜之危”,亦留恋身处盘桓之地。这无疑是忠孝观念的异化,却亦是当时的实情。鉴于此,高拱在论及忠孝发生冲突之时,出于素心自洁、清尚镇俗的目的,主张“慨然逃禄,挽不可留”。这又是偏于孝的见解。
无论是以忠统孝,还是“忘亲为难”,在忠孝论上,无不都是一种偏向之论。除此两者之外,忠孝可以两全之说,则更为值得关注。中国自古有言,“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方孝孺的孝道观,可为此论的注脚。一方面,方孝孺认为,“孝以继志,忠以尽职”; “大孝尽忠,以显父母”; “夫孝为万善之原,移事亲之心,以事君,则忠莫大焉,推爱亲之心以及人,则仁莫厚焉”。另一方面,方孝孺又认为,忠与孝并无二致,唯有“知孝亲”,而后可以“事君”;唯有“忠于君”,而后可以称为“大孝”。
揆诸明代的士大夫,所谓的“忠臣必出孝子之门”,方以智堪称典型一例。史载顺治十一年(1654),方以智已经出家为僧,在高座寺闭关。钱澄之前去探望,寓居报恩寺。在卖卜人周勿庵的店铺中,听到过去曾是宦官的老僧,说起崇祯年间方以智的一件逸事。据这位宦官言,一日,崇祯帝经筵完毕回宫,天颜不怿,忽然叹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如是者再。经宦官跪问原因,崇祯帝才说:“今早经筵上,有展书官陈某,乃陈某子。其父巡抚河南失机,问大辟,系狱候决。某衣锦熏香,展书朕前,略无戚容,不孝如此,岂能忠乎?”宦官跪进道:“展书官旧例皆然,跪近上前,防有不洁之气上触,故衣必鲜华,熏香盈袖,要令展书时芳香袭御坐耳。”崇祯帝听罢言:“既知此例,便当辞官;不然,辞差可也。朕闻新进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抚湖广,与陈某同罪下狱,闻以智怀有血疏,日日于朝门外候百官过,叩头呼号,求为上达。此亦是人子。”言讫,又叹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几,释放了方孔炤,而将陈氏大辟。正是方以智的“血疏”之举,才使崇祯帝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叹。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一直认为忠孝不能两全。李贽却从李贤“夺情”起复这一事件中,对出仕与尽孝的关系作了下面的阐述:
余谓若欲尽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养亲,又持终丧之说以买名,皆无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与庆贺,不穿吉服,日间入公门理政事,早晚焚香哭临,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体国,委身以报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为不孝可欤!天顺反正八年之间,非文达挺身负荷,则曹、石之徒,依然败坏溃烈,不可收拾矣,何莫而非文达行孝去处,而必以区区庐墓哭泣乃为孝耶?吾不知之矣。 注释标题 李贽:《续焚书》卷3《李贤》,86页。
从中可知,李贽对李贤夺情起复一事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这种行为正好是“孝之大者”,忠孝完全可以两全。
(二)忠臣孝子与大丈夫“浩然之气”
无论是为国尽忠的忠臣,还是为亲尽孝的孝子,其间的忠与孝,从精神史的源头而言,无不与孟子所谓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有关。鉴于此,需要从“气”的视角,对忠臣、烈士、孝子加以剖析。
毫无疑问,忠臣烈士的末后一著,无不与“气”有关。曹学佺对“忠臣烈士”有如下称赞:
予观古之忠臣烈士,片言只字,取珍当时,垂范后世,固重其人也欤?而其言亦有足重者。夫忠烈之性,得之天者独完,必有一段激昂直遂之气,蟠结于胸中而不可抑遏,恒先时而鸣,触事而发,以期得当,而报主知,匡世道,有所建立于时。虽为世所不容,而卒遇缺折,其光芒陆离,终不可以泯没。要之,君德为之一光,而世道亦终赖焉。 注释标题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小品》卷1《邹汝愚先生遗稿序》,载氏著:《曹学佺集》,15~16页。
这就是说,忠烈之性,其源头还是那一段“激昂直遂之气”。对于这样的忠臣烈士,在明代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讥其“不善用”,希望“进之于道”。其言外之意,就是说忠臣烈士不免意气用事,缺乏“道”的修养。对此,曹学佺作了下面的辩解:
此非真知人者也,亦非知言者也。何则?造物亦至大矣,中和之气称咸备矣。然使其光风霁日,不寒不暑,可以运四时而成岁功,亦何必为骄阳洹阴、雷电霜雪之迭见哉!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极盛之中,有至衰者伏焉。人情安于所习,以为固然,而倅不可动变,自非察几于微茫之表,转圜乎瞬息之中者,乌能有济。……故善知言者,知其根心,以及政事;知其顺理,而成文章。又知其无小大,无古今,而皆足以发之,不与世俗同。 注释标题 曹学佺:《曹能始先生小品》卷1《邹汝愚先生遗稿序》,载《曹学佺集》, 16~17页。
曹学佺的辩解,可以另一位当时之人的说法加以印证。他就是为曹学佺此说作评述的陆府治。陆氏认为,如果忠臣之言之行尚“有道可进”,就是一种“意气”,而不是“忠烈”。换言之,忠烈不是意气。当天下危亡,偏在厝薪积火,上下恬熙,蛊坏已极,忠烈之士看出其中之病,出自内心的忠诚,发出不同于世俗之言,岂是“逞少年意气,一击沽名哉”!
就“忠臣烈士”与“气”之关系,明末清初人钱澄之更是作了详尽的解析。他认为,自古以来,建天下之大功,犯天下之大难,不幸而为忠臣烈士,成天下之大名之人,无不因为“气”之所激。这种气,集义以生,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正因为此,“金石可毁,而此气不毁;星辰可移,而此气不移;世界可坏,而此气不坏;功业可朽,而此气不朽”。为此,钱澄之以明末东林党人攻击阉党一事,证明忠臣烈士之气,一脉相承,且能感动后世。一般的世俗之见认为,明末国事之坏、东林君子党祸的产生,无不都是因为东林君子相激而成。但钱澄之的观点正好相反,断言:“夫君子之祸,天为之也;君子之激,亦天为之也:不激则祸不成,不激则气亦不见。天盖早构一祸端,以成其必败自势,所以祸其身于一时,而存其气于万世,彼阉然无气者乌足以知之?”明清易代之后,虽然人与事俱已往矣,但还使人读东林君子之书则凛然以生,过东林君子之里则慨然以慕。这是什么原因?显然是受到了东林忠烈之气的感染。
无论是为臣死忠,还是为子死孝,其行为与精神,无不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贯日月、孚木石,甚至被传统的士大夫上升到“可以正万世之人心,位万世之天常”的高度加以认识。追溯这种士大夫精神,则明显导源于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正如明人罗伦所言,诸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一类的举动,无不奠基于“浩然塞于天地之间者”。
忠臣孝子一旦与浩然之气结缘,必然使忠臣具有侠士之风。照理说来,侠客与忠臣之间,尚有一线之隔。具体来说,侠客为知己者死,则完全“动于气义”。若非如此,则为“郭解之假手”,与豢犬吠人无异。忠臣以大义灭亲,则完全“关于庙社”。若非如此,则为“逢蒙之负心”,与哺枭食母无异。鉴于此,君子不受难酬之恩,不树难事之友。然而,真正的忠臣,一身兼具豪杰与圣贤的两面相。如陈继儒在为明代忠臣于谦所作的碑文中,对忠臣作了重新地诠释,认为一方面,忠臣为国,不惜死。唯因不惜死,才造就了忠臣有“豪杰之敢”的一面相,在气势上如黄河排山倒海之势;另一方面,忠臣又不惜名。唯因不惜名,才导致忠臣又有“圣贤之闷”,亦即既能伏流地中万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进而言之,真正的忠臣,显然具有狂、侠的另一面。从方孝孺忠义节烈的行为中,钱谦益已经看出了方氏所具有的古之狂士、汉之侠士的一面。他评论方孝孺道:
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谓之侠。谈笑刀锯,指叱鼎镬,噀血而大书,长歌而毕命,不可不谓之狂。自汉以来,士之矜名行、崇谨厚、卖国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为窟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惊世绝俗之为,圣贤之所不辞也。 注释标题 钱谦益:《初学集》卷29《重刻方正学文集序》,载氏著:《钱牧斋全集》,868页。
细绎钱氏之言,是说方孝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做出如此惊世绝俗的举动,固然符合圣贤的行为准则,但同样具有侠士、狂士的精神。
忠臣死后,慑于奸臣的权威,很多人只能忍气吞声,甚至不敢出来将忠臣的尸体收殓掩埋。这当然是时势所然,也是人之常情。正因为此,忠臣才只能得到侠士的惺惺相惜。所以,每当此时,自然会出来一些侠士,不顾个人的安危,慷慨为忠臣安排后事。如于谦死于西市之后,当时“家人避祸,不敢收敛”。当时有一位都指挥陈逵,奋然说于谦是“第一忠臣”,前往西市拜哭,准备好衣冠,将于谦收殓,并将其棺抬到萧寺。尽管陈逵自己说此举并非是为了“钓豪侠之名”,
却确实具备了古之侠风。
(三)忠孝名实之辨
揆诸忠臣孝子,实有名实之辨。关于此,清人蔡英著有《论名》一文,对此作了详尽的讨论。他说:
世有忠臣孝子,而其后不昌,人以为不获其报。不知名者,造物之所宝,忠孝而受大名,则已厚报之矣。若其后复昌,是犹称贷者之偿其本而加以息也。且人世美名,易浮乎实。苟好名而实不相副,即为盗名。名之盗,天之贼也。得免诛谴幸矣,尚冀后嗣之必昌乎?故古人以名胜为耻,余以为名胜则更可惧。惧之奈何?绝去沽名念,而勉为其实则可矣。 注释标题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1《蔡学博》,34页。
可见,在所谓的“忠臣孝子”中,确乎存在着名实之分。若是美名浮乎实际,好名实不相副,就是一种“盗名”之举。
事实上,忠臣的殉节,按照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说法,除了是一种“痴”情之举外,确实是有邀名的念头在作祟。在李贽看来,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臣子劝谏,岂能入其耳!作为一个臣子,既然早早知道君主不可劝谏,就应该引身而退,这才是上策;明知不可劝谏,但还是要劝谏,劝谏之后,君主不听,才辞官而去,亦算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若是君主不听,还要劝谏,甚至因谏而死,这被李贽斥责为“痴”。李贽这一说法的根据,就是君臣是以“义”相交。士为知己者死,那些无道之君,未尝以“国士”看待臣下,臣下还是一味劝谏,这就是愚痴之举。换言之,君昏则臣必哲,臣不哲,必会流于愚蠢。更为甚者,君主本非暴君,有些臣子却将其诬蔑为暴君,或本来并不需要上疏劝谏,却故意上疏劝谏,这显然是将君父视为“要名之资”,借此举作为自己他日的终南捷径。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李贽在贬斥所谓“忠臣”的好名之风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忠臣中,有些是“与君共戚者”,有些是“受遗顾命者”,有些是“世受国恩无所逃者”。所有这些人,对皇帝所尽的愚忠,确实也是出于内心的真诚。正因为此,作为讲道学之人,绝不能以明哲保身作为自己逃避责任的借口。
就此而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之说,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他认为,忠臣义士,完全是出于一种真“性”,而并非“慕其名而为之”。所谓的“名”,是国家用来报偿忠臣义士者,并希望借此作为“后之忠臣义士者劝”。换言之,真正的忠臣义士,内心并非慕名,亦不以自己的举动而感到遗憾。
顾炎武之所以有此议论,完全是因“拽梯郎君祠”而发。事情的经过如下:当顾炎武路过昌黎时,看到东门有一座拽梯郎君祠。这座祠庙的建立,也有其缘起。当明末清兵“入遵化,薄京师,下永平而攻昌黎”之时,“俘掠人民以万计,驱使之如牛马”。当时的昌黎知县左应选与其士民婴城固守,而清兵攻东门甚急。清兵抬云梯至城下,打算登城。突然出来一人,将云梯“拽而覆之”,因此被清军之帅“磔诸城下”。清兵围攻昌黎达六日,尚未攻下,只好引兵而退,城池得以保全。此事上达朝廷,崇祯帝立刻擢左应选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县丞以下,迁职有差。又过四年,巡抚杨嗣昌巡视到达昌黎,才具疏上请,县里的士大夫全都得以褒叙,将死于此战的36个民兵立祠祭祀。因不知具体拽梯之人的名字,所以杨嗣昌专门上疏请旨,将此人封为“拽梯郎君”,设立专祠祭祀。
在清初士大夫群体中,确乎存在着一种关于忠臣求名的争论。明清易代,很多士大夫视死如归,将自己的以死殉节,看成是一件“喜事”。据姚椿《晚学斋文集》,吴节愍公不从剃发,自缢身亡,在所遗家书中,题曰“报喜”;弘光元年(1645),徐无念阖门殉节,也自称“喜终居士”。可见,明代的士大夫无不以尽忠为喜。但针对士大夫的这种行为,一些苛论者,却将其视为“好名”积习所致。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以自己乃至全家人的姓名,去博取一个好名声,似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实,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忠义激发所致,才能做到慷慨捐生。对此,清人陆以湉的说法,显然较为平实公允。他认为,这些人的慷慨就义,“实足以扶翼名教,愧天下后世之苟且图存者?如是,则好名正足贵耳,奚病焉!”
忠臣以死殉节,完全出于内心的真诚,并非为名,无疑需要对“愚忠”问题加以重新的认识。这可以清初江阴城守一事为例加以解剖。当清兵入关之后,士林无羞耻之心。无论是居高官之人,还是享重名之人,无不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至于那些封疆大帅,亦无不反戈内向。在如此所谓的“率土归仁”的大势下,江阴作为弹丸下邑,却在典史阎应元等人的统率下,慷慨守义,甘心殉节。如此举动,确非“识时命”者所为,而且是“势类螳张,愚同犬吠”,但更是“愚忠”之举。就具体的功绩来说,若过去守京口之人亦能如此,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 这种愚忠的精神,其意义远不止此。正如清人韩菼所论,此类顾纲常、思节义的举动,“谓之愚,则诚愚;谓之忠,则未始非忠也”。换言之,这种“竭忠于所事”的行为,尽管被新朝视为“洛邑顽民”,但新朝的“圣天子”同样“必乐得而臣之矣”。
(四)忠孝观的转向
假若深入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探讨其忠孝观念的内涵及其变迁,无不显示出具有转向的倾向。举其荦荦大者,可以从下面几点论之:
其一,在臣子尽忠问题上,已仕者与未仕者必须有所区别。如明代学者王廷相对君臣之义的等次作了区分,认为随着“名分渐微”,臣子为君尽忠之责随之渐轻。他认为,“君臣,天地之大义;节义,生人之大闲”。守死之人,既称得上是“仁人”,亦是“义士”,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作为“重臣”“亲臣”“近臣”,为义而死,或“远臣”为职守而死,这无疑是义不容辞的事情。相比之下,若是开始出仕,至后归隐不仕,而且晦名不显,他们不再承担君主的执事,那么“不死亦可”。碰到国家有难,士大夫之名被举荐而达于君主之前,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可以“死于义”,二是可以“避而不仕”。至于士人之名不达,几乎与庶民相同,那么既可以选择“守义不仕”,亦可以出仕。
正是因为对君臣之义的等第作了区分,所以在尽忠问题上,清初明遗民更是将已入仕与未入仕之人作了严格的区分。如孙奇逢说:“古来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后亲,未入仕者先亲后君,各有攸当。”屈大均也说:“人尽臣也,然已仕、未仕则有分。已仕则急其死君,未仕则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职守不同,享受的待遇有异,自然应尽的义务亦就不同。
其二,反对将忠孝绝对化,随之而来者,则是认为忠臣并无定评,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在明代以前,已经通行这样一种说法:“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申生之孝,孝而过者也。”明朝人江盈科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进而认为,“项羽之英雄,英雄而过者也”。他拿这些作为例子,无非是为了证明,假若忠、孝、英雄这些观念的实践行为,变得太过,也就是将它们绝对化,反而会变得无用。显然,在忠、孝这些观念上,江盈科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化的观念。
自小接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无不希望自己出仕以后能做一个忠臣。但是,什么是忠臣?究竟是犯颜直谏、激浊扬清者是忠臣,还是居官不须岳岳,处事一概平和为忠臣?从明代的士风、士气乃至士行来看,其实也很难简单作一选择。这不仅仅决定于个人的性格,而且与时代乃至风气有关。若拿孙丕扬与申时行作例子,就能看出两人立朝的不同。据钱谦益言,当他初中进士时,见到了孙丕扬,孙氏对他大为器重,对钱谦益说:“子后日当大任,须是激浊扬清。”后又见到申时行,时行却对他说:“居官不须岳岳,要令国家享和平之福。”同是对后进的鼓励之言,所说却是迥然有异,从中不难发现两人的立朝大概。可见,同是君子,其性格的不同,同样可以造成为官风格的差异。
其三,将忠臣分为“大忠”与“小忠”。如在忠义观念上,李贽将“大忠”与“小忠”作了区分,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新动向。李贽立论的事实依据是建文朝臣子高翔与程济的不同行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同结果。根据史料的记载,高翔在靖难之役中死于忠义,而程济则以智脱免。关于程济随建文帝出亡逃难,几达数十载,其事实准确与否在此姑且不论,单从两人尽忠的态度而言,显然李贽更为肯定程济。两者的差别在于:高翔以杀身为忠,其结果则反而使自己的族属之亲,甚至祖考之骨,也一概未能幸免,这在李贽看来不过是一种小忠。至于程济,却是以智术为忠,其结果则能“致其主脱走,逍遥于物外,老送归阙,还葬西山”,这在李贽看来是一种出于内心真诚的大忠,通过“处之最远”的方式,而达到“所全最大”的目的。可见,在李贽心目中,已不再以死与生的行为来判断人臣之忠义与否,而是以人臣内心真诚与否作为判断的标准。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从韩通拼死与宋太祖赵匡胤相争的事实中,对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忠不易言,尤其是在那些积乱之世。王夫之并未将韩通许为周之忠臣,仅仅将他比为袁绍、曹操之讨董卓,刘裕之诛桓玄。与此同时,王夫之也认为韩通并无与赵匡胤争夺天下之心。因此,韩通与赵匡胤相争,不过是人之常情,是心中有愤、有气而已。当然,正值积乱之世,与冯道、赵凤、范质、陶榖之流的“无恒”相比,韩通应该说还是“有生人之气”,属于“有恒”。
其四,对忠臣犯颜直言与廷杖加以反思。明自中叶以后,士大夫峻严门户,看重意气,其中的贤者若是敦励名节,居官有所执争,清议随之翕然归之。然建言之人,分曹为朋,大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附取宠,则与之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于是“一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故当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淆”。可见,忠臣的犯颜直谏,固然具有沽直好事的一面,但其中亦自有公正的是非。
这就需要对明代忠臣的犯颜直谏之举以及由此引发的廷杖作一些反思。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说,很多明代皇帝坐上皇帝宝座一久,就习知人情。于是,皇帝每次见到臣下的条陈奏疏,无不将其视为一种“套子”,也就是俗套。即使有的臣下直言激切,指斥乘舆,皇帝也全不动怒,将他们的奏疏“卷而封之”,认为这些臣下不过是想借此沽名。若是将其处置,正好成就他们的名声。对此现象,明人有两种看法:于慎行加以肯定,称之为“圣明宽度”;但宋纁则加以否定,认为“时事得失,言官须极论,正要主上动心,宁可怒及言官,毕竟还有警醒。今若一概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无痛痒,无药可医矣”。
暂且不论两人所论的是非,但至少有一件事需要加以关注。即明代士大夫开始对人臣的犯颜直谏问题开始加以反思。君臣关系在明代事实上出现了以下两分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君不君,则臣不臣”。说通俗一点,即君若是不像一个为君的样子,那么作为臣子,就可以不向这样的君主称臣。另一种观点认为,“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其言外之意,即君虽然不像一个为君的样子,但臣还必须向这样的君主称臣。两相比较,前者应该说是相对主义的君臣观,亦即君臣关系的维系是有条件的,即君首先必须是一个圣君;后者则属于绝对主义的君臣观,亦即承认臣子对君主的服从是绝对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即使君主是一个昏君乃至暴君。在此两者之外,即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即“君君、臣臣”,亦即“纲常正而品物遂”,换句话说,也就是君臣之间相处和谐,君是一个圣君、仁君,臣也是贤臣、能臣。明朝人罗钦顺所持即是这样一种理想观点,并认为这种“君君、臣臣”,是《春秋》所确立的,所以有功于万世。罗钦顺进而认为,事君之道,不同于朋友之道,应该做到“忠告善道”。他说:
“忠告善道”,非友道当然,人臣之进言于君,其道亦无以医此。故“矫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矫则非忠,激则非善,欲求感格,难矣。然激出于忠诚犹可,如或出于计数,虽幸而有济,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注释标题 罗钦顺:《困知记》卷上,16页。
由此可见,臣下理想的事君之道,固然需要力戒“矫激”二字,但更应坚守“勿欺”二字。
将完全出于忠诚的犯颜直谏,视为一种“矫激”之举,而非理想的事君之道,显然在明代士大夫群体中引起了共鸣。如于慎行就对人臣的犯颜直谏加以批评。他分析道,即使犯颜直谏不是出于“为名”,仅仅是为了让君主听从自己的劝谏,但其结果则有好坏之分:好者“上从之而不受其名”,则“主、臣俱荣”;坏者“上不从而己受其辱”,则“过归于上,而名成于下”。这显然不是“纯臣之本心”。汪道昆对那些过分为了意气的“直言”,同样持一种反对的态度。若是凭一时意气而直言,导致身亡,则显然是“言与骨俱朽”的无用之举,最后必然会流于“尚口而为名高”。在汪道昆看来,臣子所自负的“直言”,必然流为好、坏两端:好者是“愚直”,是“朴忠”,还称得上是“与天为徒”,尽管其言并不中款,但还算“直者无失”;坏者“与人为徒,大言为狂,小信为谅,蔑礼为绞,讪上为翘,近名为名高,乘捷为径待”,所谓的直言,更是流为“不诚”。明末清初人徐枋,则更是认为臣子上言劝谏必须“和平”。在徐枋看来,臣下轻率地“批人君之逆鳞”,结果必然引发君主的雷霆之怒,但亦并不能因此而持一切“诡随”君主的态度,而是在上言时言词必须平和。他说:
遇事必言,言必和平,其气恻怛,其词反复抑扬,开陈善道,使听者为可受。受者为不争,而后吾言入矣。夫君子之建言也,将以匡君德而济国事也,非以较胜而争强也,非以翘过而讦直也。若持之以好辨之心,临之好胜之气,鲜有不偾者矣。若言出祸随,死亡继之,而所谓和平恻怛者往往能卓立而不变,而好辨好胜翘过而讦直者或变易委靡,一旦化为绕指而不可复振。 注释标题 徐枋:《居易堂集》卷10《书昌黎潮州谢表后》,233页。
徐枋何以有如此之论,其实还是本于一个普通的道理,即气平者不挠,而气骄者易馁。
关于东汉党锢诸君子,过去的史籍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这些君子忠以忘身,是一种大节;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些君子激以召祸,是一种畸行。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两种评价均不赞同,认为人臣事主,是否“捐身”“死之”,理应取决于对社稷有否裨益。他以明代杨继盛、杨涟为例,与汉代党锢诸君子进行比较,认为杨继盛直击严嵩,虽死却正;杨涟专劾魏忠贤,其死有光。至于汉代党锢诸君子,则是舍本攻末,根本无法与杨继盛、杨涟相颉颃。
明代忠臣直谏的结果,则是“赐杖大廷,裸体系累”。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并不以此为辱,而天下之人,因为他们抗疏成名,更是“羡之如登仙”。这种“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的现象,正如明人于慎行所言,尽管并非“盛世所宜有”, 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风气。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人臣事君之道尤其重视,认为尽管士可杀不可辱,但士之受辱,究其原因不在君主,而是士自己所致。随之而来者,则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王夫之认为,臣子因为直谏而被廷杖,这是三代以下的一种“恶政”,是人君“毁裂纲常”的大恶之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臣子不惜一死以俯受廷杖,甚至借此自旌其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内心有“他日复列清班为冠冕之首”这样一种庸俗的怪念头在作怪。
一旦对君臣关系加以梳理与反思,其结果则必使君臣关系回到孟子之论的起点,这就是君为轻、社稷为贵。在明代的忠臣中,于谦曾经坚持此说。从诸多史料记载可知,孟子显然也是一个“急于仕者”,热衷于出仕为君主服务,甚或有“少则慕父母,仕则慕君”。但另一方面,孟子亦有这样的说法:“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就是说,在君臣之间,尽管臣下有“慕君”的诚心,但并非由此决定了臣下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在后世的演变历程中,孟子此说已经异化,至明代流变为一些学者之论,即“君虽草芥视臣,臣必当腹心视君”。对此,明人熊开元直接加以贬斥,大抵已经证明,绝对主义的君臣关系,已经开始向相对主义的君臣关系转变。
其五,忠臣应该行权。忠臣是愚直的典范,这一点没有错。但在有些时候,忠臣不应该一味地鲁莽,而是应该行权。明末清初,化名“名教中人”所著小说《好逑传》,对忠臣的直言相谏问题也作了新的探讨,主要包括下面两点:一是忠臣应该有“权术”。小说作者借助男主人公铁中玉之言,认为“为臣尽忠,虽是正道,然也有些权术,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见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讳,不但事不能济,每每触主之怒,成君之过,至于杀身,虽忠何益?”其二,谏臣言事,应该讲究一种方式方法。小说记铁中玉云:“谏臣言事,固其职分,亦当料可言则言,不可言则不言,以期于事之有济。若不管事之济否,只以敢言为尽心一塞责,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捕风捉影,哓哓于君父之前,以博取高名者,皆忠臣矣,其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
忠臣必须识得时务而行权,对此王夫之以宋人文天祥为例,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王夫之肯定文天祥是忠臣,称他以儒臣起义,败而不挠,最后从容就死,若讲“忠贞”,几乎无人能超越文天祥。在王夫之看来,文天祥为赵氏宗社谋可以称得上忠,但他自谋所以效忠之法则是一个缺失。这一判断的理由如下:“海上扁舟,犹存中华之一线,等死耳,择死所而死之”。换言之,这不免有以自己之死而钓誉之嫌。不仅如此,王夫之又指出文天祥是忠臣误国。当父母病革之时,孝子的心态,其实就与当君国危亡之时,忠臣的心一样。当然,这种忠臣误国,不过是“忠而过”。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不得“行权”,不知“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的道理。
其六,按照传统的观念,无论是忠臣,还是良臣,都是令人称道或艳羡的人物典型。若是将忠臣与良臣相较,传统时代的人们还是喜欢做“良臣”,或不是“忠臣”。无论是为人之臣,还是为人之子,“忠孝”一名,均不是臣、子所乐之事。究其原因,就是忠臣与孝子的对立面,往往出现了“昏暴之主”与“顽嚣之亲”。这就是说,忠臣、孝子的成名,建立在归过于君亲之上。鉴于此,明人赵世显说:“忠孝,非臣子所乐也。”
如果有机会让士人选择,无不愿意做“良臣”,不愿做“忠臣”。宋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颁发给陈少阳的诰轴,在诰文中感叹道:“呜呼!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以为良臣已荷美名,君都显号。忠臣身婴祸诛,君陷昏恶。”这应该说不仅仅是皇帝的感叹,作为臣下者也均有同感。若是做一个良臣,君臣之间其乐融融,均能获得一个好的名声,何乐而不为!若是做一个忠臣,其结局就相对显得不妙了,忠臣通常因忠谏而获罪,甚至被皇帝所诛杀,其结局则是让皇帝陷于昏君的恶名。这一点,应该说做臣子的都明白,但为何还有很多人甘愿冒杀头之罪而去做忠臣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臣子很难遇到明君,所遇者多是昏君,君虽昏,他们却还是想尽一个臣子的责任,于是只能冒死进谏;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们不能不在朝内出了奸臣的时候,挺身而出,言无不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两者的相合,才使历代不乏忠臣。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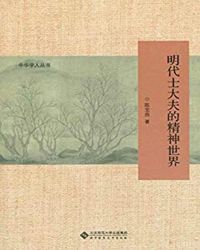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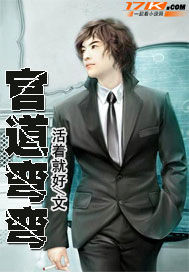

![种太阳特训学校[系统]](/uploads/novel/20240117/86b88a88a55590dec3c53b7b5d4165f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