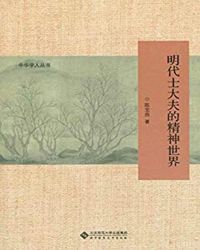三、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三、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明代社会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自明代中期以后,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无不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动荡与变迁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势必导致由法律与礼制所组成的国家控制力量的削弱,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获得了较多自由活动的空间,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显得多姿多彩。
进而言之,社会的整体变动,同样导致传统儒家伦理面临来自商业社会的诸多挑战,并使其陷入困境,诸如儒家“五伦”的排列顺序受到了质疑,夫妇或朋友两伦已经上升为五伦之首;儒家的“五常”也受到了很多经商者的怀疑,甚至发展成为有人骂“五常”为“五贼”的极端之例。即使是五伦中的夫妇一伦,同样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如妇女不再对男子逆来顺受,随之在当时的妇女中出现了“妒妇”与“悍妇”现象,与之相应的则是男子“惧内”之事亦不乏其例。至于士大夫为妇女在男女关系中所处地位之卑贱而鸣不平者,更是大有人在。在此基础上,妇女的群体人格也发生内在的转向,亦即从礼教闭锁世界中的妇女人格,转而变为一种多样化的妇女人格。
与此相应,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出现诸多的转向,诸如:通过君子、小人之辨,士大夫对君子、小人持较为理性的看法;面对生死抉择,士大夫的生死观念出现儒、佛、道合流的倾向;面对出处、仕隐的选择,士大夫开始对“心隐”有所肯定,随之而来者,则是“大隐”观的崛起及其勃盛;面对忠孝、节义的抉择,士大夫转而持忠孝可以两全的观点,并对传统的气节、节义观念进行审慎的理性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新的节义观念;通过对英雄观的全新疏理,士大夫确立了英雄崇拜的观念,进而通过英雄、大众之辨,一种重视平民大众的观念得以确立;通过文、道合一与文、武之辨,文、道与文、武合一的趋向开始形成;通过雅俗之辨,并经过由雅趋俗或由俗返雅的过程,使雅俗两分演变为雅俗兼备。
明清易代,两朝鼎革。随着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明代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历程戛然而止,甚至开始出现波折与倒退。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一)礼教秩序的重建
正如研究者周启荣所言,为了改变自己的历史境遇,清初的儒家学者在探讨道德、经典知识和社会秩序时,更强调礼的中心作用。礼开始影响各种各样的思潮,诸如纯粹主义和古典主义,试图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以便更好地应付一大批自晚明以来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在清初,思潮的主流是与绅士试图改革文化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文化已在16世纪因受商业化和都市化的影响而出现戏剧性的转变。于是,清初强制取缔都市化文化的各种形式。清初的礼教主义者通过扩大家族关系的束缚以强调道德修养或增加社会团结,目的是为了有助于重建绅士作为地方社会中思想、道德和社会的领导者。
1.礼教的重建
通言之,满洲铁骑入关,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清两朝易代、鼎革,势必会对士大夫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其结果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在清初,保守的文人学士力图把僵硬的道德准则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康熙年间严查禁止小说、戏曲的行动,已经足以证明,清初的统治者从“正人心,厚风俗”的目的出发,将小说、戏曲视为“败俗伤风”的“非圣之书”而加以禁绝。
清初重建礼教的过程,大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礼”与“情”的关系问题上,重新转向以“礼”抑“情”,导致士大夫的妇女观开始趋于保守。晚明妇女自我意识增强以及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变所带来的妇女解放的一线光明,至清初已被理学的乌云遮盖得一无所有,妇女仍然落入礼教的重压之下。这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讨论:
一是在“礼”与“情”的关系问题上,清初重新转向以“礼”抑“情”。这可以清初文人学者张尔岐、杜濬两人的相关之说加以讨论。就“礼”论来说,张尔岐对“礼”进行了重新诠释。这种新诠释,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首先,张尔岐说:“夫礼,抑人之盛气,抗人之懦情,以就于中。天下之人质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为道裂,指礼之物而赞以坦易之辞,以究其说于至深至大至尽之地,所以坚守礼者之心而统之一途也。”尽管有将“礼”归于原始的“中庸”的色彩,但其最终目的还是想让人心“守礼”,进而“统之一途”。其次,张尔岐又说:“礼者,道之所会也,虽有仁圣,不得礼,无以加于人。则礼者道之所待以征事者也,故其说不可殚。圣人之所是,皆礼同类者也。圣人之所非,皆礼之反对者也。”与晚明学者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不同,张尔岐不得不又重新回到礼教最为传统的老路,亦即以圣人的是非作为确立礼教的准绳。就“情”论而言,杜濬尽管强调“情”的重要性,但他所谓的“情”,已与汤显祖为之大唱赞歌的“情”迥然不同。换言之,虽然杜濬仍提倡“情贵与壹”,然而这种“情”已经流变为“忠”“孝”“贞”的同义语,其目的还是为了维系传统的纲常伦理秩序。与之相应,清初官方编修的《明史》,其中所收的节妇、烈女传比《元史》以前任何一代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说明编修者所刻意追求与宣扬的不过是妇女的节烈之事。而清初宋嵋编辑的《女鉴》一书,“述诸贤行,而于节烈之事尤致意焉”, 事实上是与清初崇尚“节妇”的风气遥相呼应的。可见,从晚明的“情女”,到清初重新倡导“节妇”,无疑就是明清之际妇女史演进过程中的一大波折。
二是在妇女观上,与晚明诸多学者开放的心态与意识迥然不同,清初学者的妇女观转而趋于保守,随之而来的则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清初重新甚嚣尘上。如王夫之云:“不可拂者,大经也。不可违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道之正也。”相关的看法,王夫之尚有许多,诸如:“故圣王之治,以正俗为先,以辨男女内外之分为本。权移于妇人,而天下沉迷而莫能自拔,孰为为之至此极!”“妇人司动而阴乘阳,阳从阴,履霜而冰坚,豕孚而踯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国有之,国必破;家有之,家必倾。”“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阴之干阳也。”对于历史上的母后临朝,王夫之则断言“未有不乱者也”。即使像东汉邓太后那样,以“得贤名”,但在王夫之看来,也不过是“小物之俭约、小节之退让而已,此里妇之炫其修谨者也。所见所闻,不出闺闼,其择贤辨不肖,审是非,度利害,一唯琐琐姻亚之是庸”。最后,王夫之认为,凡是“良史”,就不应该奖励“妇贤”。至于那些事奉女主的臣子,更不是“丈夫之节”。又如清初学者陆世仪亦认为,教育女子,“只可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究其原因,就是妇女识字以后,可以治理家政,治理货财,借此免除丈夫的劳累。然如果知道书义,亦即知晓读书的道理,不但没有用武之地,反而会出现“导淫”的恶果。随后,陆世仪以李清照为例加以说明,认为如果李清照不知道书义,就未必不是一个好女子。所有上述言论,无非为了强调妇女从一而终,男女内外有别,以及反对妇女从政乃至干政。就清初妇女观而言,与晚明相较,无疑是一种退步。
其二,与晚明士大夫自我意识渐趋高涨不同,清初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开始趋于衰落。明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个性的解放,除了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之外,同样得益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苏学”的复兴。但到了清初,士大夫开始对苏轼持一种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如王夫之曾将贾谊、陆贽、苏轼三人进行比较,认为此三人尽管形迹颇为相似,但从根本上说,苏轼不过“情夺其性”“利胜其命”, “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甚至“取道于异端”,很难与贾谊、陆贽“颉颃”在王夫之看来,苏轼兄弟,“益之以泛记之博,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进而倡导“率吾性,即道也;任吾情,即性也”之说,已经与“君子之学”的严于律己与和平温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流于“群起以攻君子如仇雠,斥道学如盗贼,无所惮而不为矣”。
与明代士大夫对异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不同,清初士大夫重新开始在正统与异端之间确立一道水火不相容的鸿沟。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异端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说:“夫君子之道异于异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行,以其心也。心异端之所欲,行异端之所尚,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动天下之利于为儒,则欲天下之弗贱之也,不可得已。”可见,王夫之所谓的异端,其矛头已直指儒家内部的异己分子,进而将“辟异端”归结为“学者之任,治道之本”。至于“异端”所论治国之术,诸如“黄老”“申韩”之类,王夫之均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们“与王者之道相背戾”。
随之而来者,则是士大夫在人格追求上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从“奇异”转向“平易”;二是从“狂狷”转向“完人”。
与晚明士人崇尚“怪人”“奇士”不同,清初士大夫对“怪人”“奇士”作了重新地论定。王夫之对“怪士”殊无好感,他说:“怪士不惩,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犹惜之。大经不正,庶民习于邪慝,流俗之论,以怪为奇,若此类者众矣。”尽管魏禧承认天下的“大节奇功”,决非那些“寻行数墨之人”所能辨别,然奇士的举动、议论,不单惊心骇目,实有一种“大言嚣气”。这就容易被“轻浮险躁之徒”所假借,不但为老成人所抛弃,而且其弊至于“祸身”。至清初李塨,在《富平赠言》中,专列一条“戒奇异”,主张从“至平之易”的“仁心”“仁政”,导引出“平地成天”的“至奇”“至变”,而不是“假鬼神、好元虚、说梦幻”,甚至去讲“六壬、奇门、南宫、剑客”。果若如此,不但无益,而且容易“杀身祸世”。至此,最终确立了从“奇异”向“平易”的转变。
众所周知,晚明是士大夫追求个性狂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狂人”的时代。明清易代之后,士大夫开始对“狂人”产生怀疑。如王夫之提出一个“惧”字,与其说是借此规范人君的行为,倒不如说是通过“惧”“慎”来规范士人的行为。而张履祥则通过“恭俭”二字,而对士人之“傲”与“狂狷”提出批评。在他看来,“恭俭”二字,是士人“立德之本”,否则就会流于“傲”“侈”之“凶德”。尤其是“狂狷”,张履祥亦开始提出批评。他认为,假若士人“狂”而不能“进取”,就会“轻世肆志”,最终流为“荡”;假若士人“狷”而不能“有所不为”,就会“龌龊拘谨”,最终沦为不如“胫小人”。如此狂狷,实与“乡愿”无异。至于钱澄之眼中的“完人”形状,更可证明晚明士大夫人格开始从极于一端的狂人、怪人、僻人、痴人,转向中庸的“完人”。钱澄之眼中的完人就是钱尔斐,其特点就是不但应该“风流蕴藉”,立身制行可以与魏晋之人相似,但同时也应该“有别趣而不僻”“有逸兴而不荡”“有深情而不痴”。总而言之,就是对待事物持一种“不痴”的态度,如此才能做到“不忘名而不以名自累,不隳节而不为节所苦”。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舜之赞尧,孟子之赞舜,都说他们是“舍己从人”。老子也说:“为人臣者,为人子者,无以有己。”又如齐公子元厌恶懿公,就称之为“夫己氏”。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学说中,无不将“己”字视为一种“有我之私”,所以主张克己、舍己,内心不能有己。此外,诸如传统典籍中所言“奉己”“适己”“专己”之类,无一是赞美之词,而是一种贬义之词。
明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乃至高张,显然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动。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开始趋于衰落。这可以钱谦益与归庄为例加以说明。钱谦益将“无我”与“有我”作了很好的区分:所谓无我,就是“至公”,也就是“公其身于天地万物,而不以天地万物与于吾身;公其身于天地万物,则吾之身即天地万物也”。反之,“以天地万物与于吾身”,就是“有我”。“有我”之人,即使“摩顶放踵,迂其身以为天下”,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自私。其言外之意,就是要从“有我”回归“无我”。归庄则将自己的居住之处称为“己斋”,从中就牵涉到他对“己”的重新理解。根据他自己所言,“己斋”的命名,实际上含有下面两层意思:一是所谓己斋,就是自己之斋,犹言我之所居。这看起来很简单,但结合清初之史实,同样蕴含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归庄自己所言:“既身陷左衽之邦,不能自拔,不得已,就其所居之处,指为己之斋”。这显然是一种民族气节的独立性。二是所谓己斋,就是恪守孔子所言的“古之学者为己”。归庄一言道出其意:“我平日矫矫岳岳,以节义自矜,客气也。作为古诗文,怪怪奇奇,惟恐天下后世之不我知,好名之心也。自诡他日建立奇勋伟绩,以匡国家,以显父母,虽志本忠孝,亦出位之思也。以今观之,气节非有他,不过如处子之不淫耳。文章士君子之一端,皆不足以骄人。事业存乎遭遇,所不可必,况自顾犹难当大任。从此将进而求之,除其客气,克其好名之心,敛其出位之思,而勉强学问,惟日日孜孜,求所以益我身心者,致养其内,而不求于外,为今日之所当为而不计他年。”可见,归庄所谓的“己”,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儒家传统的老路上来。
其三,对“士气”加以重新反思,进而强调“去气”“平气”。明代士气“躁竞”,无疑是清初士大夫的普遍看法。为此,导致清初士人对明代的“士气”进行反思。如王夫之认为,“士气”之说的出现,恰好代表了“世降道衰”。细究王夫之对“士气”的看法,尚可概括为下面三点:一是士气对天下“无裨”。二是重视“士道”,反对“士气”,认为士气就是习气。三是解释“气”为“用独者也”,而士气为“合众人之气以为气”。事实确实如此,晚明士人之合,往往是“声气相应”。可见,王夫之对明代士人的结社颇有微词。
陈确更是著有一篇《去气说》,提出了“去气”之说。陈确“去气”说的根基,显然建立在品茶与品酒的道理之上。如径山、龙井茶,并无多少味道,松萝茶却香味很佳,然论茶品的高低,松萝茶明显不如径山、龙井。品酒的道理大抵也是如此。一个真正擅长酿酒的高人,在他的眼里,举凡酿出的酒,有酸、甜、苦之病,还算不得失败,唯有“满口是酒气”,才算得上是酿酒失败。由此说明,酒之至者,没有“酒气”;茶之至者,同样没有“茶气”。以此来看时文、诗歌、古人,无论是“名士”,还是“善知识”,他们的作品,“人必望而知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有气故也”。当然,陈确所要除去之“气”,并不是孟子所谓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而是一种“习气”,进而达臻一种“人自所不见”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境界。
明代士风颇显“躁竞”之态,这是人所共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代盛行陆王心学。大体说来,在程朱的门下,多恭敬撙节、退让之士;而在王阳明讲学的门下,却不乏“躁竞”之徒。明代士人得此之病,尤以姚江、东林两派为甚,最终导致士大夫群体中蔓延一种“气傲心浮”之病。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对“气傲心浮”提出了批评,认为“傲”的毛病可以流为“戾”“狠”;而“浮”的毛病,则会流变为“薄”“轻”,最后趋于“邪佞”。为此,张履祥提出了两大治疗之方:一以“敬畏”治疗“傲”病,二以“诚实”治疗“浮”病。基于此,张履祥进而提出“平气”之说,作为治疗士风“躁竞”的良方。换言之,就是要通过“持敬功夫”或“持养功夫”,用来克治“习气”或平日的“暴气”。
当然,清初礼教的重建,不仅仅要求妇女、士人遵守礼教,同样体现在丧礼的恢复上。有一个事实值得再提出来加以讨论,就是在晚明时期,竟陵派的钟惺,在丁忧去职之后,枉道游览了武夷山,还写了一篇游览武夷山的游记。照理说来,钟惺为人严冷,具有至性,不应如此“昧礼”。即使如宋代的苏轼兄弟,号称为人放旷,也能在居丧期间,禁断文字。然让人奇怪的是,当谭元春为钟惺撰写墓志时,对于钟惺所为的这一件事,既不唯隐避,也没有微词,反而称赞钟惺哀乐奇到,并非俗儒所能蠡测。这是晚明士大夫的风气,即对传统礼教多有蔑视。入清之后,像阎若璩这样的大学者,同样也被礼教重建的历程所迷惑,对钟惺违反丧礼之举提出批评,认为三年之丧,属于“天下之通丧”,理应为天下之人所共同遵守。
传统礼教得以重建的结局,就是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的儒家“三纲”重新得到加强。为臣当忠,为子当孝,为妇当节,这已为传统社会的大众所共知。至于读书通古今的士大夫,畏于“名义”,更应该知道如何选择。然让归庄感到惊讶的是,当甲申、乙酉之际,士大夫在面临忠孝、节义的选择时,与传统儒家的“名义”相当悖戾。随之而来者,则是士大夫重建“三纲”之说甚嚣尘上,进而与清廷的政策桴鼓相应。
2.社会秩序的重建
随着晚明礼教藩篱的败坏,传统的等级秩序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受到来自各方社会力量的冲击。明清易代之后,经过新朝的多方努力,社会秩序得以重建。揆诸清初士大夫的言论,无不为了迎合社会秩序的重建。即以“奇士”为例,晚明士大夫所崇尚的奇士,大多“矫尾厉角,四目两口,崭然自异”,显与平常之人不同。入清之后,钱谦益已将奇士进行了改造,将其定为“经天纬地”“守先待后”“谋王断国”之人。换言之,就是要求“官守职,士守道”。那么,士人如何守道?在钱谦益看来,就是必须保有“经学”。士人有经学,就好像耕夫“有畔”、织妇“有幅”一样。从良农“不失畔”, “红女不失幅”的道理出发,士人理应不失经学。唯有如此,方可回到“士之士恒为士”的老路上去。以“士服旧德”为基础,进而“工用高曾”,使“四民各得其所”,重新建立起“教化行而风俗美”的社会秩序。
在晚明礼教失范、秩序失衡的时代里,言论的重要性被上升到相当高的位置,其结果则造成以下两大结局:一是士大夫言论不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是直抒胸臆,张扬个性;二是士大夫敢于直言,甚至能做到犯颜直谏,并对君权形成一定的冲击。入清之后,士大夫为了适应社会秩序的重建,对晚明盛极一时的言论自由倾向多加匡正,使之回到传统的轨道上来。
与王阳明倡导重视匹夫匹妇之是非不同,到了清初,重新出现了一种重视君子之是非甚或圣人之是非的思潮。王夫之、魏禧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如王夫之认为,天下存在着“大公至正之是非”,尽管“匹夫匹妇”有时也能知道这种是非,而且圣人也不能违反。但从根本上说,“君子之是非”,终究不同于“匹夫匹妇”之是非,甚至不与匹夫匹妇“争鸣”。君子“以口说为名教”,所以君子的是非一出,“天下莫敢不服”。细究王夫之重新抬出“君子之是非”的本意,还是因为“流俗”之所是、所非,已经混淆了传统的是非观念,最终导致“恶不知惩”“善不加劝”的恶果。而一旦“君子之是非”得以确立,即可通过“明赫之威”“月旦之明”,重建“君子”言论在社会上的权威性。魏禧作有《平论》四篇,究其本意就是为了“平己之情以平人之情”。换言之,他欲将明末是非、好恶、毁誉、赏罚之混乱,重新加以清理,以定于“平”。然而,他所谓的“平”,决非是一种平等,而是通过“平情”的过程,使晚明以来社会的混乱现象重新趋于稳定。于是,他就不得不以圣人作为是非的标准。他认为,由于是非的混乱,必须“衷之以圣人之说”。在他心中,“圣人之说如权衡,物有大小轻重,以权衡之,各如其数而止”。这是重建圣人在社会上的权威。
与晚明重视个人言论的时代风气相较,清初士大夫开始对言论作了很好的反思,其反思的结果,就是反对“轻言”,倡导“不乱说”,借此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如王夫之说:“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他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要求替人谋国之人,即使有了“一罅之知”,也必须“慎密以俟之,毋轻于言”。与明代士大夫重视言官不同,清初的士大夫开始对言官的职责加以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反对台谏的言论,如杨彭龄,在追摘明代旧事时,谓“明末大臣畏台谏,台谏树朋党,终误社稷”。即为典型一例。另一方面,更是对设立专职的言官表示怀疑。如王夫之认为,在上古之时,人人得以向君主进谏,并没设立专职的言官,这是因为“不欲天下之以言为尚”。然而,王夫之所信奉的,则是《易经》中的说法,即“乱之所由生,则言语以为阶”,借此希望回复到原本言无专官的时代。
王夫之当然也肯定“公论”在朝政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认为公论应该是“朝廷之柄”,而不应由外臣掌握。从上面所说不难看出,王夫之就连外臣的议论都有所否定,更遑论在野士人的“清议”甚或党社“声气”了。所以,在对待党社结盟的态度上,王夫之也持反对的态度。这显然与其父王朝聘的影响有关。与此同时,陈确也在反思人们的言论,所以他将“不乱说”三字,提到相当高的层面,以便对士人有所约束。
元代儒家学者许衡提出学者以“治生为急”,此说在明代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以致有人肯定儒家学者以经商“治生”,最终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一至清初,治生之说开始进行了新的调整,以适应当时重建社会新秩序的需要,这就是将治生层面局限于以“稼穑”为先。面对晚明职业混淆的局面,清初学者张履祥重新对职业的高低进行了分别。其说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必须固守“恒业”,唯有恒业,才能使人有“恒心”;二是在恒业之中,也必须有所选择,只有“士农”二业才算正业,其他如商贾、工技、医卜之类,显然均为贱业。尤其不能堕入倡优下贱,以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之类。与晚明很多学者对大众的肯定与重视正好相反,王夫之将农民与商人均归入“小人”之列,称农民为小人中之“拙”者,而商人则为小人中之“巧”者。
(二)士大夫对明朝灭亡的反思
在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士大夫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反思的结果,显然对清初统治者建立新的礼教秩序大有裨益。
仔细考察清初士大夫总结明亡教训的论说,大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其一,从“天运”与“风俗”两个视角,对明朝灭亡加以总结。如钱谦益就认为,明朝的灭亡,完全是因为“天运”所致。他认为,自古以来,凡是国家大运不造,杀机将发,则必有忠臣志士适逢其会,刀轮飞空,热铁在颈,“犯阴阳之治,而入天地之笼,有不知其所由然者”。所有这些,固然不是人臣之罪,而亦非明主之过,但一旦出现如此状况,势必预示着一个朝廷行将衰亡。当然,世之治乱,除了取决于“天运”之外,其实还与“风俗”趋奢尤其是人心的“无厌”有关。在钱谦益看来,“世大治乱,必有蘖芽。乱生于争,争生于无厌”。在世俗追求奢侈的大势之下,其结果则是造成“豪者益奢,奢则思攘。贫者益匮,匮则思求。相寻相構,相煎相逼,不多不餍,出尔反尔,祸斯烈焉”。换言之,在追求须臾快乐的同时,已经埋伏下明朝灭亡的“阶厉”。
其二,从制度的层面,对明朝灭亡加以反思。在清初士大夫反思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有很多学者将矛头直指明朝文武关系的失衡。黄宗羲堪称其中的典型。考察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大抵体现了以下的趋势:明初重武轻文,明代中期以后,重文轻武,遂成一时风气。在重文轻武风气的笼罩下,固然亦有武将尚文及文人尚武风气的形成,但终究难以对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巨大的威慑。所以,当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矫枉过正,为了改变重文轻武的习气,特意重用武将。即使如此,明朝最终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当北京陷落以后,悠悠之口,无不认为这是因为明朝廷“不任武力所致”,但黄宗羲颇不以此说为然。他认为,崇祯皇帝所重用的武将,全都是“粗暴之徒”,导致“君死社稷,免胄入贼师者无一人焉,荷戈衷甲,反为贼用”。这不但不得专任武力之用,反成专任武力之过。究其原因,黄宗羲认为,“尚古兵柄,本出儒术”。换言之,真正的卿相之才,必须是“有事则显忠节,无事则显儒术”,如王阳明有将帅之才,却又能文。若是将“武夫”视为“武”,就好像将“场屋嵬琐之士”称为“文”一样,是一种“名实之乱”。
明亡之时,崇祯皇帝有一番推卸自己亡国之责的话,即“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这是一种自恕之词。对此,清人龚炜作了下面的驳斥。他认为,崇祯一朝,未尝没有仁贤之士,但崇祯帝信之不专,用之不久,反而“偾事之小人日益进”,国家最终灭亡。所以,崇祯帝之贤,仅仅在于能够做到“死社稷”。至于明朝之亡,则不得一概“诿罪于诸臣”。黄宗羲尽管对于崇祯帝能够“身死社稷”有所肯定,称其“一洗怀、愍、徽、钦之耻”, “亡国而不失其正”。然从历史的经验出发,黄宗羲还是认为,明朝灭亡具有偶然性。若是崇祯皇帝能够“避之南都”,迁都到南京,那么“天下事尚未去也”,尚可保有“江左”。
其三,对明末兴盛一时的党社“声气”加以反思,从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按照传统的见解,无不将国家乱亡相续的原因,归之于“小人”之“祸人国”。而小人之祸害人国,则以宦官、朋党为甚。这就是所谓的小人祸国论。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钱谦益是明末党社中人,入清以后,却对“党祸”之酝酿、发作乃至危害作了很好的反思。他认为,明代的党祸,酝酿日久,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而大作。当此之时,一二佥人,凭借闲曹冷局,衡操宫府之柄,“媒孽正人,剪除异己”。而那些号为“君子”之人,分清浊之流,争玄黄之战,迭胜迭负,“坚垒不相下”。时日一久,椓人当国,皇纲解纽,衣冠涂炭,廉耻陵夷。于是,元气伤残,兵燹交作,土崩瓦解,天下至于不可救药。在给吴伟业之书信中,钱谦益对君子之门户也多有反思。他将汉、宋两代士君子的门户进行适当的比较,认为汉亡宋弱的结局,主要还是因为士君子门户之见“持之太甚”的缘故,导致有心世道之人,“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谨”,实属事出有因。
清初对党社“声气”作理性反思者,尚有张履祥。尽管张履祥师事刘宗周,而宗周亦是明末党社中人,但张履祥对党社显然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说:“若近代贤流,高子(指高攀龙——引者)标许,以及党同伐异之习,平生窃所羞恶,而不敢出者也。”又说:“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张履祥对异端与声气二者之患加以比较,指出二者尤以声气之害为甚。他的立论依据是明季东南士风,“溺于异端者十犹一、二,溺于声气者恒八、九”。异端之惑,“多中老成深苦之士”,而声气之惑,则“凡聪明才隽、英少之子弟,皆驱而入其中矣。”所以,他主张不仅要辨异端之尚,更应驱除声气之病。
其四,对明代的学术尤其是道学进行反思,进而揭橥道学无用之说。这种反思始于钱谦益,至顾炎武、归庄、张履祥、魏禧等人,更是蔚成一时风气。
面对晚明学术之“魔外盛行,矫乱论议”,尤其是“佛法世谛,如金银铜铁,搅和一器”, 钱谦益想燃起三把大火,以烧尽晚明儒、佛、道三教中之异端邪说。钱氏所烧的第一把火,是“祖龙之火”,专门用来烧毁“儒林道学,剽贼无根”之说;第二把火,是“须弥之火”,专门用来烧毁释典中“文句语录,骈赘无根”之说;第三把火,是“丁甲之火”,专门用来烧毁道教中“经方符箓,诞谩无稽”之说。尽管钱谦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学术重新定于一统,即归于程朱,而是为了“孔自孔,老庄自老庄,禅自禅”,但这种颇具霸道意味的烧书之说,无疑与清初学术界趋于一统之风是桴鼓相应的。
顾炎武亦对明代学术进行了反思,批评的矛头直指道学,指斥道学之士“言心言性”,实属“空虚之学”; 归庄有一首《读书》诗,专门就明代学术作了总结,批评王氏后学的空虚无用,倡导读书人真正成为“有用”之人,去建立“格天功业”; 张履祥认为,天下多变的原因,无不源于“学术之不正”,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在当时已被学界“靡然向风”的王学及其后学,认为其导致的结果,则是“人心坏,学术害,横流所极,至于天地易位,生民涂炭,而未知其所止息”; 魏禧更是将“国家之败亡,风俗之偷,政事之乖,法度纪纲之坏乱”,一则归咎于“道学不明”,二则归咎于道学之士“迂疏狭隘”,“试于事百无一用”。
其五,对明代的“士气”进行反思,进而指出文人“习气”之危害。甲申年(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陷入李自成之手,消息传到江南,无不震惊。在震惊之余,一些人不免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士气”,并对士气做了总结。如归庄在诗中言:“媚似狐狸贪似狼,年来士气大堪伤!只今九庙成灰烬,可有南朝李侍郎?”又云:“书生闻变涕霑裳,狂悖人心不可量。青绶铜章□此日,吴歌楚舞醉霞觞。”矛头所指,就是“媚似狐狸”或“贪似狼”的士气。归庄的这种感叹,事实上也是有事实依据的。如北都沦陷之后,在江南官场却是一片莺歌燕舞。四月末,江南粮储道官署中,照例还是演戏。五月初一至端午,嘉定知县更是挟妖童娼妓观看赛龙舟之戏。
晋人之风流标致,在明代士人中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一至清初,就有学者对此深加贬斥。如张履祥说:“晋人风流,坐致中原陆沈。文士习气,可以败常乱俗,吾人当痛以为戒。”陈继儒作为一个山人,是晚明布衣文人的杰出代表,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被张履祥所瞧不起,称他为“近代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于末俗,故令得保首领以没,恶可容于尧、舜之世乎?”
(三)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明清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与之相应,揆诸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同样发生了诸多的转向,甚至出现了不小的波折。
1.重新确立儒学一统
在晚明时代,随着诸子学的缓慢复兴,申韩、黄老之学,其价值均得到了肯定,学术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入清之后,随着新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学重新趋于一统,诸子学随之多被排斥。
仔细考察传统中国政治的统治之术,尽管明为儒学,但正如明人熊开元所言,实际在治术上大多受到申商之说的影响,“或杂用申商,或专用申商,或学申商而不逮”。这是熊开元在隆武元年(1645)所上奏疏中所言。其实,早在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为了筹措军饷,对官场因循之习稍加综合,于是就遭到来自一批儒家学者的反对,请求行宽政,以致被崇祯皇帝斥责为“迂阔之谈谭”。在熊开元看来,这些迂阔儒臣之说,确实不是符合时事的“对症之药”。但并不能因此认定熊开元主张行综合的申商霸道,而是希望在综合之中,仍能保持一种儒家之“道”。他劝诫崇祯,在对待臣下之时,应该“惟辟作威有道焉。先其大,而后其小;详所重,而后略所轻;密于故,而疏于过”。若能如此,“虽疾风怒雷,时一震叠,贤人君子止觉其宽之可乐,而不见其严之可忧。故四体展舒,厥功自集”。从熊开元与崇祯帝的对话中不难发现,至明末之后,已经有人不满于王霸并用之说,进而对申韩之说加以审慎的质疑。
与晚明学术界重视诸子之说并主张王、霸并用不同,清初学者开始重新摒弃霸道,重视王道。于是,诸如像申商一类的学说,重又被置于排斥之列。这样的思想倒退,即使王夫之也很难幸免。如他说:“为君子儒者,亟于言治,而师申、商之说,束缚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诧曰:‘此先王经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汉、唐皆有之,而宋为甚。……圣王不作,而横议兴,取《诗》《书》《周礼》之文,断章以饰申、商之刻核,为君子儒者汨没不悟,哀我人斯,死于口给,亦惨矣哉!”显然,王夫之重新拾起了“君子儒”的大旗。但他所要恢复的君子儒,不是宋代以后所谓的“君子儒”,而是原始意义上真正以仁术治天下的君子儒。在王夫之看来,真正的君子儒,其言应该“蔼如也”,其政“油如也”。换言之,真正的儒家治术,理应是“建之为道术,推之为治法,内以求心,勿损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贼天下”。至于如老庄、申韩,无不都与儒家仁术相反。老庄是求合于仁心不得,则流于“诐”;而申韩则是“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者”。王夫之所最为担忧的是打着儒之大旗的杂术之儒,亦即以“圣人之道”文饰邪慝,诸如“老庄之儒”“浮屠之儒”“申韩之儒”。这就是说,王夫之的目的在于净化儒家阵营,以便能恢复原始意义上的“君子儒”。
申韩之说遭到批评,黄老之说在清初同样难以幸免。清初著名学者张履祥从汉文帝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人主学术不可不正”的结论。他立论的依据,当然是鉴于汉文帝采用黄老之术,并以“清净无事为道”。但张履祥对“无事”作了重新的解释:“夫所谓无事者,因乎事之所当然,不以私智扰之。如当刑则刑,当赏则赏,刑赏在物,而己不与也。推之因革损益,莫不皆然。非谓当为而概无之也。”这显然是对黄老治术的批评,甚至看到了黄老流而为申韩的危险性。
与晚明重视智慧甚至出现《智囊》一类的书籍不同,清初学者对“智”“术”开始加以反思,并且审慎地加以批评。王夫之重新对“智士”“智”加以定义,认为所谓的智士,“非乘人而斗其捷以幸胜之谓也”,而所谓的智,也不是“挟机取捷之术”,借此确立“小智”与“大智”之别。魏禧更是对“智”与“术”作了全面的反思,认为“凿智”之害,与阴贼险狠“同趣”。尽管魏禧不得不承认,人无智术,不可济世全身,但同时又严肃指出,智术之人,“最易堕入邪僻,反以杀身毒世”。“智术”二字,必须无愧“忠厚光明”四字。换言之,“术”尽管也有“不可少”之处,但属不得已而用,且有圣贤、奸雄之别:“专意利人而用,谓之圣贤;可不必用而用,专意利己而用,谓之奸雄。”张履祥也主张,“术不可不慎”。他认为,“凡不容于尧、舜之世者,在己不可为,在人亦不可与近”。
2.历史观的转向及其倒退
如果说晚明史学中“玩”的特点,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商业化乃至通俗化的思潮,那么自明季以后,一直到清初,随着经世思潮的崛起,在史学上也逐渐转向以史经世。如王夫之对史的意义作了下面的定义:“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以李贽、钟惺为杰出代表的晚明思想家的历史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出机杼,不以圣贤的是非为是非。这种历史观,显然承继了宋人苏洵之说。入清之后,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若与李贽、钟惺等人相较,其历史观反而出现了倒退。与李贽之称颂冯道不同,王夫之则对冯道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冯道是“鄙夫”,在国破君易之下,“贪生惜利禄,弗获已而数易其心”。王夫之在史论上,显然不满于李贽之说,对自宋人苏洵以至李贽的史观,大张挞伐,认为他们“奖权谋、堕信义”。他将李贽、钟惺等人的史论斥为“卑污之说”,造成“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甚至“逾于洪水、烈于猛兽”。
3.英雄、大众观念的逆转
与晚明士大夫的英雄崇拜不同,清初士大夫对英雄的认识开始有所倒退,进而以“君子之道”补充英雄在传统道德层面的不足。王夫之与史震林可谓士大夫英雄观转向的代表。譬如英雄大多具有诡谲鸷悍之才,在晚明时代,这种才能已经得到了士大夫的理性支持。但一至清初,王夫之将此类才能进行了两分:一类是“雄杰”,如曹操之流,虽怀不测之情,但还是可以用“名义”加以驾驭。如果有明主兴起,并加以有效的驾驭,那么这些人终究可以“功业立,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另一类则是“贪利乐祸不恤名义”之辈,如袁绍之类,很难加以驾驭。即使有明主兴,也“为彭越、卢芳以自罹于诛而已。不然,则乱天下以为人先驱,身殪家亡而国与俱敝”。换言之,王夫之对英雄之略,尽管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也仅仅限于“正用之”,这与他反对用“权谋”和“谲道”显然是一致的。他说:“士当逆乱垂亡忧危沓至之日,诡随则陷于恶,躁进则迷于所响,亦唯为其所可为,为其所得为;而定大谋、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节以不颠沛而逆行者亦在此。”这就是说,英雄之略,“君子有取”,但必须“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必须“正用之”,才可以使自己立于“天纲裂、地维坼”之日,而又内心没有愧疚。在此基础上,王夫之进而提出,英雄应尽“君子之道”,亦即在“尽己”之外,尚有“忧天下”之心。史震林在《西清三记》中,对豪侠与才子亦作了一番评述。他认为,豪侠之人令人可惜者有三:一是助“凶人”得暴名,二是挥泛财得败名,三是纳庸客得滥名。尽管对豪侠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但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有自己的见解。至于才子,则在他的笔下反而比“佞臣”还不如。他说,才子的罪孽甚至胜于佞臣。他说这番话的理由是,佞臣尽管误国害民,但所计不过数十年时间。而才子则不同,他们所写的淫书流传后世,“炽情欲,坏风俗,不可胜计”。这显然是一种传统卫道之说。
在晚明士大夫重视大众的时代潮流中,作为大众一员的“盗贼”,亦得到了谨慎而理性的肯定。一至清初,王夫之对“盗贼”的看法,既代表了他的一种政治倾向,也说明到了清初,士大夫精神史已经处于一种逆转的状态。王夫之首先认为,“盗不可轻用”,即使要用,亦必须有所辨析,即可以用一般之“盗”,不可用盗贼中的“渠帅”。
4.感伤主义精神蔚然成风
在明代的承平时期,士大夫相当风流,而一当明清之际两朝鼎革,这种风流已不复存在,使人不能不产生诸多的感慨。如黄宗羲以他的家乡浙江余姚为例,说明了社会由承平转向动荡之后士大夫生活的变化,即原本“当花对酒,登山临水”的风流生活,仅仅存在于梦境之中。陈舜系亦以家乡广东吴川为例,称其在万历末年时,“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显然对明代的生活多有留恋。
早在晚明,文人士大夫就已经具有一种幻灭感与末世意识。如洪应明云:“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悉属旧时争战之场。盛衰何常?强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只是入清以后,在经历了天崩地陷一幕之后的士大夫,其幻灭与感伤情绪,则更显突出。清初诗人吴伟业《琵琶行》一诗,细玩诗旨,其基调无疑带有感伤主义的色彩。这种感伤情绪的产生,来源于对过去的回忆,亦即旧时宫中生活的繁华,所羡慕的更是“前辈风流”。然入清之后,“升平乐事难重见”,也就难免“坐中有客泪如霰”与“偶逢丝竹便沾巾”了,“相与哽咽”,在所难免。
对于经历了明清之际两朝鼎革的文人士大夫来说,那些活下来的读书人,无不觉得这种“天崩地坼”的场景,恍惚做了一场梦。在如何看待这一梦景时,却各有自己的心思。如张岱作《西湖梦寻》一书,目睹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堙没,百不存一,至于西湖边上的诸多大家别墅、湖庄,更是仅存瓦砾。于是,就产生了“保吾梦中之西湖”的想法,犹如“梦中说梦,非魇即呓”。可见,张岱的宗旨是保留“旧梦”。
对于张岱如此沉溺于旧梦,清初也有部分士大夫并不首肯。如李长祥反对寻“旧梦”,主张寻“新梦”。当时杭州的道隐和尚,更是从佛教的观点对梦境加以阐述,认为国家的兴替,已是极其渺小之事,更何况西湖的兴衰。这是从佛经的出世思想出发,反对人们沉溺于寻找旧梦。查继佐则相对比较积极。他不主张生活在“旧梦”里,认为旧梦不过是“妖梦”,不必辗转反侧,在梦寐中求之。言外之意,他是劝张岱不必有负罪之感,躲进旧梦中不出,即使是恶人,经过了斋戒沐浴之后,尚可以事上帝,更何况是原本本色之人!诸如此类的见解,无不说明,在清初士大夫广泛盛行幻灭、负罪、感伤情绪的同时,正在别出一股寻找“新梦”的时代思潮,尽管不能遽断是为了迎合清初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在两者之间,应该桴鼓相应,不无因缘关系。
综上所述,借助于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剧,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进而形成巨大的“活力”与“多样化”的色彩。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社会秩序与礼教秩序的重建,尤其是统治者对旧朝士大夫力量的严厉打击,清初士大夫的精神史开始出现波折,甚至是倒退的转向。
清初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部分士大夫从制度与精神两大层面对明朝的灭亡加以反思与总结,进而提出了较为理性的看法,甚至将矛头直指传统的专制统治,属于积极的转向;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受制于新朝强权政治的威慑,只能留恋于过去,导致感伤主义精神流行一时,甚或为了顺应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主动提出传统、保守的看法,借此重新确立儒学一统。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