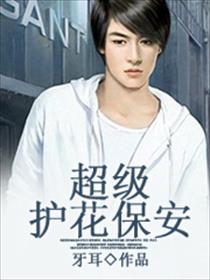§四
尽管我不答理他,眼皮不求他,最终他还是熬不住,不得不凑到我跟前来,主动搭话:
“他不能说话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我眼前堵上来一张青笋般又长又尖的脸,眼光尖厉,带着一股冷森森的仇恨。这种尖头顶的家伙不好斗。
“您是谁?我为什么要跟您说?”
我明知故问,打击一下他的气焰。
“我是赵旺达的儿子。”
“噢,怎么称呼您?”
“赵盛。”
“是您把赵旺达同志拉到这儿来的?”
“不错。我父亲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现在又身患重病,理应受到党和国家的照顾。可你们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他。我只好把他给你们送来了,你们要看得过去,就让他在这大树底下待着;看不过去就快点解决他的住房问题。”
“您把话说过了头就没有分量了,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会没有房子住?有人相信吗?据我所知,国家先后分给赵旺达同志三套房子,厨房阳台不算,一共七室三厅。这些房子都到哪儿去了?”
“这些房子已经归别人住了。”
“别人是谁?”
他不想说。当众被我问含糊了更暴露了他的色厉内荏。他不管多么恶狠狠,也是来求我办事,我怕什么?老干部局是国家机关,我是国家干部,说难听的咱们公事公办,说好听的咱们商量着办。穿鞋的还怕光脚的吗?何况我这个老干部局又不管房子……
既然他接不上话茬儿,我正好趁机来一段官腔,叫他也长长见识:
“政府决定成立老干部局,正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优越。西方一些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不要说普通老人,就是一些大人物退休后都得自食其力,或重操旧业,或另谋生路。美国不就号称是青年的天堂、中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场吗?尼克松从总统的位子上下来以后,曾一度陷入经济困境,连住院治病的钱都没有。我们的全国有九千多万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差不多是全国共产党员的两倍,很快就将进入国际规定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享受高工资、高福利,住房宽松一点儿是应该的。我的工作就是保证老干部的权益。作为老干部,都很清楚我们国家的家底儿,不愿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作为老干部的家属,难道不该理解老干部,替别人、替国家想想吗?”
“行啦,辛局长,用不着讲这些大道理。你叫我们为别人着想,那别人活着干什么?谁为我们着想?我们是老干部的家属,同样也是人,也有资格要求有个住的地方。那三套房子,我大哥住一套,我姐姐住一套,我住一套,有房本为证,那三套房子的使用权是我们,而不是我的父亲。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赵盛同志,您谈到法律,这太好了。子女把父母的房本改成自己的名字,这并不困难。如果较真儿的话,这种改动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是受到法律的追究,可就难说了。因为这房子不是你们家的私有财产,是国家根据老赵同志的需要分配给他居住的,按规定他本人无权转让,别人更无权侵占。这是第一……”
“老干部是有家的,不是光杆儿一个人。你说的这么好听,哪个老干部的房子儿女不能住?这是谁的规定?”
“第二,这么热的天,您把身有重病的老人赶出家,放在这样一个露天地儿,名为要找领导,实际上是拿自己的老人示众,让老人难堪,经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倘老赵同志有个一差两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要问你一个虐待老人罪!”
“那你们就去告吧,我等着!老干部有困难,你们迟迟不给解决,我们这是被逼无奈。与其活着受洋罪,还不如进监狱算了!我父亲生活不能自理,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天天在家里照顾他。想雇个人负责照顾他,又没有地方给保姆住。你们老干部局不是负责保护老干部的权益吗?要不就给解决一间房子,要不就负责照顾老干部。叫大伙儿说,这要求过分吗?”
他的心里有点虚。不管他嗓门多高,口气多硬,已经由攻变成守了。我要按自己的思路,把该讲的话讲完:
“第三,房子问题只有房管局能够处理。如果赵旺达同志住房确实有困难,我们可以帮着向房管局呼吁。但,这不能成为虐待老人的理由。这是两回事。采取闹事的办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许多别的问题。按国家规定,老干部如果没有直系亲属,一切都由老干部局负责到底。赵盛同志,您的父亲不属于这种情况。我把利害关系都跟您说清楚了,您应该赶快把赵旺达同志接回家去。然后,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否则,老赵同志在这儿出了什么事,那后果严重了,责任全由您负!”
我转身对围观者们说:
“本局的职工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外人请离开我们的院子,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把该说的话说完,不再看任何人,包括赵旺达,径直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舒眉跟在我屁股后面也走了进来,拿起暖瓶给我的茶杯里斟满水,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的亮光:
“太棒了!”
“什么太棒了?”
“你今天的表现,一百二十分!有理有利有节。”
她的口气,她的神态,她的眼光,使我感到一种新奇的兴奋和舒坦,还有一种紧张和不自然。借喝茶躲开了她的目光:
“你把他们都叫到会议室去,咱们商量一下。”
所谓“他们”,就是老干部局顶戗的那七八位大将。正像“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这就是我的阵容。
大家的精气神不错,感慨很多,议论风生,一改往日那种死眉塌眼、半醒半睡的样子。看来老干局需要隔三差五地发生点儿具有挑战意味的事端,会给老气横秋的工作激发出一股活力。
依照惯例,我出完题目以后就不再吭声,先让大家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现代社会,人人都有演说欲和表现欲。一个开明的领导,要给部下以当众演说的机会和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
说白了,我这个老干部局长不过是个“幼老园”主任,哄着老的玩儿好(老干部),还要哄着小的玩儿好(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只有极少数几个中年人)。
——这当官儿的儿女更不孝顺。把他爹折腾死,他每月不还少拿好几百块钱了吗?怎么就算不过这个账来呢!
——人到老了还得有个老伴儿,儿女靠不住。
——最好别活得太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太长了便无幸福可言。我活到六十岁就行。
——“老”与“朽”总是分不开的,世界上真正老而不朽的东西很少。当初赵旺达是有名的“铁嘴部长”,做起报告来如江河直泻。现在,别人说什么他都只能听着……
我听这些又挨边儿又不挨边儿的话倒觉得蛮有意思,可以知道每个人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朱材高爱充大尾巴鹰,捏出一派二局长的腔调截住了别人的话头:
“时候不早了,咱们说点儿真格的吧。刚才局长那一番话说得太厉害了,赵盛没有台阶下了。这大热的天,眼看就到中午了,那棵老杨树根本不遮凉。赵旺达万一一口气上不来,死在我们院子里,那就说不清楚了,会成为全市的头号新闻,我们也就被动了。我的意见不如先把他抬进传达室或楼下的某一间娱乐室,先救人要紧。局长,你说呢?”
怜悯唤起了他的善良意识。但这不是怜悯和善良所能解决得了的。好心人的错误,或者说人类的错误,就在于用己之心度人之心。朱材高担心的问题我也想过。但他是个笨蛋,怎么能让那样的局面出现呢!
我准备给这个碰头会作结论。不,是像一个警长那样给属下分派任务——
朱材高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决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赵旺达,我们不能动他,这是他儿子把他放在那儿的,出了问题由他儿子负责。我们一动他,容易被反咬一口;更不能把他抬进屋子,抬进去容易,再想抬出来就难了,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占一间房。
老朱,你到医务室叫上王大夫,负责在现场盯着。你可以动用自己的全部技巧,给赵盛以台阶下,让他尽快把他老子弄走。记住,不要真正的答应他什么,他在没有把他老子弄走之前什么事也不要答应他。在现在的这种情势下,拒绝比赞成需要更大的勇气。可以给老头儿打一把伞,叫食堂为他做点好饭。让王大夫跟医院联系好,如果到下午五点钟,赵盛还没有把他老子弄走的意思,就叫医院派救护车来。把赵旺达拉到医院去过夜,又安全,又可靠,出了任何事情也与我们无关。
舒眉,你去赵旺达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所,了解一下赵盛平时对待老人的态度,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做点工作。
陈湘,你去赵盛和他老婆的单位,叫他们出面,给赵盛压力。
刘明,你不是跟公安局和检察院很熟吗?去联系一下,赵盛如果蛮横到底,我们能不能起诉他?或者先传讯他、拘留他,吓唬吓唬他。在这方面你的点子比我多……
总之,我们四面包抄,他有炮(泡蘑菇),我们有枪(强制性措施),我就不信赵盛不快点把他老子再拉回家去!
我把任务大体分派完毕,心里立刻就轻松了,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大小是个头头的对自己的领导意识的满足。
我很清楚,自己在这种时候是最有风采、最富魅力的。直率、睿智、全面,水平高出别人一大截。我的眼睛可以毫不躲闪地坦诚锐利地盯视每一个人,跟他们进行深层的交流。他们也都望着我,被我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所吸引。
我是个以身作则的头头,不能光给别人分派任务,不给自己找点活儿干:
“我要立刻去找主管领导,然后找组织部、房管局,汇报、备案。该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再出了什么问题,责任就不在我们这里。大家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行!”
我知道,不可能不行。
今天这一早晨够可以的了……
1992年4月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