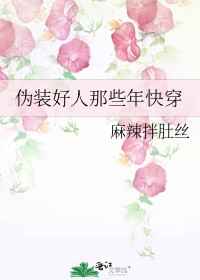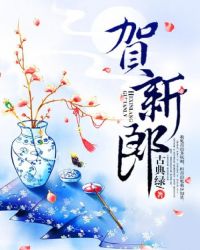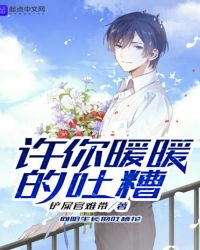§追踪任殷
《电影追踪》——读完这本书不能不承认:中国电影的确难逃任殷的追踪。敏锐地执着地追踪,既有热望,又有透彻地概括。
任殷——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被喜欢猜度的读者,甚至是一些电影界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男的”,而且是“老先生”。我为什么不跟踪一番任殷呢?
我被批评家批评得够多了。现在来评一评批评家颇觉惬意。何况电影是“全民的艺术”,凡看电影的人都可当它的“婆婆”,指手画脚一番,我又何必太谦?
严格地讲,我以作家的身份从未真正和电影打过交道。机会很多,都错过了。不是怕“触电”,是身不由己地被生活抛来抛去,唯独没有被抛到电影的飞船上。所谓属于我的轨迹给了我一种惯性,也可叫惰性。唯一的一次参加电影界的会议,认识了任殷,原来是位纤巧的女性。平时不声不响地坐在会务组工作人员的椅子上,有时则坐到主席的位子上,和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轮流主持会议,面对电影界、理论界和文学界的各路名家沉静自若,显得自我意识很强,有内涵丰富的气质。与其说靠她的机智还不如说靠她的这种气质,调度会场上几十种即使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也绝不能说是笨拙的大脑,和谐地奏出会议的主旋律。
这就是任殷“老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六年多以前的事了。
以后我看到了她批评根据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的文章——《乐曲在哪里交响?》(也收在这本书里),文字聪明而平静,娓娓道来,说理,很有耐性,决不偏颇,几乎没有丝毫感情色彩。却读得我透彻清凉。这个人太厉害,不好惹!
她的文章似乎让我明白了我的小说为什么不适宜改电影。虽然还有几部我的作品被搬上了屏幕,却永远忘不掉看完试片后自己的窘相,觉得对不起编导、导演,坑害了人家。我一向认为文学是电影的血液,电影无论怎样“电影化”,也不能化掉文学。我的小说却没有给电影提供应有的营养——任殷没有这样说,我知趣地想到了这一点。她的文章不能不叫人多想。
这类文章不过是任殷偶有所感,信手拈来的。她真正下力量“追踪”,不惜动用自己丰厚的心理资源来关注乃至为之呼号奔走的,是中国的电影剧作。只要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便一目了然,从《1977—1980:现实主义的恢复和探索》到《1986:平年掠影》,其间经历了一九八二年的“注目当代生活”,一九八三年的“重要的是写人”,一九八四年的“渴求新意”,一九八五年的“步履艰难”——这是作者紧追不舍式地评述,也是十年电影文学脚步的客观记录和总结。
人们都知道,电影艺术的上帝是导演,演员也可成为令人宠爱的天使。不知为什么没人注意写剧本的人,除非影片失败了,大家都会公认首先是剧本不好,影片获得了成功又似乎跟剧本关系不大,尽管每部影片都把编剧的名字摆在醒目的位置。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刚学着舞文弄墨,读的电影剧本比看的电影多,有时读剧本更觉“过瘾”,有一种在电影院所得不到的享受。当然在电影院所得到的也非读剧本的感受所能替代。当时一些电影剧作家的名字在群众中十分响亮,如:王愿坚,梁信,陆柱国等。“文革”后的最初几年也还是如此,白桦、叶楠两兄弟不是靠写电影使其声名再震的吗?
渐渐地电影文学和电影艺术拉开了距离。当任殷发出忧虑的感叹:电影文学的创作又是一个平年,电影却丰收了。电影文学“步履艰难”的时候电影已开始“腾飞”。电影文学还在“渴求新意”,一批探索性影片已经快被自己开掘出来的新意淹死了!就我自己来说,每年总要进几次电影院,电影剧本却是不读了。
是电影出了毛病,还是电影文学出了毛病?我以为很难责怪电影,落伍的只能是电影文学。这跟整个的当代文学现状有关。当文学陷入一种自作多情、顾影自怜的尴尬境地时,中国电影不是已经在开始获得世界级的声誉吗?不能说这种声誉是由于文学的落伍造就的。一种辉煌的文学可以使这荣誉更辉煌,倒是无疑的。
唯其如此,任殷把一个批评家的才智集中用来研究被电影和观众以及评论界疏远冷淡了的电影文学。她有最便利的条件去锦上添花,却宁愿雪里送炭,不失为一件功德,令人起敬。
任殷的这一组分量不轻的论文,虽然仍保留着她文章的一贯特色:章法严谨,旁引博证不杂芜,含蓄蕴藉。但失去了超然的心态,文字间藏着隐隐忧虑,不再一味地温柔敦厚。她在《电影剧作的困窘》里说:“创作走入了一个平板的缺乏足够生气的境地,好像是在进行机械化的运转”,“纷纭复杂、多彩多姿、深不可测的大千世界,往往在电影剧本里被条理成类型化、规格化。创作岂不是走到了套子里?不管什么题材,都会像很有经验的匠人一样早已有驾轻就熟的路数和模子”。岂止是电影剧作如此!不是由成熟走向深刻、恢宏、伟大,而是由圆熟走向油滑,玩儿——玩儿一切,包括自己。她还认为编剧的功力、艺术技巧跟不上影片拍摄形势的需要,这也是剧作落后于电影的一个原因。
任殷是站在电影的角度重视和鼓励电影文学的。实际是以电影批评家的眼光裁判和选择文学。我听说——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感觉,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有两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电影文学是文学不是电影。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后的电影史将是电影剧本的历史。
我读《电影追踪》的感觉,任殷显然不赞成第一种意见。可也看不出她明确地充满信心地认为第二种意见能成为现实。这不单单取决于电影和电影文学本身,还要受整个中国人文环境的影响。
我以为目前中国的电影比文学更有爆发力和冲击力。电影剧本离开电影一筹莫展,所谓“一剧之本”,无“剧”也无所谓“本”。而影片,则对各种文化都有强大的吸收力,甚至有股霸气,夺取各种文化的营养,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本应文学给予电影,现在却是电影给予文学——电影走红可使原小说大噪。这无可厚非。
任殷的才华不在于评判是非,而是表现在对电影剧本的创作能作出深刻的概括,显出自己独特的力量和气质。她不是“造句运动”中的时髦人物,她的语言的培养液是思想,表达平实而精当。才华表现出激情,激情又燃烧了她的才华。真诚的心灵使这本书既清新又可贵,也引起读者心灵的振荡。
批评家居然也有如此激情——看来我太不了解批评家了。
她读过成百上千的剧本,好读的,不好读的。也可一连几天看电影,好的,坏的,看得下去的,看不下去的。真够苦的!看自己想看的电影做为消遣,是乐事。做为工作整天看电影,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从来不硬看看不下去的东西。所以我不能积累学问,当不了批评家。
可惜,好剧本就是那么几个,任殷翻来覆去,无论怎样变换角度,谈的还是那几个。没有好的对象,纵使她身手不凡,“追踪”也难。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还是有一些幸运的电影剧作家获得了任殷的赞赏。他们是鲁彦周、张弦和张子良。
当影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引起人们的惊叹和议论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时候,编剧张子良却“默默地躲在角落里,并没有引起行家和观众的注意”,她为此感到不公。当《天云山传奇》在第一届中国金鸡奖上“连获四项最佳”,却没有让鲁彦周获得编剧奖,她又为编剧感到不平。导演个人的光彩,在影片成功以后不是发挥而是遮住了剧本的光彩。
任殷要评价他们的电影创作,却要读完他们包括大量小说在内的全部作品,研究他们的整个创作道路,把他们的剧本创作放在中国电影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认真、严肃而有特点。文章也充满智慧和感情。且看她怎样分析张弦:“在女性的命运轮回中寻找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真是精辟!张弦笔下没有一个成功的男人形象,似乎专攻女人就没有笔墨再去了解男人。只写好女人一样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写不好女人却难以成为了不起的作家。她分析鲁彦周的一段话,我相信让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作家都会有相同的感触:“创作冲动既发源于生活实际,又往往拘囿政治的要求。他无形中屈从于某些外加的思想规范,有意无意地压抑着自身情感的和理性的认识。”只有挣脱这种“拘囿”和“压抑”,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有个性的作家。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走过来的作家,大多都经历了这样的“挣脱”。挣不脱这种“拘囿”和“压抑”的则难以再从事创作。
剧作家隐身在电影的后面,任殷又隐身在剧作家的后面。她是个谦虚的批评家。更没有人注意她,默默地做着艰苦的却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当我对她进行了一番“追踪”,准备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却感到自己像童话中的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无从下嘴,又不敢轻易动步,怕碰碎了一店精美的瓷器。只能小心地嗅嗅鼻子,捕捉一点味道。
从外表看,《电影追踪》不是一片很大的堂皇得吓人的店铺。任殷有条件给自己盖一座那样的殿堂。她很勤苦,文章发表了不少,谁都知道现在出一本书不太容易,难得出版社的编辑找上门来,趁机兼收并蓄弄它大大厚厚的一本,也不为过。任殷偏不,挑挑拣拣,宁要少而专,不要多而杂,编成了这本不厚大却精致好读的书。可见她的老实和严谨。出版界没有忘记像她这样辛辛苦苦作学问的人,读者也不会忘记她。
但愿我们这个充斥着铅字和油墨污染的世界,多一点学问。
1988年9月11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