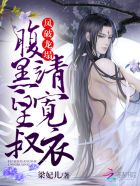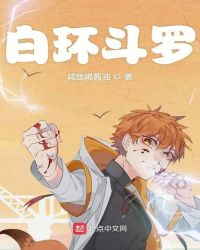§评《鼠精》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领导同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干净的写字台,漂亮的大沙发,让人感到宽松、和谐、舒畅。唯一令人不解的是浅绿色的地毯上撒着星星点点的黑色颗粒,甚为不雅。一问才知是耗子屎。
我顿时联想浮动,可以写一篇小说。耗子成精,居然打进领导的办公室,对我们领导人的精神构成威胁。它们见领导比我们还容易。不久,看到了李玉林的中篇小说《鼠精》。这个“点子”令我叫绝。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老鼠排着队大摇大摆地行进在堆放糕点的货架上,什么大八件、小八件、绿豆糕、核桃酥等根本不在话下,鼻不嗅、眼不瞅。只有碰上无比松软的蛋糕才肯降尊纡贵地饱餐一顿。女售货员们躲在远处,扬起玉手轻轻地吆喝着:“去,去!”
老鼠不理睬,傲气凌人。
人怕老鼠。人吃老鼠吃剩下的。
老鼠磨牙咬断了电线,乐声戛然而止,在黑暗中现代舞会上的现代青年陷入一片充满现代意识的混乱之中,老鼠未尝不是成全了他们。
老鼠叼来大块巧克力,剥开锡纸送到猫的嘴里,大拍猫老爷的“马屁”。当猫被打死以后,它们则一拥而上,食其肉、喝其血!
不管耗子闹腾得多凶,人们泰然处之,甚至大沾耗子的光。耗子身上有一种寄生虫,爬到人的身上也会叮出红疙瘩奇痒难挨,便可歇病假。售货员们轮流歇班,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天半月,乐得轻闲。
耗子每天都损耗大量的东西,到底损耗多少,无法统计。因为谁也不知道耗子究竟有多少。两条腿的人便以耗子的名义大吃店里的东西,还可以像耗子搬家一样把店里的东西拿走。
当来了个党支部书记不干“正事”,专门打耗子的时候,遭到了上下一致的抵制和嘲笑。连顾客听说他打死了许多耗子都不到这个店里来买东西了……
荒诞吗?是的。然而又具有生活的可信性。
可信吗?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又是真实的。
超现实来自现实,荒诞不经正好反映了曲折复杂的真正生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客观事物的非理性、混乱性,在小说中有相当精彩的刻画。有时看得人毛骨悚然,仿佛自己身上也爬满了老鼠身上的那种寄生虫。
《鼠精》的象征力量在于此。
对李玉林来说,这是一部快“成精”的作品。
他以独有的怪诞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对生活的感知丰富而多彩,不再满足于低层次地描述现实,不再将笔墨囿于就事论事的格局。
他开始艺术地掌握世界了。
李玉林用了大半年的业余时间经营《鼠精》,数易其稿,终于跨出了这一步,拓宽了自己的文学天地,可喜可贺!
细读《鼠精》,研究李玉林在创作上如何迈步以及迈出的这一步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感到很有兴味。我建议许多处于“创作苦恼”中的业余作者都来思索一下这个问题,也许会受到某些启示。
李玉林怎样变、变了哪些呢?
最首要的我以为是他改变或叫加强自己的文学意识。
从《鼠精》选材的角度、结构的方法、语言的运用都跟李玉林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他开始注重发掘自己的想象,认识和调动自身意识的丰富性。只有作者自己的意识感知丰富了,才能认识生活的丰富性,笔下的现实才不会单调,不至于光是编故事,写简单的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
有人不是老爱说提高呀,突破呀,变化呀,对李玉林来说《鼠精》就是提高,就是突破,就是变化。他反映出了生活的丰富感和变化感。
他的一个突出技巧就是跟踪宗义(小说的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时而直视内心,时而剥开人物潜意识的真实。有时只是表达一种感悟,一种情绪,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宗义这个人物不再那么简单了。他在跟耗子的战斗中(几乎是一种决斗),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别人,别人却不认得他了。读者则看到了人的本质。
作者对宗义这个人物的夸张和变形,实际是对艺术变形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不仅没有把人物简单化和漫画化,反而使人物显得深刻复杂了。
可以说,这部“内向化”的小说是由宗义这个“内省型”的人物支撑起来的。
《鼠精》的结构实际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依据,靠联想联系情节,组成的故事。
作者有意追求象征意味,把感官的、梦幻的、潜意识的东西错综交叉在一起,既梦又实,实而似梦。这一切看上去荒诞,实际效果却达到了更深刻的真实。
抓住幻觉、错觉与现实的交叉点,不是轻视现实,而是重视它。想想吧,人鼠大战,有时人胜鼠死,有时鼠胜人败。打了四条腿的老鼠,触怒了两条腿的“老鼠”,群起而攻之,群鼠而攻之。人物陷在老鼠的包围和同事的包围之中,为作者、为人物提供了多么美妙而又广阔的心理空间!想象可任意驰骋。行动、对话、独白、描述;想象、梦境、幻觉、潜意识,一个接一个的心理层面让人震惊,发人深思。无法不感到新颖和深刻。
混乱而莫名其妙的环境,正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象征。社会的某些荒诞应该是人的世界的变形,是现代人心性的变形。怪诞是人的精神产物。李玉林小说里的荒诞意识来自真实的荒诞,来自对实实在在的中国某些荒诞的独特感受。不是作荒诞状,不是从外国著作中演绎来的。
文学的灵魂找到了自己的肉体。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增强了。也毋庸讳言,作者想起了一个“一流的点子”,抓住了一个“一流的题材”,也给自己出了个很好的大难题。尽管付出了相当艰苦的努力,仍看得出他驾驭自己的灵魂和材料相当吃力,似有些力不从心。
《鼠精》应该成为精品、妙品,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可现在还有些地方让人感到仅仅是个半成品,语言是很大变化,但也有半生不熟、疙疙瘩瘩的句子,所以我说它还没有完全“成精”。
李玉林要想“成精”,是非得经过这一步不可的。有了这重要的第二步,还愁迈不出第三步、第四步吗?《鼠精》发表后反响不错。《小说月报》等报刊转载(被这些选精拔萃的刊物转载似乎也说明一种规格),《天津文学》编辑部为这部小说召开讨论会,天津文学界的名公巨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过去对李玉林来说如在云彩眼儿里的文坛,不知怎么一抬腿就上去了,转眼间毫无准备地就成了颇负声誉的“文学新星”。《文艺报》曾约我写一篇介绍李玉林的文章。李玉林对我说:“你这一写,我今后若写不出东西来怎么办?”“今后你写得出写不出,与我的文章何干?你怀疑自己吗?”我们两个都有点“受宠若惊”。他很年轻,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倘有一股现代的狂劲:“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介绍我?三山五岳让开,我来了!”——也无可厚非。
李玉林很实在:“我自知在创作上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也不会专门吃这碗饭。只想尽量写得好一点,能不断有所长进。”
从一九七九年至今,他已经发表了近五十篇作品,有短篇、中篇,在本市也拿过几个优秀作品奖。说有影响吧,不太大;说没有影响吧,又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写不出东西来。他总是一股劲,从表面看他不是那种对写作感到很困难的人,但也不是一挥而就,下笔灿然的才子型人物。据说《鼠精》改了五六遍,老改老有热情,不厌烦、不放弃,有股蔫劲——这一点很难得。每一次见面,只要我问起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总会告诉我刚写完两个或三个短篇小说。要写的东西有的是,小说题目有的是,好像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两三个。最近他又要发表两个短篇小说,一个叫《厦下三题》,他自我感觉比《鼠精》要好得多。用现代技法写城市的拥挤,一老人过不去马路,感到大街上都是眼睛,高空、中空、低空,眼珠碰眼球;另一篇叫《半个月亮,半个太阳》。每个人都有一个月亮、一个太阳,唯独每天半夜上班的扫路工人,只有半个月亮、半个太阳,还常常把月亮当太阳,把太阳当月亮。长年累月地上“鬼班”,搞得生物钟紊乱,夫妻生活不协调,即使白头偕老也只等于“半世夫妻”,是守在眼前的两地分居……
李玉林的小说总有一种现实的品格,给人的感觉扎实而厚重,丰富而新鲜。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以不太有规律的,像现实一般自然而平淡的形态呈现给读者。难得有空洞无物的新奇玩意儿,更少夸夸其谈。他似乎相信只有到生活里才能找到艺术,就像鱼只有到水里才能获得自由的生命一样。现实生活是他创作灵感的培养液。
他的根茎牢靠,茫茫人海中有一块属于他独有的王国:饮食行业、服务行业(浴池、修配等)、糖果、环境卫生、房地产、街道工作等等,他熟得几乎不能再熟了。
他创作的契机——直觉和经验。直觉成了他灵感的呼声,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使他敏感、多思。有人说:“创作不是一种爱好,也不是一种激情,创作就是作家本人。”关于李玉林本人,三句两句可真说不清楚。
“业余作者”处理好“业”跟“余”的关系不容易。有了点名气之后往往跟本单位的关系不够和谐。李玉林在区委的人缘儿却很好。有了升官的机会,让;长工资,让。他不是傻子,吃一点小亏买个清静,买个心情舒畅。这些年来,他没请过一天创作假,工作只有多干,决不比别人少干。上上下下都承认他能干,且没有是非,为人厚道,不出风头。他什么时候读书写作呢?一天三顿饭都在机关吃,每天晚上在办公室干到九点多钟才回家……
除去有个美满的后院,他还有一副令人羡慕的好体魄,这是他长时期坚持“革命加拼命”的本钱。李玉林从十岁起跟着名师学摔跤,可谓科班出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会摔跤、能捣皮拳。他个子不高,文质彬彬,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个赳赳武夫。他稳重敦厚,脾气随和,入党时最大的缺点是“斗争性不强”。每逢参加文艺界的会议,听着别的年轻作家那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的滔滔宏论,李玉林就傻了,连插嘴的份儿都没有,觉得自己还是去摔跤更合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坚持着走自己的道路。有的人喜欢在引人注目的海滩弄潮玩水,身后留下清晰的脚印,潮水一过,踪迹皆无。有的人则在平地上踩出脚印。
借李玉林的第一本小说集即将问世的机会,我把过去介绍李玉林的两篇短文捏在一起,权充作序。
1988年9月28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