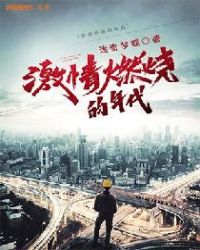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激情燃烧的年代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小时后,姚清明一家全来了,老远看见姚清远那个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样子,料想他在外面一定混得不错。
“哎呀,清远,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了,我与你哥觉得你肯定不会回来了!今日一见,想必兄弟发了大财,荣归故里啦!”李翠莲仍然还是那样心直嘴快。
“翠莲嫂子,快别那么说,一个臭打工的,哪里谈得上荣归故里?”
姚清明一见,急忙催着身旁的姚动生招呼人:“动生娃,这是你堂叔清远,快叫呀。”
姚动生有些羞涩地叫了声:“堂叔。”然后就跑开了。姚清远眼泪顿时流了下来,觉得才十来年的功夫,从小一块儿玩的动生娃,虽说快长成大小伙子了,但怎么跟自己还生份起来了呢。
左右的邻居们听说姚清远回来了,也都纷纷来看看姚清远,人们都认为他混成大款衣锦还乡,看他衣着时髦,高档大气,都在姚云轩和洪杏花面前极力夸赞姚清远有出息。
晚上,姚清远留姚动生一家吃晚饭,吩咐洪杏花弄几个凉菜下酒。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着各自的见闻。姚清远聊城市这几年的大变化,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涌出,宽阔的街道,八车道的大马路,还有花园一般的绿化带。其他人也聊过完年准备也去大城市打工,说现在村里人没有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更没有几个年轻人会种田,老年人种不了那么多田地,只好在田里种树,说这样十几年之后树也能卖钱。
然后,聊着聊着就聊到给姚动生买房娶媳妇儿的事儿上来,姚清明这才开口向姚清远借一部分钱。姚清远问姚清明:“干吗要在镇上买房呢?在村里不是挺好吗?有田有地青山绿水,养几只鸡鸭,自己种点菜园,不是挺好的神仙日子吗?你知道很多城市人过些年还都想搬回农村来住呢。”
姚清明回答他:“远弟呀!那是城里的有钱人过的生活,他们回农村是养老,种一点菜园,住两间小屋,到月有退休金,想买什么买什么,不足靠种田耕地生活,旱涝保收,当然轻松惬意。我们农村人就不一样,没有经济来源,都指望种田地挣钱生活,多累多辛苦,夏天毒太阳晒得满头大汗还要在田里干活,地里刚刚拔完草下一场雨草又疯长。我们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两者的出发点和世界观都不一样。”
李翠莲也说:“这还不算,农村交通也不发达,即使农作物丰收了,农产品堆积如山,介于都是土路,一下雨地上就起泥宁不堪,而城市却是宽阔的水泥路。在农村就是死马一匹,没有就业机会,在城市或者镇上好歹还能找个超市上班,哪怕赚个零花钱,也比种田来得快当啊。况且,城里的小孩教育和医疗水平都比农村要好,两相比较谁还愿意呆在农村呢?”
姚清远大大咧咧地调侃道:“我记得当年嫂子下乡时还高呼口号:‘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怎么?现在热情消褪没啦?”
“你还在拿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事儿取乐啊?现在都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你还翻老黄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莫要在我们面前唱什么高调哈!”李翠莲嗔怪道。
“嘿嘿,开句玩笑,嫂子别介意。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养鸡场,或者做生态农业,比如观光旅游、农夫市集什么的。”
李翠莲一听,撇了撇嘴说道:“我大姨姐家就是开养鸡场的,稻谷一块三一斤,鸡蛋才三元钱一斤,赔本赔得着急上火,血压居高不下,再也别提养鸡了。然而,你说的搞观光农业,这不纯属痴人说梦么?从镇上到咱生产队里十多里泥巴路谁来修?难道要让人家城市人开车趟泥泞到这儿来观光旅游?恐怕洗车钱比买农产品的钱还多!”
姚清远又调侃地说道:“要想富,就得先修路,不修路,什么也发展不起来,可以说服生产队里的社员们集集资修建,毕竞路修通了,于各家各户均有好处,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姚云轩在一旁听得不耐烦:“你说好轻巧!你去队里各户收收钱试试,看能有几个人出钱修路的?都巴不得国家和政府出钱修好他们免费使用,哪有人响应你的?尽说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等我哪天回乡来,我就自己出资修路,等路一修好,就在两头设关卡收费,谁家想从路上通车,就得向我交钱!”
“清远,别扯那些没用的!你以为自已是山大王?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哈哈,你真是异想天开!且不说你收不收得着路费,恐怕你这条路还未必修得通,即使你免费为村里人修路,有的人家还未必领你的情,比如,修路时通过人家庄稼地或自留地时,人家不愿让你通过咋办?就像电视报道的那个‘钉子户’,就是不让你通过他家地方,你也无可奈何,还想收费?门儿都没有!”
“照你们这么一说,我要回乡来创业就一事无成了?原本打算要在镇上开办一家养老助残综合服务企业,在镇上建一个大院子,把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接来。。。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服务。。。”
姚清远还没说完,就遭到一家人的反对:“你那高调真是越唱越高啦?!政府办养老院还都办不下去呢?你还有那闲钱去填那个无底洞?你若真是有钱,不如在咱们市里搞房地产开发,再不济也在镇上开发地产卖房,届时我们大伙儿也买点便宜房呀,也比搞那个养老院强!再说那个养老院,咱保石镇合并之前,水井乡那个养老院不是也开不下去了么?光是老人们生病了的医药费就不好办?你能给他们看得起病吗?手上的钱花完了,没有吃的把他们饿死了怎么办?没有经济来源不能持续下去,养老机构用什么生存?”
姚云轩撇了撇嘴说道:“光有一腔热忱是不够的,你得考察一下投资环境和官风民情,记得前几年一位张姓香肠厂老板,带着一百多万回到家乡想投资干一番事业,刚一动工,乡里、村里来了一帮子收费的,用张老板的话说‘一圈伸手要钱的,’,今天不是请这个部门吃饭,就是明天请那个管事的喝酒,不到一年,事业没有创起来,一百多万花光了,第二年张老板只好带着行李出门做生意去了。
从那以后,人们都知道这个前车之鉴,发财的老板们都不回来投资建厂了。就连考上大学的人们都愿留在城市,而不是回乡创业,毕竟城市就业机会多,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回乡能干什么呢?拼命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跳出龙门吗? 现在老家农村都是这种现象,在外发了财的村民不会回到家乡投资建设的。”
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姚清远想想,也确实解决不了经费的问题,于是,他只好选择沉默。到了晚上十点钟,大伙儿也聊的差不多了,姚清明一家便告辞开着农用三轮车回家去了。
洪杏花收拾完厨房里灶头上那些活儿,见姚清远躺在堂屋的椅子上,就上前问:“你喝不喝茶?我给你泡一杯去?”
洪杏花跟在姚清远后面问了两三遍,姚清远也不回答,直到在东屋的炕沿上坐下了才说:“不喝。”
洪杏花又说:“那我给你倒水洗脚吧,烫烫脚解解乏。”姚清远也没有做声。洪杏花赶紧去厨房打来一盆洗脚水放在他脚下。见姚清远仍没有要洗脚的意思,她蹲下身子把丈夫的鞋袜脱掉,将两只脚按到水里,之后去铺床。洪杏花一边铺床一边关切地问这问那,姚清远两只脚在水盆里揉蹭着,简短地做着回答。
姚清远洗完脚,洪杏花敏捷地下地去给他拿来擦脚布,转身端走洗脚盆去厨房将水倒掉。做这些事的时候,洪杏花有意无意地看姚清远,见丈夫两眼仍直视着自己,娇羞爬到脸上,两眼水汪汪地充满温情,迎着他的目光走到近前,双手揽住姚清远的脖子说:“还不睡吗?这么长时间了,我可想你了!”
洪杏花说着,便去解他的衣扣。大概是感受到妻子的体温,刺激着肾上腺分泌出的荷尔蒙发挥了作用,逼迫着姚清远按熄了灯。
第二天姚清远醒来时天已大亮,“啊。。。”他双臂上举,十指相扣手掌外翻,使劲抻了个懒腰,在厨房里做活的洪杏花闻声快步走到他面前,弯腰低头双臂撑在床沿上,四目相对,柔声问:“醒了?睡好了?”
姚清远情不自禁伸出双臂揽住了媳妇的脖子,说:“好了!”
洪杏花问:“什么时候吃早饭?我已经做好了。”
姚清远肉麻地说:“亲一个,亲一个就起来。”
洪杏花顺从地在他额上亲了一下,姚清远又说:“不对,亲错了,再补一个!”
洪杏花双目含笑,慢慢地将嘴唇贴在丈夫的嘴唇上,姚清远双臂用力把她的脖子揽得更紧了。一会儿洪杏花挣脱开,说:“内衣内裤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被窝里焐着呢,都换了吧,一会儿我好全部都洗了。毛裤也找出来了,在褥子下焐着呢,穿上吧,别着凉了,咱这不比北方有暖气!”
姚清远说:“内衣换了没两天,就不换吧?”
洪杏花说:“换了!换了!回来得有个新鲜样,也好一块儿洗。”
姚清远听了媳妇的话开始换衣服起床,洪杏花立刻去厨房端饭菜上餐桌去了。
姚清远家在村子的西南角上,一溜三间,砖瓦结构,高台基高房架,四周套着院墙,绿漆皮的大门开在南墙的正中间,院墙外是开阔的田地,可以看得很远。一出房门,姚清远的双眼被雪地上反射的阳光刺得睁不开,他觑眯起眼睛走下台阶。
出了大门向东走出院子就是南北向的小泥路,地上的泥泞被人踩出深深的脚印,在寒冷的夜冻得坚硬结实,走上去很搁脚,一路上沆沆洼洼的。姚清远有些不适应,小步出溜着沿泥路向北走。路上遇到些乡亲,叔长哥短地打着招呼。
路过柳梦华家的小卖部兼麻将馆时,姚清远下意识地摸了摸衣兜,早上刚换的衣服没有带烟,便折进小卖店。老家人有猫冬的习惯,这时节的小卖店是人最多最杂是非最多的地方,无事可做的人们,不分男女聚在这里打牌、赌小钱,东家长,西家短地把闲话当作新闻传播着。
在店里看柜的是柳梦华的媳妇,一见姚清远进门就笑着打招呼:“哦,清远,啥时候回来的?”
“昨天。”姚清远回答说:“嫂子,给我拿盒烟,再拿一个打火机。今天刚换的衣服忘带钱了,先记上啊,晌午时给你送钱来。”
这时店里已经聚集了些人,有玩牌的,有看玩牌的,厚道的人问些家长里短,也有尖酸刻薄的人,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柳大壮的个子大,嗓门儿粗,撇着眼睛说:“什么带钱不带钱的,言语一声就有人上赶着给还了!”
杨青山长得瘦,见姚清远没带帽子,尖声尖气地说:“行啊,越混越精神,要是戴个小军帽(暗含绿帽的意思)就更精神了!”
随着杨青山话音落下,牌桌上便有些人跟着吃吃地偷笑。姚清远笑呵呵地作答:“青山叔,天不太冷,不用戴帽子。”
柳梦华媳妇儿急忙把话岔开:“是去看我公公的吧?”
姚清远回答:“嗯。”
柳梦华媳妇说:“快去吧,这一走就快十年了,我公公说不定都不认得你了!”
“嗯,嗯。”姚清远答应着出了小卖店,咂吧着柳大壮和杨青山的话,总觉着有不对味的地方。
姚清远一走,柳梦华媳妇指着杨青山说:“你妈逼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这种事儿也到处张扬,就不怕乱子闹大了?就你龟儿子嘴快!”
杨青山咧了咧嘴说道:“我可不象你说的那样坏,这事儿他早晚都得知道,我这是先给他打个预防针,也是为他好!”屋里的人就着这个话头,又嘁咕喳咕地议论起来了。
为了得到村中年轻人的积极响应,姚清远准备出面找柳下会谈,以他的影响力号召大伙儿勇跃加入自己的建筑劳务队伍。柳下会的院子很显眼,属于那种时髦的高地基红砖墙瓦房。柳下会家的庭院规划的很齐整,四周是红砖砌的院墙,朝南开的大门紧靠着西院墙,门垛上贴着大红的对联。院里有一道纵向的花墙,南起大门口东门垛,向北延伸至房前三米左右的地方呈直角东折,与东院墙相衔接。
被花墙包围的是菜园,东西向花墙外是与之平行的花池,池中立着几株干枯的花枝。在西院墙与纵向花墙之间是红砖铺砌的甬道,甬道上方罩着镀锌铁管焊接的拱形葡萄架,葡萄秧被拉下来埋在土里过冬,拱架上残存着葡萄的卷须。观形知景,可以想见赏夜晚的星空,纳夏凉,品秋果的惬意,柳下会夫妇确是会享受生活的人。
房檐以下水泥罩面,房顶上挂紫色釉面瓦,前墙外镶乳白色瓷砖,双层的铝合金窗户。姚清远顺着台阶上了晾台,他以为柳下会以老规矩住在东屋,透过玻璃看到那两间屋子空着,屋内存放着粮食杂物,四周的墙壁上连底灰也没有打。
“老支书在家吗?”姚清远在屋外台阶上轻轻问道。
“在。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用猜,那一定是柳支书的妻子王大娘。
顷刻间,柳下会立在大门框上仔细打量来人。柳下会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头了,个子不高,短腿,圆方脸,面皮白晰,眼睛细长,前额上的头发稀疏,向后梳着。他当过二十多年的村支书,他文化程度不高,中学未读完就辍学了,但他酷爱读书,而且涉猎范围既宽且泛,不分文学、经济、军事、政治,也不分好书、坏书,实在无书可读时,连儿童画册也不放过。新书一到手,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点灯熬夜也要一气读完,否则食不甘味,寝不安眠,为这没少耽误活儿,也没少挨他老伴儿骂。
姚清远张口喊道:“老支书,过年好!”
“你是。。。”
“姚清远,姚云轩的小儿子。”
“呵呵,稀客,稀客,快请进屋来坐!”王大娘热情地招呼道。 激情燃烧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