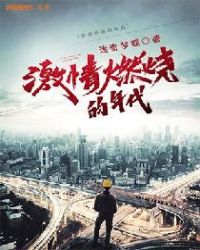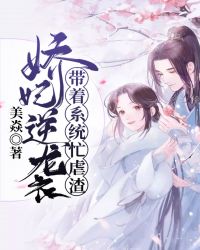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激情燃烧的年代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接下来,就是刘益首的尸体火化问题。姚动生与刘云鹤商量,准备在工地民工的生活区域一个偏僻的角落,替死者搭一个简易的能遮住阳光和雨水的灵棚,在灵棚正中铺一张灵床,以便沐浴更衣后放在上面。在此举行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让工地上的工友们都来一一拜祭,然后再送往火葬场进行火化。
为慎重起见,姚动生把堂爷爷姚云轩请到工地坐镇指挥,以便在刘云鹤刘翔等人面前,显示对逝去的刘益首极大的尊重。姚云轩来到之后,就吩咐姚动生道:“第一件事儿就是刘益首寿衣,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死者身上贴身穿白色的衬衣衬裤,再穿黑色的棉衣棉裤,最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的长袍。而且,整套服装还不能有扣子,也就是全部要用布条条(俗称带子)系紧,这样做是取其谐音‘带来儿子’,表示后继有人的意思。”
见姚云轩说的有理,刘云鹤与刘翔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刘云鹤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的头上还要戴上一顶挽边的黑色帽,帽顶上缝一个用红布做成的疙瘩,用来驱除煞气,这样做对家人或子孙后代才吉祥,在我们凉山州,如果死者是男性的话,脚上要穿黑色的布鞋,而如果是女性的话要穿蓝色的布鞋。”
姚云轩表示同意刘云鹤的看法,继续说道:“寿衣一定要是传统的式样,哪怕改朝换代、时过境迁,平时再也不穿民族的传统服饰了,等到临死的那一天,也得要恢复原来的老旧装束。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人死之后就要去见远古的老祖宗,如果老祖宗认不出自己的子孙,就不会让他认祖归宗,他就进不了祖坟,也上不了祠堂的牌位。”
这些姚动生基本都懂,而且都一一照办。然后就问刘云鹤还有哪些不是和没办好的地方。刘云鹤对他说道:“我们那边在为去世的人穿寿衣的时候,除了穿上死者平时所穿的衣服之外,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件反过来穿的新衣服,这样做是因为在民族传统的观念里,不能把死者平日所穿的旧衣服脱掉,这样方便死者的灵魂回来认识自己的身体,而把后来加上去的新衣服反过来穿,是为了让死者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刘云鹤说到这里,刘翔又进行了补充:“衣服的正面和反面,和穿衣的单数和双数一样,是人们在生与死、阴与阳交接的人生‘换届‘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换装仪式。这种被称为‘反饰’的习俗,是为了改变死者寿衣的穿着式样,使他的灵魂没有办法停留在阳间。同时也有通过反正颠倒来暗喻阴阳两界的意思,因为阴阳两界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是完全颠倒过来的。所以,寿衣就成为人们观念中灵魂的一个代码了。”
姚云轩立刻说道:“这些都没问题,完全可以办到。” 最后,经过大家协商,买了一套中山服,把上面的钮扣和风纪扣,以及裤子上的拉链等全部拆除掉后再穿到了刘益首身上。
在从医院冷冻库接回刘益首尸体之前,工友们利用工地支模材料的木枋与黑色多层板,用乳胶进行粘接为刘益首定制了一口简易的棺材,以便将他的遗体置于其中供人们吊唁。姚动生还将手机中存贮的刘益首的照片,去照像馆里制成一个二十六英寸的黑白遗照,放在灵堂正上方悬挂。
一切就绪之后,姚动生带领众人去医院利用它们的车,将刘益首的遗体送回工地。下一步就是要给死者沐浴更衣,姚云轩对刘云鹤说道:“工地人多眼杂,不可能去淋浴间为他洗澡,只能用桶去打点温热水来,用毛巾沾水一点点地替他擦拭身体。”
待姚动生刚要转身去办,姚云轩又把他喊住:“叫厨房的采购人员去市场上买三只活着的公鸡回来养着,这两三天都要用,一会儿引魂就杀一只!”
姚动生便去食堂安排。一会儿,他又把木嘎奢哲、吴登峰、李老蔫、桂正雄等人找来,对姚云轩说道:“堂爷爷,这几个都是我们老家的工友,有什么需要跑腿的活儿,尽管安排他们去做!”
于是,姚云轩就安排木嘎奢哲、李老蔫替刘益首洗身子。
待到沐浴更衣的结束之后,姚云轩立刻宰杀一只刚买回来的公鸡,进到刘益首生前住的那个民工宿舍里面,将一条白布搭上房粱,从高处穿过后拖下来,再用那只公鸡在他曾经睡过大铺上拖了几下,然后着人继续拖着白布,延伸至屋外那个刚搭好的灵床上,马上吩咐众人把刘益首的尸体抬到灵床上。姚云轩提着公鸡在死者身边走上一圈,这样,相当于就把死者的灵魂也引到灵床上去了。
李老蔫看得很认真也很仔细,他以前没少看姚云轩在老家替人办丧事,所以对这些事儿门儿清,他对旁边的吴登峰说道:“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死者生前做过屠夫,那么家里人要用一块大红布把他的手包起来,伪装成被斩断的样子,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在阴间被他宰杀的牲畜咬他的手。。。”
吴登峰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真有那么神?我看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
不曾想此话被姚云轩听见了,他回过头去狠狠地勒了吴登峰一眼,心想这么严肃的场景,你们太不尊重死者,马上便冲他吼道:“过来,给死者嘴里喂饭去!”
吴登峰立刻去食堂端来一碗米饭和菜,给死者嘴里象征性地灌了几勺。这是按照旧时的规矩,这是为了不让死者张着空嘴,饿着肚子成为饿死鬼到阴间去受罪。末了,姚云轩又吩咐吴登峰:“再在他嘴里放一枚铜钱去!”
吴登峰不服气地答道:“你真能出难题儿,这会儿我上哪儿给你弄铜钱去?那都是大清王朝才有的玩意儿,民国都只有袁大头!”
众人一听都纷纷取笑他:“笨!你真笨!没有铜钱,难道身上还没有钢嘣儿?笨得要死!”
于是,吴登峰还真的拿一枚硬币塞到刘益首嘴里,姚云轩见此也没说什么。这个意思是“含口银子”,意为死后灵魂保佑活着的人们平安吉祥、健康发财。接着,他就安排人在给死者灵床不远的地方烧纸锭、锡箔之类的信物,也就是俗称的烧落地纸。姚云轩问:“他生前睡过的枕头还在不在?如果还在,连他以前的床上用品,也都一块儿拿来烧掉!”
这个风俗,有些老一点的人会明白,有些年轻的工友就不明白,实际上把死人的枕头顺便烧了,俗称“捎上”,多少年来传来传去,由于发音相近,“捎上”便被说成是“烧上”。
这些前凑序曲结束之后,就是停尸这个重大活动了。为何要停尸呢?那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很难判定人是真死还是假死。所谓的假死,可以分很多种,其中古代战争频繁,有人流血过多暂时休克,也有产妇难产而大出血,心跳脉搏频率减少呼吸微弱,手脚僵直冰冷,让医生都无法感觉到此人是否活着,往往连孕妇带肚子里的孩子被误诊已死遭到活埋。而现代医学发达,有心电图等仪器,不需要停尸等待都能鉴定出人死人活,但停尸这个古老风俗却保留下来了。
停尸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死者亲属都会把头低着,这表面上是一种表达悲伤的方式,而另一种原因就是观察棺材底下有没有东西滴出来,要是死者小便失禁,那说明死者还在新陈代谢,那就是假死。另一种就是滴出来的是血,家属就观察血的颜色,判断出死者是否是假死。
众人把刘益首的尸体装进棺材而不封钉,按照老规矩棺材盖不能盖严,在死者的头部留有与头部等长的一段空隙,打算在工地停两三天供亲人朋友祭奠。由于不似在老家供给土葬之用,而且在蓟州城也很难买到真正的棺材,工友们别出心裁,用工地的木方染漆与黑色多层模板,替刘益首用白乳胶粘了一口棺材。
这是白天的仪式,到了晚上具体活儿就是为死者寻灵。这可是个不眨眼的难干活儿,一方面要不停地为死者烧纸作揖,更主要是防猫儿狗儿上前来惊挠。因为死者灵前摆放不少糕点供品,那些小动物们趁人不被,往往前来偷吃。犹其是猫儿如果来挠,多半就要出大事。传说中半夜出来猫儿容易惊到死者的魂灵,会让死者魂飞魄散,甚至变成厉鬼出来害人!
只有面对死亡,才深切体验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人生一世,不可再生,每一时每一秒都是以逝去的态势向终点靠近。而且人生只有那么一次,时时刻刻始终都在彩排,没有一次正式演出,或者说始终都在正式演出,没有机会进行彩排。人的出生,就是向死亡迈出的第一步,从来都不能倒退,只是一个劲儿地走向死亡之路,在这条路上生命多存舛,人生无常,不可预测。
按老家的风俗,亲人要在灵棚里通宵守夜。而刘益首的父亲刚来蓟州,姚动生怕他夜里很不习惯,因为蓟州的半夜三更,天气异常寒冷。所以,姚动生决定分派木嘎奢哲和其他工友陪着老人给刘益首守夜,每两小时一班守至天亮,木嘎奢哲带一名工友守10至12点这班。
灵棚里被昏黄凄凉的灯光笼罩着,上面正中是刘益首的巨幅遗照,两边有两朵花圈屹立。正中间整齐地摆放着刘益首的棺材,里面的遗体已经被素布覆盖全身,头向内脚对外直挺挺躺着。棺村前面一个供品桌,上面有水果、糕点之类,地上蜡、香、纸燃烧,烟雾燎绕。燃香的旁边放了一个铁盆,专门用来烧纸装灰的,棚内不时有嬝嬝青烟飞出。
捱过这漫长的两个时辰,转身离开之际,木嘎奢哲瞥了室内一眼,刘云鹤与刘翔两人头缠白布,跪扶在棺材边悲怆地哭泣,还不停地抽搐,那场面可谓悲天怆地。一个人活在人间,或苦或悲,或甜或喜,总有他们存在的价值,让身边的人感受着,或开心或痛苦。因为人是社会人,一个群体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的死去也许对于世间万物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地球照常转动,太阳照常升起。可他的家人、朋友定会痛苦悲伤,因为这个人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他人或家人不再孤单。
驻足凝视片刻之后,木嘎奢哲带工友返回工地。可是,他回去后久久也无法合眼,刘云鹤那一幕悲伤情景始终在他脑海中晃来晃去的,挥之不去。生离死别是人生的悲剧,特别是至亲的故世更令人终身难忘,这也许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怆凉、凄惨、惊悚、悲恸的震撼心灵的经历。
这种情况,木嘎奢哲在老家也司空见惯,如果谁家有人去世,那全家的亲人必须通宵守灵,而且左邻右舍则大门紧闭,据说是避阴晦气。死人家属如果行走至邻家庭院,就要被长辈们呵斥责骂不懂事,被认为把晦气带到邻居家了。
不仅如此,在把死者“送上坡”入土为安之后,所有参加人员一定要从火堆上走过,以“烧掉”阴晦之气,给人一种说不出来别扭、冷漠的感觉。让木嘎奢哲心中有了更刻骨铭心、肝肠寸断的记忆。
祭奠亡者的仪式一般要操办了三天两夜,而且还通宵未眠,动辄花上数万元。仪式上请毕摩(当地的祭师)主持各种祭典,敲锣、打鼓、诵经、念祭文,随时还伴有亲人在停歇的间隙之中放声大哭,嘴里念念有词地哭诉,大多是诉说死者生前的经历,甚至晚上还要请人彻夜唱“孝歌”,念各种经文以超度亡灵。
在这三天的祭奠之中,守灵出殡前后两天,披孝的家人不踏入厨房,一日三餐由邻家人帮忙操办。另外还要请一些老者来帮忙,扎一些花花绿绿的“供品”:纸竹糊制的别墅、洋车、彩电、沙发、手机。。。还要为死者裁剪出无数套一年四季换装的纸衣纸裤。有些祭品制作精美,而且体型不小,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另外,就是把亲友们送来的黄纸,用半园形的锉子钉上印痕,做成烧给死者的纸钱。
老家还有“老不送幼,大不送小”的忌讳风俗,也就是说刘益首如果回家安葬的话,他的堂兄及堂嫂、堂姐及堂姐夫以上的亲属皆要“迴避”,那么,陪同他入土为安们就只有一帮与刘益首同年的村里人了,连他的父母哥姐都不能跟去送行。
木嘠奢哲有时都觉得,这个风俗太操蛋,完全不符合人情世故,而且左邻右舍闭门闪躲,如“避瘟神”一般的忌讳也不可取。但对于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大操大办也固然不好,丧礼应隆重而又简单,宗族亲戚朋友聚集一起共同悼念一位走完漫长人生道路的死者,才是最佳的选择。“生离死别”的风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的对“生命”及其意义的感悟体验与理解,这也是一个更宏大更深奥的问题。
三天一过,姚动生通知火葬场派车来拉刘益首的尸体。在火葬场隆重的一阵庄重哀乐声中,刘益首很快便被推进火化间,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堆骨灰,装在一个黑匣子中,送到了刘云鹤的手中。在火葬厂门前的空地上,姚动生焚烧了一个花圈,大伙儿团坐在一起,为刘益首祈祷,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一丝青烟在寒风中飘然而去,为刘益首准备的一瓶二锅头在飘起的烟火中渗入了地中,留下一团湿乎乎的泥土。
生命从无到有,物质从有到无,包括荣辱、名利、心情最终全都会烟消云散,不留一丝痕迹。这个自然法则和规律,是客观存在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悲观,有人执着,有人超脱,面对相同的人生走向,态度迥异。
想想人生百年,看似鸟儿丰满的羽翼,但在浩渺如烟的历史长河中瘦的可怜,区区一粒尘埃而矣,微乎其微。一个生命从有到无的事实,没有人能够改变。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最终不也一去不复返,包括世外桃源修炼的归隐居士,不也一样来日遥遥无期。 激情燃烧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