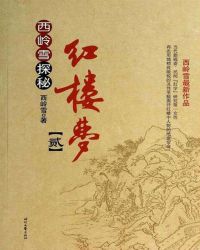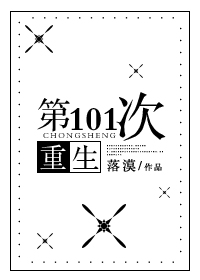10.宝钗与黛玉的金兰契
10
宝钗与黛玉的金兰契
宝钗和黛玉是书中最势均力敌的两个女主角,一个端庄守礼,一个才情横溢,正是各擅胜场,难分轩轾,可说是“感性”与“理性”的两大极端代表。然而脂砚斋却偏偏说:
“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这句话初看极其无理,细想却并非空穴来风。《金陵十二钗》册子中,正册首页上,便是两株枯木悬一玉带,旁边雪下埋着股金簪,诗云:“可叹停机德,应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将宝钗比乐羊子妻,极褒其德,而黛玉比谢道韫,仰重其才,却将两人命运系于一诗,正是“德才兼备”;而宝玉梦中所温存之可卿,又是“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的,果然“兼美”,可见其纠结难分,你中有我。
世上果然有如此兼美之人,堪称典范;而若能娶此二人为妻,更是遂心如愿,梦里才有的好事儿了。然而此书要极力写明的原是“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整个前八十回,宝钗与黛玉的关系,便正是铺叙这“好事多魔”的过程,从对立到和谐,直至合二为一。
前文说过,早在宝玉对钗黛湘以及众女儿并无分别时,黛玉已经妒意横生,认定宝钗为第一假想敌了。她一再地试探宝玉,跟他闹别扭,哭一阵好一阵的,直到三十二回“诉肺腑时,才终于确定了宝玉的真心,从此再无疑忌之心,却对宝钗越发含酸,看到宝钗哭红了眼睛,忍不住出言讥讽:“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
同时,宝玉捱打后,也的确是宝钗对宝玉的第一次真情流露,但她与黛玉的较量却绝不是旗鼓鲜明分庭抗理的,而是一直暗中较劲儿。在宝钗,本以为德才兼备,万口褒赞,品貌不输黛玉,德行更足自夸,而且又有元妃赏赐的暗示,“金玉姻缘”的风声,上有王夫人疼爱,下有袭人助力,中间还得到史湘云等的极力支持,远比黛玉人多势众,对于宝二奶奶之位原是稳操胜券的。
种种心理暗示之下,薛宝钗渐渐已把自己看成了宝玉的“准未婚妻”,不但时时提点规劝,还不避嫌疑地替他绣起肚兜儿来,而且绣的是鸳鸯。偏偏宝玉不领情,这时候已经同黛玉互相倾心,誓同生死了,因此在梦中也叫出来:“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书中说,宝钗听了这话,登时怔住了。显然,不论宝钗有多少优势,宝玉心中却只认定黛玉一个,这一点,却令宝钗情何以堪?
现在,摆在宝钗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是撇开宝玉,斩断情根,别觅如意郎君。这显然不太现实,一则有损家族利益,上哪里再找贾府这样的大靠山呢?二则宝钗此时已对宝玉情根深种,也实在放不下;
第二条路是与黛玉斗到底,非争出个你死我活不可。但是宝钗毕竟是温厚守礼的闺秀淑媛,而不是泼辣狠毒的王熙凤;且黛玉上有贾母疼爱,又得宝玉真情,绝非来历不明出身低微的尤二姐,真个斗下去,宝钗未必能赢。
第三条路,则是化敌为友,接受黛玉跟宝玉的感情,二女同事一夫。
显然宝钗选了第三条路。
这选择是被迫,但也是主动的,而且不只是对湘云、对袭人那样施以小恩小惠的收扰,不是帮忙做个针线活,赞助办个螃蟹宴这么简单,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大手笔,是“攻心之术”。
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是宝钗对黛玉的小试牛刀。先是出其不意地笑着来了句:“你跪下,我要审你。”因黛玉不解,便又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谁知黛玉仍然不解,宝钗遂笑着说明:“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那里来的。”
将“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与“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联系起来,罪名已经很清楚——读了邪书,移了性情,竟还公诸于众人之前——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传统礼教下,却的的确确不是一个闺秀的所言所行。
因此黛玉回想清楚,也自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主动说:“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竟然乖乖上钩,主动受教了。
于是宝钗安稳坐定,深入浅出,由己及人,说出了好长一番大道理来,“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这是黛玉的第一次服软儿。
但凡钗黛之情,必由宝玉眼中鉴定,因此后文又有众人议论惜春画事,宝钗为黛玉理鬓一节,“宝玉在旁看着,只觉更好,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抿上鬓去,也该留着,此时叫他替他抿去。”
到了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是宝钗进一步出招:上次是以理服人,今次则是以情动心。不但体贴黛玉之病,送她燕窝补养,且说:“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
如此感人肺腑之语,怎不让“情情”林黛玉感激涕零,遂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彻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推宝钗为生平知己。
此回目既名“金兰契”,可见宝钗完全收服了黛玉,二人已是情同姐妹,合二为一了。
因此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湘云暗讽黛玉小心眼,必会妒嫉贾母多疼了宝琴,宝钗便为其辩护说:“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样。他喜欢的比我还疼呢,那里还恼?”
书中借宝玉之观察,写黛玉赶着宝琴直呼妹妹,并不提名道姓,而宝琴亦觉得黛玉出类拔萃,故对之亲敬异常。宝玉心下十分不解,过后特地往潇湘馆询问:“是何时孟光接了梁鸿案?”黛玉因把说错酒令、送燕窝等事细告,并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对宝钗心悦诚服,其挚爱之心,较从前之史湘云犹为笃诚。
到了五十二回,二人感情益发融洽。书中再次借宝玉之眼之口称赞:“好一副‘冬闺集艳图’!”
正是寒冬腊月,潇湘馆中却是暖香春色,不但宝钗、宝琴都来看黛玉,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围坐在熏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作针黹。此时,岫烟尚未提亲薛蝌,似乎是“外人”,但我们知道,薛家姐妹和邢岫烟很快就会“姑嫂一家亲”了,那么黛玉夹在其中,又是什么关系呢?
接着就是五十七回的重头戏了,《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紫鹃一句玩笑把宝黛之情通了天,众人都已心知肚明,薛姨妈还在装糊涂,直说:“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但是宝玉养了许久的病,贾母又一直留下紫鹃伏侍,这件事做得这么明白,亦如袭人的二两银子一样,薛姨妈再是自欺欺人,也不能够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于是她也向女儿宝钗学习,改用怀柔之策,对黛玉忽而亲热起来,且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无靠,为人作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我们也洑上水去了。”
可叹黛玉心实,既早已认了宝钗做姐姐,如今听见薛姨妈一番话,也就心甘情愿地说:“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
而宝钗便同母亲半真半假,一唱一和,从月下老人说到岫烟的亲事,最终提出了一个“四角俱全”的主意来。按薛姨妈的说法,提到这建议本是因为贾母有意提亲薛宝琴,只是宝琴已经有了人家,故而薛姨妈只好另给一个人,不如就把黛玉说给宝玉。但是此前明明满园子里尤其薛姨妈天天念着宝钗的金“要找个有玉的来配”,如今倒怎么说没人可给呢?难道宝钗不是人?这显然是以退为进、无私显见私的说法,而黛玉是聪明人,也不会听不懂——所谓四角俱全,乃是宝钗为姐,黛玉为妹,钗黛同嫁宝玉矣。
那么,这个建议黛玉接不接受呢?
对于黛玉来说,她下世只是为了“还泪”,一心都在宝玉身上,“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只要宝玉好,她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她决不会离了宝玉去跟第二个人,所以之前不是担心宝钗藏奸,就是害怕湘云多事,但是对袭人却毫无醋意,一片赤诚称之为“嫂子”的。
可见黛玉之醋,并不是怕宝玉多情花心,因为她是宝玉知己,深知宝玉之情并非淫邪一路;她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不能跟宝玉在一起。只要不把她和宝玉分开,宝玉另外再娶多少个,她都不会在意的。
今天的恋人们,最在意的就是一心一意,心无旁鹜。但是在古时,男人三妻四妾是常情,女人善妒反而是七出之罪。黛玉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害怕宝玉辜负自己,却并非没有容人之量。所以只要不破坏她能跟宝玉长相厮守这个大前提,她是不会计较与别人分享宝玉的。
尤其五十七回认了薛姨妈做干妈,五十八回时薛姨妈索性搬进潇湘馆来了,“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贾母见如此,也十分喜悦放心。”很明显,黛玉这自幼父母双亡,在亲情上极度缺失的女孩儿,在薛姨妈母女的双重攻势下,彻底缴械,而且是心甘情愿地服了输。
第五十八回宝玉病愈,往潇湘馆来看黛玉,见其病虽好,但亦发瘦得可怜;黛玉见宝玉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些微谈了谈,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
虽只寥寥几句,已写得柔肠百转,凄苦缠绵。此时黛玉经过紫鹃试玉之举,已经深知宝玉对自己的心意,满心里再无丝毫疑猜妒忌,却只是一心为宝玉心疼难过——忆昔流泪是感激相知,催促歇息是怜惜体贴。宝玉这次病得实在严重,休养了这许久还要拄拐而行,哪里还能再禁得再有波澜蹉跎?
此时的宝黛之间,已经是“情投意和,愿同生死”,只要宝玉能好,受什么委屈黛玉也是不会介意的了。于是,就终于有了宝玉生日宴上的半盏茶。
第六十二回中,宝钗与黛玉正在说话,袭人送了茶来,因只有一盏,遂说:“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
这时候宝钗和黛玉两个人的表现都极为奇怪:那个一向温柔谦让的宝钗竟然抢先接了过来,还说:“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既然不渴,又何以抢先?而且喝了一口后,把杯子还给袭人就是了,她却把剩下的半盏茶递进黛玉手中,这不是逼别人喝她的剩茶吗?
很明显这是宝钗开出的一道题目。须知“茶礼”在古时是极为讲究的,而红楼中关于茶订和茶道也多有照应,比如凤姐对黛玉开玩笑时便说过:“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就说的是这种规矩——订婚前,下聘叫“过茶订”;新人进门,要给长辈敬茶;男人娶了不只一位妻妾的,小的要给大的敬茶——这些道理,钗黛这样的大家闺秀不会不懂。所以,宝钗递给黛玉的这半盏茶,是半真半假地试探,而她所以敢做得如此大胆果断,是从第四十二回“兰言解疑癖”到现在这二十回里层层铺垫,做足了功课的。如今胜券在握,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收服了黛玉,所以才敢如此“放肆”,检验战斗成果来了。
此时,那林黛玉该怎么做呢?接是不接?答是不答?应是不应?
这样的尴尬怪异举止,连站在一旁的袭人也觉得不妥,明知黛玉是有洁癖的,因此赶紧说:“我再倒去。”然而黛玉却只是轻轻笑了一笑,说:“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我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她到底是接了!
可怜黛玉,痴爱宝玉如此之深,至于委曲求全,自愿居次,正如同《儿女英雄传》中的张金凤与何玉凤。
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钗黛同嫁了宝玉,也不代表宝钗为妻黛玉为妾。古人有“三妻四妾”,可以最多娶三个女子做“平妻”,虽姐妹相称,共事一夫,但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原配正室。
黛玉名为“潇湘妃子”,这典故正是出于舜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潇妃与湘妃一同嫁给大禹,潇湘二妃并无正庶之分,这岂非暗示宝黛同嫁之命运呢?
且回目中又有《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一名,将宝钗比作杨妃,黛玉形为飞燕。而在历史上,那杨贵妃深得唐玄宗宠爱,曾将自己的姐姐都引入宫中,俱封了夫人;而赵飞燕更是与妹妹赵合德一起承欢汉帝,广为流传。书中说茗烟孝敬宝玉,“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亦可谓逗漏先机矣。
钗黛二人既然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宝、黛、钗之间的纠结纷争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文中关于三人的情感戏突然减少,连一次小争吵都没有了。
如果事情真能够照着计划发展下去,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兼美”的好事,可叹的是,八十回后风波又起,终至黛玉薄命,早早地魂归离恨天了;脂批说“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可知宝钗嫁了宝玉后,相待宝玉之情不压于黛玉,无奈宝玉心中不忘黛玉,“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终究是“悬崖撒手”了。
不论宝钗有多么完美,她毕竟不是黛玉,毕竟不能取而代之,“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钗黛合一”终究只是个理想,这两人在《金陵十二钗》诗册中原是一体,到了《红楼梦仙曲十二支》中却已分作两支,各有归源了。黛与钗,无论怎么合契也好,到底不是一体。 西岭雪探秘红楼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