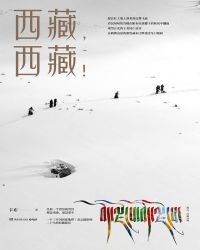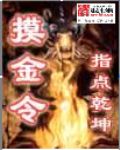◎ 陈塘夏尔巴
做沙画的僧人们,又一次放大了正方形,做的仍然还是一个同比例放大的图案,这样的图案由里向外发散。这种发散的方式,就像散落在西藏各地的原住民,他们的居住方式看上去是以拉萨为中心,或者说,人们住在大昭寺的周围,然后有了拉萨,有了拉萨的周边,一直到这一大片土地中所有的边地和沟谷之中,都有了各种不同生活习俗的人。看上去这是一种生命的结构,我当然知道,西藏的夏尔巴人,他们中有一部分,住在了遥远的山沟里,那条山沟叫陈塘。
陈塘,在陈塘沟的一个小山顶上,是个镇级单位,从山脚到山顶共有1000多级台阶,这可能是全国最后一个还不通公路的镇级政府。我问过镇长,为什么镇子不建在下面通公路的沟里而建在山头,这很不方便。镇长说:“政府需要靠前守边。”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
我去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所有的物资都必须靠人力,用牛、马驮至山顶,我在这里遇到了需要在这些石阶上上上下下的孩子。孩子们为了上学,每天要上下石阶,放学后的孩子们还会背上各种物品再上山,我问他们有没有报酬,他们说背一趟20元。途中也常见妇女们在额头上勒一条牛皮绳子拉着身后的一个大背篓背货,背篓里有时候还会坐一个孩子,有时候货物垒得很高,从背后看,背货的人看上去有2米多高。这些在石梯上,每天上上下下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夏尔巴人,传说,他们是最能负重爬山的人。
夏尔巴人就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地,生活对于他们就是这样,去任何地方,只能依靠脚力,人们在这样的大山里只能把生计放在背上。我们要把所有的拍摄装备搬上去,当然也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腿,剧组这帮人很能搞怪,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灯,在这个灯的包上用剧组的黑色大力胶给我贴了一个大大的“LV”。我很时尚地背着这个包,开始上山。这条上山的路正是近年热起来的户外徙步穿越线路起点,是珠峰东坡徒步线路中的一个重要结点。陈塘的南侧山后,就是尼泊尔。
陈塘沟、嘎玛沟的产生和这里的朋曲河,有着直接的关系。
朋曲在流过定日白坝村,拐了一个大弯向南,它横切了喜马拉雅山脉,掉头向南。从这里开始的朋曲,在聚合了数十条珠峰群东侧的冰川融水之后,它有了切开山脉的力量,切出了陈塘沟。因此,喜马拉雅山脉在自西向东经历了一系列极高峰的精彩纷呈之后,到这一段后突然戛然而止,10~20千米宽的范围,全是有极高落差的河谷地带,附近没有超出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峰。
近些年日喀则旅游宣传常提到喜马拉雅五条沟,五条沟其实也就是个说法,这个说法让人们便于记忆,但喜马拉雅的山沟哪里止于五条,这种说法的真相是:我们来讲喜马拉雅在日喀则这一段的这五条沟。单就陈塘沟附近,看卫星地图,上面就有诸多绿色树杈状的分支,那些分支全都是沟,规模比较大的至少有三条。在珠穆朗卓峰上方有一条比较大的沟,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嘎玛沟。在经历了陈塘沟的断裂带之后,喜马拉雅继续向东绵延,要到亚东沟才会再一次稍稍断裂,所谓的断裂是指海拔降到了看似不能继续延续的高度。断裂那儿有一个山口,是海拔4500米左右的乃堆拉,那里是中印边境。这个山口在群山之中显得太矮了,于是就断裂了,是高度上的断裂,并不是真的断开。在陈塘沟与亚东沟之间,是一大片喜马拉雅的传说,那是干城章嘉峰群。我喜欢那一大片雪山,无法靠得太近的开鲁山口是我一直以来的向往。
陈塘镇就位于朋曲河谷的半山坡上,我第一次到这里,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匆匆抵达山脚下的藏嘎村,一轮弦月正好升起,它挂在了山坡上的陈塘镇上。天明一看,山坡四周,是人们依山开凿的层层梯田,生活在山谷之中的人们,只能依山层层蓄田。云南如是,广西如是,西藏亦如是,看起来这就是边地居民们的普遍生存法则。每年的盛夏,田地中会长出一种特殊的植物,黄澄澄的是鸡爪谷,这些本地特有的谷类早已经不再用于主食,夏尔巴人用它们来酿酒,酿鸡爪谷酒。
山地人,劳作辛苦。夏尔巴人消除疲惫的办法,是美美地喝上一桶鸡爪谷酒。人们捧着一个短粗的木桶,里边盛放着发酵过的鸡爪谷酒,往其中注入开水后,插入一根比筷子粗一些,镶嵌了银饰的竹竿,用力吸。这酒看上去劲比较大,因为陪我来这里的拉姆局长和日喀则旅游局的德吉刚喝了半桶就开始放声唱起了歌,我发觉这桶好看,立即央求老板,买下了两个,今天它们还放在我办公室的窗台上。
陈塘镇的房子是石木结构,石为基,上面以木为房。我去家访,家家门前均插着一根杆,杆上有分叉,这根杆子显得有些意义不明,好奇的我打听了才明白,这些分叉表明了这一户人家的人数。比如我去的这家,主人叫拉姆德吉,家中养育了6个女儿,2个儿子,这些孩子又生了11个孩子,所以,她家里有22口人,我很仔细地到门口去数她家门口的那根杆子上的分叉,果真是22。
拉姆德吉的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帽子上有花和孔雀羽毛点缀,脖子上挂着由200多个银环连成的项链,胸前挂着6个银制的小串子,腰部系着银带,手腕戴着大白贝壳。她走起路来身上丁零作响,闪闪发光,煞是妩媚。家里的男人们也戴帽子,其上也有花和羽毛,腰间插着名叫“果奔”的弯月形砍刀,这种刀和尼泊尔人的刀特别像,后来我知道不是像,那就是。他们现在头上插的花,已经是塑料花了,这有利于持久鲜艳。陈塘与尼泊尔紧紧挨着,从前他们还通婚,所以村里好多人的亲戚都在尼泊尔,我在村里买了几个从那边带来的手工敲的壶,这几个壶今天还在我家里用于装酥油茶。
陈塘镇有夏尔巴人,有夏尔巴的地方当然就有巫师。我见过一个,他叫多吉平措,62岁。
他有一套专职的服饰,有点脏,唯一值钱的是头上那顶以熊皮制成的圆圈一样的帽子。他身上那件以堆绣做出来的长袍,看上去很有年代感,他表演驱鬼舞蹈时,口中念念有词,眼神犀利。留着大胡子的他在跳起来的动作中会加以摇铃,这让他和他的长袍在陈塘镇的云雾之中显得非常通灵。
在陈塘镇,巫师这个职业是家族传承的。他的职业其实复杂,除了祈福迎祥,也负责请神驱鬼,同时他还是一个医生,他能医治骨折。他说这个地方的人从悬崖上失足造成骨折的很多,有些骨折甚至包括身体里的12对肋骨,面对这些他都会想办法去医治。他说他当了很久的藏医,从24岁开始,现在人老了,视力也逐渐不好,但是救急没问题。他的两个儿子曲培和丹增也在跟着他学,他们现在也能独立去做法事了。凡地处偏远,人们从精神层面上总需要对神明、对大地有敬畏,巫师们除了司职通灵,也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土法去解除人们的病痛。多吉平措的职业在这里古老而神圣,他一直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热爱,因此他常常醉倒在村民的鸡爪谷酒桶边。
陈塘镇的对面,是他们的夏季营地,名叫莫若它瓦拉山。在那里,可以俯瞰陈塘镇,山脚,朋曲与嘎玛藏布交汇,这是一个陈塘版的“大拐弯”。西藏到处都是大拐弯,所以,在山里走的时间久了,我真的不好奇各种河流的拐弯,它们会自然地绕过那些切不开的山,自然形成一个一个的弯,这和人生路,没什么两样。
镇子附近是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充足的降雨和温和的气候,让树木自由生长,我进去过,树高大而且笔直。我想起来在离此不远的萨迦寺听过的一个故事。修建萨迦寺大殿的木材,当年都是从陈塘运过去的。在距萨迦寺不到10千米处,有一座山名叫“仲乌拉”,藏语的意思是“牦牛哭泣的地方”。传说当年修建萨迦寺从陈塘运送木材的牦牛们走不动了,在这座山前流下了眼泪而得名。我去过萨迦寺,那里的大殿中用到的巨木高达几十米,有40根。山岭让牦牛也感觉陡峭,而夏尔巴人却在这山谷中走得轻松自如,他们用的仅仅是一个额头,一双脚,一条绳和一个筐。
离开陈塘镇,下到藏嘎村的路对我这个膝盖不好的人来说,阶梯一定不好走。天气很热,我穿着短袖。下到山底,我们开始在投宿的家庭旅馆院子里做饭,今天说好了我来掌勺。在炒菜的间隙,因为太热了,我去换了拖鞋,并洗了脚,把裤腿挽了起来,用猛火炒菜。
做完饭,开始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两条小腿被虫子咬了,已经起了一大片疙瘩,并且红肿,从那一天起,这些红肿就一直陪着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擦过各种国产药和进口药,全部无效,必须用挠才能止痒,所以直到今天,我小腿上还有一大片黑色的点,那是陈塘给我的礼物。我至今不知道我是被什么样的虫子咬了,我一直很习惯,反正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招虫子恨的人。同一天,浩哥也和我一样被这种虫子给咬了,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会交换各种涂抹的药水。他和我一样,被咬后涂啥都没什么效果,只有不停地挠,甚至我们在不远处的一处温泉,商量着用很烫的温泉水泡,也无效。真是顽固。
后来,我听说了还有比我更惨的人,是司机扎西。
他在陈塘的那几天一直在闹肚子,因此他必须要经常去草丛里光着屁股。在那种时候被虫子疯狂地咬,想一下就觉得可怜,他被咬了之后,每天都得开车。那段时间我们转场频繁,组里一直传说他的屁股烂了很久很久。我相信他们说的,因为他亲口告诉过我,他在没人的时候会脱掉裤子,拼命地挠。
顺着简易公路出藏嘎村,回望,陈塘的日出开始了,陈塘镇被升腾的云雾慢慢掩隐起来,朋曲河面水雾升腾,河对面的夏尔巴人已经开始干农活。后来,尼泊尔大地震那年,我打了两天的电话,才联系上镇长。他告诉我,村里没大事,只是有些老房子塌了,没伤着人,万幸。
我记忆中的陈塘,是曾经在黄昏里路过的一间间木屋。我在那里听见了夏尔巴人围在屋中火塘边的饮酒欢歌,整个村庄都随着夜的来临醉了。我听见了歌者缓缓唱来:“摊开你的手掌,再握紧,我们想要握在手中的叫作幸福。”
是啊,握起来的拳头,大小和自己的心脏一样,是心房。这“三寸见方”的大小就是我们能容纳所有幸福的空间。 西藏,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