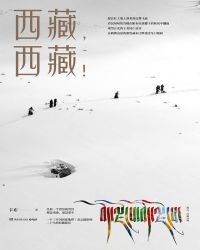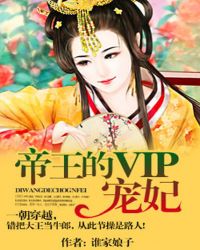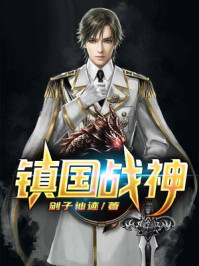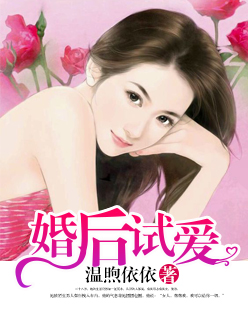◎ 日土岩画
坛城中所有的沙画部分已经完成,僧人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仪式,他们在建成的坛城上摆放了3个黄色的小桌,那上面摆上了供奉的朵玛,然后他们拿来了8块围板,把坛城从四面团团围了起来,这8块围板上有孔,他们在这些孔里插入了定制的木棍,这些木棍上又被他们插上了经幢。最后,他们在四个角上安置了长长的四根棍子,这些棍子插好后,他们拿来了黄色的布幔,他们用这张大大的黄布,把建好的坛城彻底包了起来。在西侧,这个布幔有一扇类似帐篷门的开口,他们撩开了这个开口,在那里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了花、酥油灯以及朵玛,完成这一仪式后,所有的僧人开始诵经。这是坛城中极盛的时刻,这种时刻就像丰收的秋天,正在等待完成收割,待到一切结束,大地将归于沉寂和休养,这像极了四季中从秋到冬的转换。
初冬,再次抵达日土县,这次是计划在秋雨过后的蓝天白云之下认真去探访一种遥远而神秘的存在——岩画。
中国学者常霞青先生在《麝香之路的青藏文化》中曾经指出,青藏高原曾经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我看到日土的岩画之后,对此观点深表赞同。
西藏岩画的早期发现集中在20世纪的前40年,发现者大都是在西藏境内进行考察的外国学者。20世纪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彼得·奥夫施莱特,曾多次深入西藏腹地进行考察,对岩画研究考察较为专业,发现较多的是美籍藏学家温森特·贝莱萨,他从1992年起便在藏北高原考察探索。研究者还发现欧亚草原岩画与拉达克、阿里地区等地发现的岩画风格极为接近,因此推测这种岩画极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间流行于欧亚大草原所有游牧部族的重要风格。反观岩画,从经济形态上看,主要分布于以牧业经济为主,或农牧结合式经济的地区,鲜见以传统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越是人烟稀少和偏远的地区反而会更多地存在,日土的岩画,多为凿刻式的北方猎牧人的岩画类型,藏北高原一直以来都以牧业为主,当今发现岩画存在的密集地区几乎都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西藏早期北部游牧部落社会生活中,原始宗教发展兴盛,具有鲜明的特点,原始宗教是岩画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内在动力。青藏高原北部地区曾经是古象雄王国的统治地域,这就意味着藏北“羌塘”草原在铜石并用时期曾经是文化、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因此,奠定了岩画存在的基础环境。
这一次,我们加上向导寻找岩画的小分队共有五人,因为去的地方叫日土,他们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们号称自己是:西部吃土小分队。我们五个人在阿里以西的山头翻找,个个晒得黝黑发亮,我头上戴着西部牛仔的帽子,要说气场和西部牛仔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差牵一匹马,扛杆步枪,腰里再别一把左轮了。
我们在日土认真地寻找岩画,日土的岩画群四处散落,点与点之间相距甚远,我大约去过30处,还有很多处,我实在没能一次全部到访。据我这一次的调查来看,大致有如下一些地方有岩画:日土县、日松乡、热帮乡、东汝乡、多玛乡乌江村,每一个乡岩画分布不均,处于四处散布状态。比较成形的是热帮乡和多玛乡乌江村。
当地人把乌江村有岩画的地方称为:小人山谷。在那里,一整面石壁上刻满了小小的人,有背包的,有拄拐的,有牵马的,有射箭的。还有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刻画于山体崖壁上的岩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人与动物,尤其是人与牛羊。看来游牧的人们,在很久远之前就描述过了人们与牛羊间的彼此亲密。而最新的考古发现在2018年,藏北羌塘高原已经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这把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时间一下子就推到了4万年以前。
我一直以为,西藏阿里除了象雄文化、古格文化之外,应该还有一种被人们忽略的文化。岩画是不是明显早于这两种文化?这确实有待考证,年代不好界定这是目前的困难之处,这些刻画的痕迹确实还没有特别先进的科学技术能瞬间测定距离今天的时间,何况看起来特别久远的线条,那些人和羊,在他们的旁边又有了刻画的佛塔以及经文,这两种图案的并存,一瞬间就拉近了猜测中的历史和当下的距离,那么只能说是有待考证。不过,我一直觉得有待考证就有希望,起码日土丰富的岩画内容,向我们诠释了藏北高原远古时期的文明程度。而更重要的,我看到了延续,延续至今的,是人们与家畜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岩画中出现过,同时在今天在当下仍然在继续,日土岩画中有90%以上的图像都是动物,在所有动物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牦牛,其次是鹿、羊、马、鹰、狗。我发现,鹿是日土岩画中出现概率比较高的动物,今天的藏北高原上早已经没有了鹿的踪迹,但鹿出现在了岩画里,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从前这一地域的环境和气候。还有一点,我见到所有的岩画中,对鹿的图像刻画都非常具有艺术表现风格,寥寥几根线条就勾勒呈现出一种非常高贵华丽的艺术气质,让观者顿觉赏心悦目。牦牛图像,是日土岩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也是出现概率最高的图像,据我那一次的粗略统计,在日土的岩画内容中牦牛占主导地位的有多处。牦牛大量出现于日土的岩画中,这说明牦牛与早期活跃于羌塘草原的古代族群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今天我们根本无法确认当初的刻画者,是出于祭祀?出于巫术?还是就仅仅是放牧时的随手兴起,唯一可以肯定的,牦牛是羌塘草原上最普遍、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
而反观进入工业社会的当下社会,这种依存关系早已迅速恶化,当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高级,手中便掌握了各种生杀大权,我们对牲畜们可以想养多大养多大,想长多肥长多肥,想杀便杀,想宰就宰。如果你和真正的藏北牧民们一起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和牦牛生活在一起后,几乎什么也不缺。人活着,无外衣食住行。衣,以牛皮制衣帽、鞋裤。食,以牛奶制品、肉。住,以牦牛毛,手捻成线,编织为帐篷。行,与牛马同行。对啊,好像没有盐,你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一大片空地上有几千个湖泊,它们中一多半都是盐湖。对于盐,这一生活中的必需品,在羌塘深处游牧的人们深知它的重要,所以,在远一些的时光中,人们有着独特而神圣的取盐以及驮运仪式。还缺一样必需的生活物品,是维生素。这就体现出青稞的重要性,牧区无农作物,从前的牧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以物易物,牧区的人会用牲畜或者盐去换取农区出产的青稞,这样的事多半发生在盛大的赛马节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茶。茶叶在游牧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亚于盐,换取远道而来的茶叶,这样的需求成就了茶马互市的起源。在藏北,牧民们从不会以自己家有多少头牛羊来计算自己拥有的财富,因为牲畜从来就不是用来计算财富的单位。我见过在大雪中,人们把蹄子受伤的羊用毯子包裹起来,小心地放在摩托车后,带回帐篷休养。我见过孩子们抱着小小的羊羔,同吃同睡。我见过人们用干打垒砌墙成圈,再铺以厚厚的干燥羊粪,让羊群在寒冷的冬天防狼保暖,初生的小羊们会有更特殊的待遇,牧民们为它们单独砌出一个小洞,在天明时分,神山之上阳光升起时,牧民们会揭开盖在洞上的羊毛毯子,一个个地把它们抱到地面,带到母羊跟前吃奶。我还见过家里半大的孩子,一声口哨,家中头羊,那只高大的黑色公羊,出群而立,少年翩然上羊,骑着羊检阅整个羊群。
牧民们因为感恩大地,感恩上苍,感恩一切,所以会用感恩的方式为一切命名,他们感恩牛羊,所以,他们的羊和牛是有名字的,而我们,会不会给自行车起一个名字?牧民们与牦牛,是与适应高原生存的牲畜们共同在这片大地上相依为命,他们叫得出每一头牛的名字,我们中大多的人,是看低了这种相处方式,这是一种情感,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拥有。
有一年到措勤,在春末夏初,花似开非开的季节,我在草地上的帐篷里和游牧的人们一起过林卡,我被他们热情地用青稞酒闹得开始上头,我侧过脸,看着那个叫曲珍的美丽姑娘,她正在唱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吉祥的村庄,搭起了黑色的帐篷,黑色帐篷周边,生活着牧民,牧民养育着5500头牦牛,牦牛有着5500头小牦牛……
曲珍的老公,接着唱了下一首歌,我迷迷糊糊地问唱歌的金嗓子叫什么名字?他们回答我,他叫解放。这名字有意思,问其来由,也简单,他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是路过的金珠玛米救了他,他的名字就改成了解放。
当我站在日土那片旷野,站在刻满了各种动物与人的岩画石壁前,我渐渐开始懂得,认知世界有另一种方式与哲学。 西藏,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