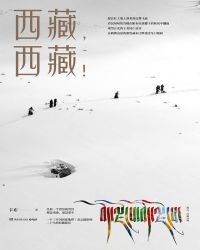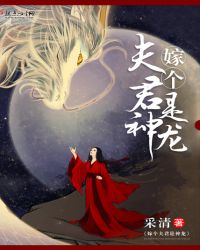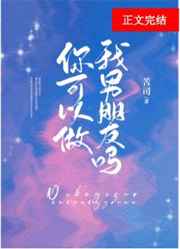◎ 象雄古道
制作坛城的大板上,最外侧是僧人们用笔绘制出来的那些大大的圆,这些圆在整个坛城的最外围。如果把西藏比成这块制作坛城的板,那么,这些边缘就是和西藏接壤的那些地方。这些圆和圆叠加之后,中间留有空隙,僧人们在这些圆与圆之间画上了密密麻麻不同的线条,看上去像一条条的小径,它们通向圆周与圆周之间。在西藏,自古以来,从西域来的人,从南侧印度、尼泊尔来的人,从拉达克那边来的人,从门隅来的人,他们就一直往来于这些小道之中。
有一条小路,从普兰出发,可以直达札达,从札达顺着象泉河可以在什布奇去向印度,这是一条在札达西南方向,沿边境线往东的小路。人们传说,这条路从前是官道,证据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天然的山口。这个山口极窄,处于易守难攻之处,人们通过这里只能从河谷中的两山交会处穿过,穿过之处就是一个天然的关口,在其旁边的山岩之上,有从前的官印印章岩画。我去看过,确实有印,盖在高高的岩壁之上,目前仍然清晰可辨。人们传说,这就是原来通关的印章。我喜欢传说中的久远神秘,这会引发我强烈的好奇心。阿里,是苯教的诞生地,阿里这个名字一直如影随形地存在于西藏的每个角落和藏民族的生活细节之中。
与阿里同宗的拉达克地区的列城,有一幅壁画,画面正中,是白雪皑皑的冈仁波齐,它的四周分别静卧着狮、象、马和孔雀,有四股泉水从它们的口中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向四方流去。这些河流,顺着峡谷奔出,来到平原,最终它们全部汇入了海洋。这幅画中的四条河,就是狮泉河(森格藏布)、象泉河(朗钦藏布)、马泉河(达确藏布)、孔雀河(马甲藏布)。
狮泉河,它起源于冈底斯山北坡,流经克什米尔后变为了著名的印度河;起源于冈底斯山西南部的象泉河穿过昔日古格王国的中心区——札达盆地,横切阿伊拉日居后,从底雅附近流入印度,被称为萨特累季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的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上游,进入印度叫作布拉马普特拉河,它最终汇入闻名于世的圣河——恒河;起源于冈底斯山南面喜马拉雅山的孔雀河,是恒河支流哥格拉河的上游。
这次,我要沿着象泉河一直穿行,我将要行走于札达盆地的峡谷之中。象泉河,其源头海拔约5300米。它从源头西流至门士,经札达、什布奇,最终横向穿越喜马拉雅山后流入印度河。
夏天,我从普兰科迦寺出发,在鬼湖拉昂错折向西,穿过门士乡,沿象泉河,途经古入江寺、卡尔东遗址、曲龙村、东波寺、达巴遗址、芒囊寺,穿过大片大片的土林,抵达札达县底雅乡。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道。沿此古道,有着大面积的古象雄遗址群和古格文明遗址。
我曾经有两次这样的探寻,都试图踏上这条神秘的“象雄古道”。
第一次去探路,过了达巴乡,翻越东波寺那座山后,是一片台地。从这里到门士乡极易迷路,我在一个岔口眼见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在右侧,我被盛开的花吸引,自动驶入而不自知脚下的路是错的。行出去好几十千米后,我才发现,我的行车方向已经偏向了正南,四周已再没有任何可辨的坐标。我很想碰到牧民,但看来我完全被周围这一片高地中的藏野驴包围了,它们远远地一边吃草一边嘲笑我。面对这样的嘲笑,我决定在荒滩上将行车方向强行折向北,我清楚地知道如果向南,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甚至会跑到印度边境去。我只能选择向北,向东北方向我还有希望找到大路。在西藏行车,有时候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只要你还有油,只要你的车还没坏,你就可以见山过山,遇河过河,需要保持的是方向,需要忍受的是对自己决定的怀疑。过了两座山后,在山坡下,我发现了牧民定居点,而且还有牧民,阿弥陀佛,在天黑前遇到了活人。问清方向,继续前行,在半夜12点终于到了门士乡。
第二次,有了经验,路也知晓了,行走变得从容,这一次,我会慢慢游历。
这次先去了直达布日寺。
在噶尔县门士乡的直达布日寺,就是人们传说中神山冈仁波齐的“衣领”,寺庙南侧,有200多米长的玛尼石墙驻守。传说这堵墙是妖魔射向莲花生大师的一支箭,大师施展法力,将这支飞行的箭化为一道墙,终日守在冈仁波齐的门户。人们认为,如要转神山冈仁波齐,必先朝拜直达布日寺,转完神山后,需再重返此地转经,然后到旁边的扎不日温泉,洗掉身上的灰尘,才算功德圆满。我在温泉边碰到了转山归来的人,我们都没淋浴,就一起在温泉水与河流的交汇处洗脸、洗头、泡脚。直达布日寺是一座宁玛派寺庙,其山脚下的多吉帕姆拉康里面,有一个“女性猪头金刚”的修行洞,洞口外面立着一个巨大的泉华石,形似多吉帕姆的生殖器,人们又在旁边摆上了似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头,一并供人朝拜。寺庙僧人不多,我和70多岁的多布杰聊天,他15岁就来到这里。他很认真,带我慢慢参观从前的从前,曾经的曾经,以及各种神迹。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及“大鹏鸟”和“修行洞”等事物,这些事物都和神秘的象雄文明有关。“象雄”一词是古象雄语的音译,在藏语中叫“穹窿”,“穹”是一种神鸟的名字,“窿”是山谷之意,所以“象雄”一词是“穹氏部落居住的山谷”。我,正在这条山谷之中。
从直达布日寺顺河而下,不远处即是卡尔东遗址。
苯教文献《赡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记载,穹窿银城的遗址坐落在卡尔东。“卡尔东”是藏语,“卡尔”即城堡、要塞,“东”是山梁的意思。在一个高约100米的巨大平台上,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托举着遗址的山梁,上去以后才能看见遗址。卡尔东遗址出土文物的年代约在公元200年至公元400年间,和苯教关于象雄王国修建穹窿银城的说法在时间上相符。我上到卡尔东遗址,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砖瓦的痕迹,阿里的大风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土堆,偶有几处洞穴。在山顶,我发现象泉河在这里围绕着卡尔东遗址转了一个90度的大弯。从卡尔东遗址顺象泉河向西约5千米,便是大名鼎鼎的古入江寺。
象泉河的三条支流在古入江寺附近相汇,苯教发源地位于阿里地区,但如今阿里只有古入江寺一座苯教寺院。这里的僧人错成平错坚持认为,古入江寺是苯教的祖寺。有证据表明,苯教大师詹巴南喀大师就诞生在古入江寺附近。
古入江寺以山崖上的修行洞为基础建成。寺庙主体建筑都以白色为主色,包括四五座殿堂,供奉着金、银、铜和石、泥质地的苯教祖师塑像,其中有一尊天然的石像很特别。寺庙窗格、寺庙顶上随处可见苯教“雍仲”符号。2006年,古入江寺门前大兴土木,人们在挖掘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片古墓群。墓葬群出土了“王侯”铭纹禽兽纹丝绸残片和大量的素面褐色丝绸残片、木制生活用具、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器等。这些象雄时期的文物,震惊了考古界和世人。
地域辽阔且位于古代交通要道的象雄,堪称“古代文明交往的驿站”。在吐蕃王朝崛起之前,“象雄”是横跨中亚及青藏高原最强大的文明古国。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古象雄王国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在藏文字创制之前,象雄文字是记载雪域高原历史的重要工具。作为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体现在西藏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生活,从民俗到信仰,处处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煨桑,转经,转山,堆玛尼石,做朵玛等宗教仪式,都源自象雄文化。
我在古入江寺往西的曲龙村的曲龙寺发现过一些破损的文稿,不是经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文字。我交给专家们解读,专家们说这不是梵语也不是藏语,像印度那边的文字。我可以去猜想,但其实最终也就是猜想。正如我们去猜想埃及金字塔一样,你怎么能说这个地球上从前就没有出现过一个高等文明后来被毁灭再轮回到今天的情形?古道的风沙早已经吹了千年,从前和真相,已经被时间尘封。
近年来,古象雄文明渐渐成了一个热点,人们都对其都城“穹窿银城”好奇,也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与探寻,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认为穹窿银城就是卡尔东遗址,有人认为是曲龙村。“穹窿”是“有大鹏鸟的地方”,卡尔东遗址被认为是穹窿银城有文献证据的支撑,而曲龙村山崖上的银色区域,像一只展翅的大鹏鸟,在形象上胜了一筹。其实这两处遗址相距并不远,不超过20千米。我多次从卡尔东经曲龙村前往“穹窿银城”,并上到遗址内部,这里比卡尔东更多的是有着大量的以洞穴为主的遗址。洞穴中的洞壁之上烟熏火燎的痕迹至今仍存,每一个洞穴内都有一个类似佛龛的洞。我在山顶部的一个洞穴之中,发现过一幅残存的壁画,距今天的时间已经很难考证。十多年前,这片遗址附近还有一片钙化池的泉化滩,今天已经完全退化,消失殆尽。唯遗址东侧的象泉河边还有一处温泉,小小的泉眼,还在向外喷发着热流。我曾经在这里,在夜里,坐在泉眼中,在月光下的象泉河畔泡过一次温泉。站在这里从象泉河的南侧望向北侧,这一大片土林真的是像极了一只大鹏鸟。作为一个以画面记忆为主要记忆的人,我选择相信穹窿银城就在曲龙村,我真的很难理解民政部门为什么在地名音译的时候,不把曲龙村这三个字译为穹窿村。
离开这里,走小路会上到高高的台地,这一大片台地其实就是南侧冈底斯山脉冰川融水以及降雨冲刷而成的,所以,台地与台地之间,多的是深深的沟壑。需要不时上上下下,台地结束在东波村附近,东波村的山顶上,有一个遗址,那是东波寺。稍不留意,矗立在山顶已经残破的东波寺遗址便与人擦肩而过。历史上,东波寺曾经香火旺盛,香客远道而来,为了朝拜,在山下挖土筑房。昔日繁华远去,而今寺庙徒留断壁残垣。当日,我们投宿在东波寺下面的东波村,那是两山之间的一个洼处,是不超过十幢建筑的小村庄。在这里居然有一个汉族干部,他是前来驻村的,仔细一问,他叫刘红旗,在这里能见到我们一行人,他显得非常热情,居然在他住的地方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我吃得特别忐忑,这里物资供应应该非常不便,我当然知道在这条路上,他应该碰不到任何游客,相对于外面的世界,这里实在太安静了。
过东波村后,抵达达巴乡,达巴遗址就在北侧的土林山坡之上。
我在达巴寺采访僧人嘎玛丹珍,我要他给我讲传说中的森巴之战,那场达巴宗曾经发生过的惨烈的战争。我一直在猜想僧人与森巴之间的战争,这场传说中的战争,是否和古格王朝的消失在同一时期,或者说是同一场战争?
达巴遗址坐落在达巴乡政府北坡土林山顶之上,呈北高南低走向。达巴河由北向东南方向缓缓流淌,整个城堡布局如倒Y字形,西北与古格都城札不让遥遥相望。从这里往西北方向穿越千姿百态的土林峡谷,是古格另一重镇多香,东面则是镇守古格西方通路的东波。从这个可攻又可守的战略要冲来看,达巴宗在古格王朝的地位可见一斑。遗址中,有残留的大量作为武器的拳头大小的鹅卵石、制陶遗迹。当天夜里,我停留在达巴乡,在这里,我居然碰到了一支乡村乐队:达巴乡“落箭乐队”,他们正在排练,我请他们为我们演唱了一首《在雨中》。
次日,从达巴向西前往芒囊寺。芒囊寺在西藏艺术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那些传说中的克什米尔风格的精美壁画,如今仅存于意大利考古专家杜齐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杜齐在书中描述芒囊寺说:“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过往的商客将它的上部分称为‘石堡’和‘中间的城堡’,下部分有14座寺庙,称作玛囊译师寺。”可是今天,芒囊寺的大部分建筑业已坍塌,我找来杜齐书中不够清晰的黑白壁画图片,那是芒囊寺早期壁画。这些壁画在今天,大部分荡然无存,仅余少量可见,寺庙顶部绘制有图案的天花板据说还是古格时期的遗物。离开芒囊寺前行,上至山顶,大风顺山谷吹来,我相信吹过达巴古城的风,也在轻抚着不远处芒囊寺的金顶,面对时光,当下的人们当然对从前力不从心。
从这里,我将前往古格的都城:札不让,关口就在这里。
两山峡谷之间有一条小河,小河流水浅,几近断流,两山间直线距离不过50米,左侧的山岩之侧有一个巨大的洞穴。传说,守关之人便于此处验看来往人等通官文书,并盖章放行,那些洞壁上的印章岩画就是明证。从这里上到台地之上,向东向南向西极目望远,都是大片大片的土林。如果说璀璨文明是象雄古道上人类的杰作,而壮观、秀美的土林奇观一定是大自然对象雄古道的恩赐。这一大片土林,东起普兰县,西抵克什米尔,南到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交界,北靠阿伊拉日居与噶尔县相接,以托林镇为中心,沿象泉河两岸展布,这就是以土林地貌为主要地质,面积约为2464平方千米的札达土林。
土林地貌是人们获知札达的第一要素,从科学层面上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取决于札达盆地特定的内、外地质作用。在年降雨量仅为160毫米的干旱气候条件下,印度板块持续地向北运动,使得呈半固结状态、沉积厚度大,且具有水平层理地层的札达盆地持续抬升,之后经受强烈物理风化和暴雨冲刷,加上象泉河及其水系的剧烈切割,形成了既雄浑豪放,又精细灵秀的札达土林地貌。这是世界上最典型、分布面积最大的第三系地层风化形成的土林。就像岁月和经历会在人脸上留下痕迹一样,土林奇观给人以直观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蜿蜒的象泉河河水在土林的峡谷中静静流淌,行走在土林环绕的峡谷,宛若置身于仙境中,在梦游一个奇幻无比的世界。
在这里,你可以忘记你见到过的所有土林地貌,札达可以代表所有。
象泉河畔土林环绕的寺庙,叫托林寺,相较于只剩下废墟的皮央寺院,托林寺有着较好的命运。远观托林寺,外表其貌不扬。坐落于札达县城西北象泉河畔的托林寺,始建于996年,是古格第一代国王长子益西沃在阿里地区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只有真正懂得的人知道,托林寺简陋的外表下有着独特的旷世瑰宝——壁画。残存的克什米尔风格壁画,色彩至今浓艳如初,壁画内容有度母、金刚、护法神、僧人礼佛等。托林寺,在我心里就像是立在札达的一座纪念碑,是忧伤而伟大的纪念碑。
古格王朝遗址,离札达县城并不远,出城往北就是。如果能用宿命来解释古格王朝的消失,那再好不过了,但是古格文明的突然消失至今是个谜。吐蕃赞普嫡系后裔形成的王族,在青藏高原的最西端,以象泉河流域丰饶的物产,逐渐建立起统治中心,形成了古格王朝。距离札达18千米的象泉河南岸,现今的古格王朝遗址周遭,是古格的都城札不让。古格立国之初,鉴于朗达玛灭佛而导致吐蕃亡国的惨痛教训,大兴佛教。除了选拔21名青年到克什米尔学习佛教密法,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国王益西沃和他的继承者们历尽千辛万苦,到印度迎请高僧阿底侠到古格来讲法传教,为此,益西沃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古格以佛教立国,阿里地区自此寺院如林。它是吐蕃世袭的延续,还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后在西藏的再次传播找到立足点,开启了佛教在西藏的后弘期,奠定了西藏藏传佛教今天的格局和基础。
古格王朝在13、14和15世纪,经济、佛教和文化艺术发展进入繁荣昌盛时期,16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古格不仅有以“古格银眼”为代表的工艺精湛的佛像、精美的金银器,还有世界上最纤细、最珍贵的羊毛。到了近代,这朵辉煌的文明之花,甚至吸引了西方传教士来传教。
古格王朝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在西藏吐蕃王朝以后的历史舞台上,在维护西藏地域的完整和信仰的继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国王与佛教首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充满内忧外患。据说,1630年,与古格同宗的西部邻族拉达克人发动了入侵战争,古格王朝就此灭亡。
如今的古格,只有一座高达200米几近坍塌的古堡建筑群,一幅幅精美绝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的壁画,一部部金汁、银汁写就的经书,伴随着神话、信仰,被人们传说。
原以为我早已经看遍了札达的土林,霞义沟的出现,绝对是对传统土林地貌的一次颠覆。我对象雄古道进行考察的队伍中有一个札达本地工作人员,他是现任阿里地区旅游局的局长,他叫晋美,是他告诉我这片土林如何与众不同。我当时半信半疑,架不住好奇,我到了香孜乡后,就折进了沟。我确实被霞义沟震惊了,以至当天我就决定在这里扎营,这么好的地方,我得好好看看。次日,我在这里的每一条小沟中进进出出,这一大片土林与札达县其他地方的黄色土林截然不同。这里居然有彩色和白色的土林,还有一种风化后长得特别像蘑菇的土林柱。这之后,这儿成了我来札达的必经之地。来得多了,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每一次到这里,都能在这条沟口遇到一群岩羊,我严重怀疑它们就是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一小群。每次都不例外,一小群岩羊,都会在我的期待下,真的出现在沟口。它们真的会在我的镜头前炫耀它们的技能,那是为它们正名的技巧性攀登,在近乎垂直的土林之中,几个跳跃腾挪,它们就上到了土林的顶部,有一只甚至站到了土林的悬崖边,它脚下已经有松动的沙石从山顶纷纷落下。它们以土林为基,站在蓝色的天空下,它们立于土林的最高处,它们显然是这里的王者。
后来我一直和阿里那些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就应该把那一大片白色的土林命名为卡布土林,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并拍摄宣传那里的人。”我曾经在12月的冬夜里坐在霞义沟的土林边,看着月亮从东侧升起,在西侧落下。我见过月光投射出来的影子缓缓在土林山壁上移动,我曾经坐在这片天地中,思绪万千。
从霞义沟往西不远,就是香孜乡,香孜乡就是香孜古堡,是700年前的遗址,遗址有大量残存的建筑、洞穴及精美壁画,与之相邻不远的两个村庄,是东嘎和皮央,在村庄附近的山崖上,发现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东嘎皮央石窟群存石窟总数近千座,包括礼佛窟、禅窟与僧房窟、仓库窟与厨房窟等不同类型的石窟。蜂巢一般密密麻麻的洞窟,绵延近2000米,其中绘有精美壁画的几个洞窟,集中在东面一片呈“U”字形的山崖上,石窟壁画是用矿物颜料绘制的,因此至今色泽完好。
而皮央村原本就在遗址之上,民居混杂在寺院、城堡、石窟和塔林的遗址之中,间或还有青稞田地和油菜花,这里的总规模比东嘎大一些。
仔细去看,凡有佛像之处,必有人,凡有人之处,必有佛。人们其实一直都和佛在一起生活,所以,佛在人间。
终于到了札达县城,我住进了朋友张勇新开的土林城堡酒店,十多年过去了,阿里地区札达县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酒店。舒适的环境容易让人忘记艰苦,在阿里,在札达,下乡最苦。最苦的下乡旅程,我想是去底雅乡或者是去楚鲁松杰。
去底雅的路有多难走?我第一次慕名而去,因为车的油箱太小,我险些没能回到札达县城。后来的一次,我让助手仔细在前去的路上数一数。他回来后认真地告诉我,去底雅乡要翻越6座山,其中有2座回头弯最多的山,一座山有86个,另一座山有68个,去底雅的公路,还是搓板路。底雅在什么位置?你翻开中国地图,找到鸡屁股下蛋的位置就对了,那里紧挨着印度,是阿里地区有苹果树的地方。曾经在底雅乡问过一个妇女,她叫仁增旺姆,54岁。问及她家里的情况,她说:“我家耕地大概有8.2亩,有162头牲畜,我们住在峡谷里,种地全看天气。如果天不下雨,收成就不好,草也长不起来,草长不起来我就会担心羊会死,如果羊死了,我们这一年的生活就会很困难。”我曾经去到底雅后试着带回来两箱苹果,因为回程的路太烂了,苹果的香味还在,可已经放不了几天,它们全部被颠坏了。象泉河,从底雅流出了中国,进入了印度实际控制区。
札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偏远,这里还有着关于楚鲁松杰的传说,它是那种先车后马再徒步才能抵达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偏远之处的楚鲁松杰的人们之所以能歌善舞,热爱喝酒,根本就是缘于多数人的寂寞。
在阿里,人要活下去不太容易,死反而相对简单。 西藏,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