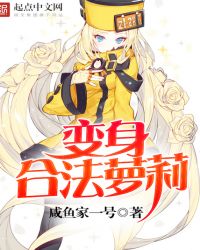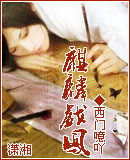◎ 白马岗
从坛城的正上方俯瞰,全部完成的底稿是圆形的,特别像一朵花。如果说花有圣洁之白,我一定会首先想到莲花。白马岗,是传说中的莲花宝地,就是现在的墨脱。
去墨脱,当年算是一个挑战。我曾多次沿着扎墨公路翻越嘎隆拉雪山后前往墨脱,也曾经两次徒步从背崩方向走去墨脱。那个时候,全长140多千米的扎墨公路,在行车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走两天时间,从波密到墨脱的公路一直时断时通。从前,人们用20千米—52千米—80千米这样的千米数给一些歇脚的地方命名,每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都聚集成了一个过往的小镇。第一天人们大多从波密出发,翻越嘎隆拉雪山,住到80千米处已经快要天黑。次日,在全天赶路的情况下,顺利的话在下午甚至更晚一些时候才能抵达墨脱县城。2008年奥运会开幕那天,我好不容易过了垭口到了80千米处,不料半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当夜,距离80千米下行5千米处大滑坡,只能返回。
2016年再次前往墨脱,除了不好翻越的嘎隆拉雪山通了隧道以外,下至墨脱的公路仍然和从前一样。我特别能理解这样的路况,在这里修建公路难度系数太大了。这条山谷全年平均有二百多天降雨,山体地质结构疏松,遇雨很容易滑坡,刚修好的公路不久也会被水给毁了。这一次,相对顺利,甚至我还在前往墨脱公路旁的村庄里买到了本地的芭蕉,这里的芭蕉特别香甜。村子里还有一种木制的筷子,那是铁线木做的,工艺简单,木头材质真好。
墨脱很热,从山上下来必须要换上短袖,最低海拔只有400米,从4000米以上下到400米,确实不容易适应。读陈渠珍旧书《艽野尘梦》,有章节对此地有描述:“次日晨起,又觅得熟悉番语者为通译,复召野番至,反复诘问生番情形。始悉其地皆重山,少平原。人尤太古,无政府,无宗教,无文字;构木为巢,上覆树皮,以蔽风雨。截巨竹留节,以为釜甑,一端实稻米为饭,一端实野虫为肴,泥封两端,洒水烘熟。饭熟倾出,以手搏食。编竹藤为衣,以障身,非恃为御寒也。民野朴,安居乐俗,不通庆市。遍地皆崇山峻岭,道路鲜通。番人来往,则攀藤附葛,超腾上下,捷若猿猴。遇悬崖绝壁,亦结藤梯登,不绕越。亦无市庄。”这一段生动再现了一百年前的墨脱。早年间描述墨脱的还有一人,刘赞廷,河北河间府人。1908年随赵尔丰边军入康,1910年奉命驰援川军,破波密新达寺,南至白马岗。此时刘赞廷为边军中营帮带(副营长)。在这场战事中,刘赞廷任帮带的中营(顾复庆营)进军路线最长。该营自拉里南进,由硕般多一线长驱波密,直插墨脱。刘赞廷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了行军路线,战斗经过以及沿途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物候民俗,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他率部队行进至白马岗、妥坝、波密交界处的一个小村,但见大山横亘,出入鸟道,森林弥漫,云雾返濛而藤萝满谷,花木遍山。刘赞廷曾有感赋诗:
崇峰环绕入云屯,翠叠藤萝山下村。
曲径在望春色远,小桥斜渡夜黄昏。
从前的墨脱,是绝对的边地。是流放人的地方。
从波密县城的扎木镇出发,跨过扎木大桥,沿着往东南方向的公路,行驶24千米,会到一座山前,这座山叫嘎隆拉。上山的路很窄,只能容一车通过,山路崎岖而陡峭。翻越东侧的垭口,公路的东北侧,有低海拔海洋性冰川的冰舌延伸。半山之上在夏秋季节会开满雪莲,过了垭口,能见到3个小湖,本地人叫嘎隆拉天池。湖水的颜色一般随天气而变,下至半山,湖水外溢,渐成小河。因为公路盘旋直降,小河从上层公路垂直掉入下一层公路,居然形成了一个天然瀑布。这个瀑布有点像架在公路上的淋浴房,专门洗车。往下,离开了东侧的冰川后,植被渐丰,从高山灌木一直到森林密布,间隔距离没超过5千米,下到山底过了几条横切公路的河流后,便是52千米。扎墨公路的每一个歇脚处,是以千米数命名的,从24千米到52千米,再到80千米。从80千米往后,公路会从河谷中的北侧转到南侧,北侧正是一条大江:雅鲁藏布江。公路在这一段会顺着江水和芭蕉树最后抵达114千米处,那里就是墨脱县城。这条简易公路由东蜿蜒而来,往西曲折而去,十几年前我去时,用时最长的一次是14小时,前几天看到一个朋友去,问她用了多久,她说用了9个多小时,看来公路仍然时断时续。
从墨脱县城出发,往南,沿雅鲁藏布江而下,有一个大拐弯,是果果塘。墨脱附近的路同样不易,近年好些乡已经通了公路,甚至部分村庄还通上了水泥路和柏油路。这次前往,是雨季,沿途遇到很多大小不一的瀑布,每一条都水量巨大。在果果塘继续往南前进的一个垭口,我发现了曾和恐龙在同一时期的桫椤,而且很高大。我见到附近村庄的人们在山边的坡地上采摘一种植物,仔细看,采的是雨后新冒出来的一种白色野生蘑菇。我向村民们买了很多这样的蘑菇,回到县城后请饭馆帮着加工,美味。
我去墨脱遇到一件怪事,那么多次来墨脱,早年间,为了证明我抵达过这里,我曾经坐在老县政府门口,以那个大门为背景拍摄过一张照片。很奇怪的事发生了,我二十年都没丢过任何照片,且,我在去墨脱的路上,回去的路上,这些前后的照片都有,唯独就没了在县政府门口拍摄的那张照片。我想了好久找不到答案,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也许是从前来的这么多次,我都没回过我自己的村:卡布村。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叫卡布,我跟藏族人讲:“嘎布。”他们瞬间就明白了,哦,是曲登嘎布(翻译为白塔,嗄布就是白色或者喜欢)这个意思。我给汉族人就得讲,这是我出生地的一个村庄名字,稍显费力。不过,很难想象在相隔好几千千米的地方,在墨脱的山谷中居然也有一个村子叫卡布。我曾经在山南地区隆子县的斗玉乡(今为斗玉珞巴民族乡),在那个深深的峡谷中发现有一个村子也叫卡布。当我发现这两个村庄与远在几千千米外的理塘那个叫卡布的村子同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天意。
到了这三个村庄,我理所当然是回家了,理所当然要有故事,这种归属感让我差点尝试去各地竞选村主任。
确实,我回到了我的村庄。不过,我是被村子里的桑杰拉姆带回来的。昨天我在墨脱本地找的珞巴翻译,就是她。工作间隔我问起她,她居然告诉我她村子的名字是卡布。我不大放心地问她,是不是“卡布”这两个字,她肯定地告诉我:“是。”
这必须是缘分,这必须要进村去。
我们到了村庄,她和家人们非常热情而且正式地欢迎了我们。围坐在她家的火塘边,我吃了一顿最正式的珞巴家乡饭,他们家用了各种型号大小不一的石锅做了很多种我从没听说过也没见过的野菜。这一顿饭,我吃得特别香,一定是因为有家乡饭的味道。吃完饭我对桑杰拉姆的爷爷笑着说:“我这个村主任可真没当好,这样的好饭我居然从来都没吃过。”爷爷叫平措,我去的那年他快要70岁了。老人都有故事,我喜欢听老人讲故事。
从前的猎人,就在丛林之中过活,丛林中的生活只需手持一张弓,背上毒箭筒,做几个捕猎的陷阱,便会以那种古老、率直的方式持续。森林密集而空旷,任何进入其中的人,都能有那种自在从容地处于一个他自以为是自己的地方的感觉,这块土地专属于他,不属于别人。他可以穿过河边的热带雨林,越过干燥的桦树林,沿着自己踩出来的路,一路攀行,搜索猎物。夜幕降临之后,他就停在自己建立的舒适营地之中。这种生活并不容易,他所有的收获总和艰难形影不离。时常有的贫乏季节和坏运气以及从陷阱里跑掉的猎物,让人疲惫失望,多日独自在密林的云雾之中出没,会用去他大量的时间,而且未必就真有回报。
后来,他定居在那里,开始种植农作物,养鸡。他不再狩猎。他跟我说:“说起死亡,从出生开始我们身边就会有一个保护神。这个保护神会陪伴你一生,在你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保护你,随着你渐渐长大并开始狩猎、杀生,他会把你所做的一切都记下,会让你有所报应,这就像喇嘛所说的因果报应。我害怕死去,最害怕的便是死亡。因为我觉得我造了很多孽,虽然我知道杀生是不好的,但为了活着,这不可避免。”我听得出来他的担忧,可是这有时候显得自相矛盾。
矛盾,从来就一直存在,爷爷平措也不能例外。
墨脱,产大名鼎鼎的石锅,我买过。这种石锅其实是一种软石。人们用这种软石为基做出石锅形状,然后用这种锅煮饭,炖土鸡,加上山那边鲁朗产的手掌参,是美味。回程,再过嘎隆拉,它就立在扎墨公路24千米处。这座山,让波密和墨脱河谷变成了两种天气,它是山南北两侧的天气分界岭。从前这座山并没有隧道,人们只能从垭口来回翻越,上山前,要祈祷天气良好,要祈祷大车不多,要不然跟在大车后面将慢行如牛,因为路太窄了,根本没办法超车。我一直非常喜欢这座山,所以去过好多次。山并不算高,山前山后,景色因气候而截然不同。梯次渐变的植被,在南侧变得更加丰富,直至雨林。在这里,四季雨雪充沛,山顶下雪,山下落雨。低海拔海洋性冰川,就在山顶。冰川已经逐年后退,气象专家说西藏每十年上升0.4摄氏度。2008年,我与躲避奥运会逃离北京的小咸弟弟相约同行去墨脱。在过此山的路途中,我们停下来野炊的时候,寻觅了一处瀑布,在那里我们自制了午餐,餐后还坐在瀑布边啃着用冰水浸过的林芝西瓜。
我们总是希望去到的地方还有探险,还有猎奇,可在这里生活的人,因为交通困难而必须面对日常生活上的不便。这是我们这些好奇的过客根本没有来得及体验也来不及想象的。修路的同时,景观事物都会有些变化,是的,但我依然希望给那片大山背后的墨脱人一条稍微通畅的道路,他们太需要这条道路和外界保持联系,无论是物质抑或是情感,都需要。 西藏,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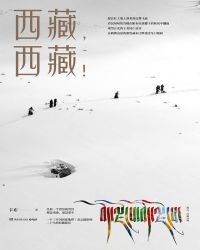
![师尊今天OOC了吗[穿书]](/uploads/novel/20210406/8a218042c0d0fd41a5f7bbb7381e69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