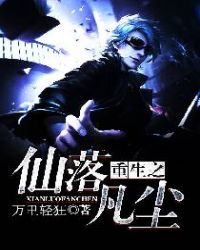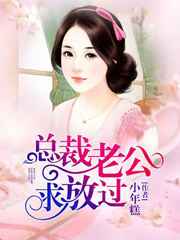翻开地图,有一片雪山环绕的高原傲然于世,这就是被人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片表面看似荒原的厚土下不知隐藏了多少人类未知的秘密。以至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不间断地闯入这片神奇的土地而不能自拔。尤其是西方工业化后,一批传教士、旅行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接着一个试图闯入这片“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染指的最后净土”,为了什么?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中认为:“西方人追求一种梦想”“西方人是梦想家,但他们不会对其梦感到满意”,于是必须归化信徒、签订条约、收集标本、验证理论、著书立说,人一批又一批地出现,因为“西藏激发产生了许多梦想”。物质的梦想是满地金子、精神的梦想是香格里拉、信仰的梦想是约翰的基督国 。如今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个耸立于地球“第三极”的雪域高原早已脱离了封闭的过去,迈入现代化的轨道。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强烈而神秘的诱惑依然持续不断。我身边无数国内外的朋友依然无限向往这片高原,一个接着一个走进高原、走进西藏。
卡布就是其中一位,他持久地做着这样的“白日梦”,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用脚步写下了他的“西藏梦”,这就是《西藏,西藏!》。这本书正如卡布所言:他如实地把自己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的点滴记录下来,让所有人能客观感受他的那些曾经,那些他曾经用了二十年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历险以及感动。其实卡布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影像记录,我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在那里看到了他正在剪辑制作中的纪录片,当画面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天文台里,我正在观看着宇宙里游动的星海,漫无边际;喜马拉雅山脉在漫天的星海下的画面中犹如一座座冰川在悠扬激荡的音乐声中缓缓移动;远处一群喇嘛的红色阴影由远至近,由小变大,渐渐走进一座古老的寺庙,这时我的眼前突然被一片红色覆盖,是他们在反反复复围绕一个彩色的沙盘忙忙碌碌。影片的主题由此显现——吉廓。
卡布说:“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西藏,我会用:吉廓。”而这个词正是佛教名词坛城的藏语一词的音译,意为“中围”。意思就是用某种东西筑起一个土坛或沙坛,把佛教观修的诸本尊佛安置其中做祭供。据说是藏传佛教密宗修“秘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而建。这使我想起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时用现代化枪炮攻克藏军营地,大肆屠杀藏军后发现一个帐篷里有几个喇嘛居然仍然在严肃认真地举行着“打败”英军的宗教仪式,从战争的角度看这个仪式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但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他们相信一座土坛城可以防止魔鬼入侵,一次只有几个喇嘛进行的宗教仪式可以阻挡手持犀利武器的英军部队入侵。这就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要理解这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就必须了解西藏解放的过去。在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社会,最高的利益、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宗教,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总之在这个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教育,甚至艺术等都是为了宗教这个核心利益而存在。歌舞、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等,也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服务宗教为目的。而脱离宗教的民俗艺术是农奴自娱自乐的形式,登不了“大雅之堂”。比如,过去的民间戏剧、热巴舞等,最早是为了挣口饭吃,没有固定的舞台。优秀的雕塑家、绘画家,大多数没有社会地位,创作最精美艺术品的银匠、铁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地位非常低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一切创新的文化、现代的文化、先进的文化都很难传播和生根发芽。
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西藏曾经有过一个英文学校,但很快就被关闭了。一个欧洲留学回来的藏族人曾经想开展一些略有民主思想的活动,最后也被关起来了。同样,外来的基督教也被排斥。迈向民主进步的哪怕是很小的尝试都会被无情地扼杀。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下,把政治与宗教捆绑在一起,使西藏文化逐渐失去开放性,也失去了迈向现代化的机会。正如《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所言:传统的西藏社会以宗教为最高利益,寺院集团是代表和维护这个利益的强大堡垒,“因此,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扰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寺院集团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保守派盟友一再阻扰迈向现代化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伐。” 因此西藏现代史上(1913-1951)试图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多起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以宗教为中心或宗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文化阻碍了西藏现代化进程,甚至使整个西藏社会文化停滞不前。与此相适应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重约束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西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今天的西藏各族人民早已迈上了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之路,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吉廓”依然高高耸立。每年成千上万的藏族居民在享受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高高兴兴地在以大昭寺为核心的林廓路上行进,围绕他们认为的宇宙中心冈底斯山不间断地徒步行走。这些行为不是为了比赛或锻炼身体,而是为了心中难以磨灭的“吉廓”。
卡布,是一个出生于我们康区理塘的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仙女在牵引着他,并围绕着他心中的圣地雪域盘旋不止,舒适的城市生活并没能留住他的脚步和心,于是在遥远的阿里、那曲、山南、昌都、日喀则、林芝,甚至无人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都留下了他的田野足迹和珍贵记录,他为我们这些每天进出教学楼的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提供了美好而珍贵的影像,同时他居然还以人类学方式进行了大量翔实的影像和文字调查。如果说视频和照片能够记录一个人的心灵轨迹,那么,这本图文并茂的图书正是记录了卡布曾用人生中最激情和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追逐梦想的历程。其结果是为我们今天这个物欲横行的时代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格勒(格勒,藏族,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总干事、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负责人。担任过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多次应邀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联合国中国项目的人类学和藏学咨询顾问。撰写并出版《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Collected Works on Tibetology and Anthropology(《藏学、人类学论文集》)等多部学术专著。与他人合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等10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几点思考》《中国西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演讲稿》等100多篇中文学术论文和“The - Washu - Sethare - A Nomadic Community of Eastern Tibet”“The Tibetan Plateau - One of the Homes of Early Man”等10多篇英文论文。他还出版了学术随笔《月亮西沉的地方——一个人类学家在阿里无人区的行走沉吟》等散文类作品。1991年1月,获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1992年10月,作为“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表彰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4月,以学术身份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以及金质“五一”劳动奖章一枚。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手。)
2019年6月7日 西藏,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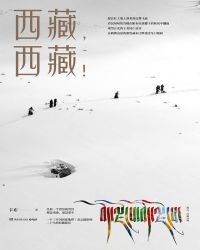
![[综]名震江湖](/uploads/novel/20210406/7b2f2969b0f4ac11baef6edf53714c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