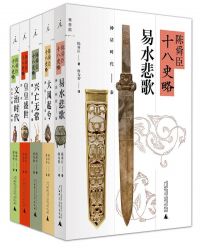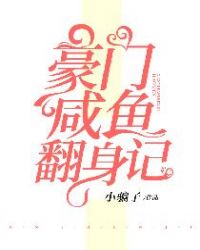一四、明月何时照我还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四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的“新法”之途并不平坦。
“不晓得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皇太后高氏蹙着眉头,对众侍女和太监道。
——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差,去年的收入又比前年差。这不是一年不如一年吗?是不是政治有了问题呢?
皇太后的娘家人,不久向她如此诉说。
——哀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皇上尚年幼还另当别论,但皇上已经成人,有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应该看看新法的效果如何啊!
皇太后说这些话,总算安抚了娘家的人。她对公私之间是拿捏得很有分寸的。但对新法的不满,也从另外的管道传进她的耳里。
“街上的人莫不摇头叹息,因为生意越来越不好……”
太监向上翻弄眼珠,一边察看皇太后的神色一边说。
生意——生意式微不只是街上的商人,连太监们的生意也与日俱下。
做宫廷生意的商人,向宫廷交货时,一定要贿赂太监,因为宫廷采购物品的决定权,全为太监所掌握。
——宫廷使用的蜡烛,希望向我们独家采购。请多关照。
大商人会向太监做此打点,太监也当然因此从中牟取好处。
宫廷和政府采购物资,全都透过称之为“行”的大商人联合组织,这个组织垄断一切这类物资的供应事宜。
被王安石作为新法之一环而实施的“市易法”,对“行”的独占带来极大的打击。不透过此行而分别向个体商人采购物资,这是市易法的规定。此法目的在于排除市场独占,以价格竞争谋取采购的合理化。过去因独占而垄断利益的大商人,因而蒙受极大的不利。
此外,市易法规定政府可以低利贷款给商人,订定这个规定的目的在于救济小商人。
——国家怎么可以办理放款业务呢?
如此的诘难之声又甚嚣尘上,情形和实施青苗法时一样。然而,青苗法无论如何是以振兴农业为名目,市易法则纯粹为商人谋取便宜,因此,诘难之声更为炽烈。重农轻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据说,王安石和商人有所勾结。老百姓对市易法批评得很厉害……”
太监如此煽动皇太后。
宫廷女性和外界接触的管道只有太监和娘家,皇太后透过这两个管道听到的都是对王安石的恶评。
“到目前为止,被认为坏蛋的是王安石。可是,谁知道人民的怨嗟什么时候会转到起用王安石的朝廷头上呢?”
听到这句话时,皇太后开始担忧起来。
“这样的事情非防患未然不可——”
她因此陷入沉思中。
小商人因低利融资而变得基础稳固,国家税收自然会增加,但这要经过一段时期后才看得出来,眼前看到的只是大商人生意日趋低落的现象。
因市易法抬头的新兴商人,开始涉足到既成财阀以“行”之名为武器所独占的各方面了。新兴商人是以竞争力被经济官僚承认的,因之甚少有必要与太监接触。
太监因财务被断而憎恨新法,对于推动新法的王安石更是憎恶到了极点。
“你说商人都落魄了,是不是?”
皇太后特别询问对她做有关报告的太监。
“是的,一点没错。”
“听说地方名族全都没落了……”
皇太后略为歪了头。
“所有的老百姓都闹穷,当然,国家也闹穷。这是值得忧虑的事,奴才无日不为国家的将来担忧……”
太监跪伏下来,颤抖着双肩表示其忧国之情。
“哀家认为你的忧国之心值得嘉许……”
皇太后已盈泪欲滴了。
她的大地主娘家收入降低,大商人的收益也越来越少,这些都是事实,但太监却以“闹穷”这个夸张之词形容,是另有居心的。实施新法后,贫农复苏,小商人也开始致富,这些事情太监却没有向皇太后报告。
“哀家会想办法的,”皇太后道,“为了国家的前途,哀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卿到江宁(南京)休养一段时期吧!”
神宗召来王安石如此命令,这句话不外乎是宣告将他左迁为江宁知府。这是熙宁七年(1074)的事。
王安石垂头默然不语。
“国内目前的状况如何,相信卿了然于胸……”
神宗以尴尬的表情说了这句话。
“是,臣知道。”
除了皇太后以外,神宗皇后的娘家也对新法表示不满。
连年旱魃,对王安石而言是一项不幸。
——歉收的原因完全在于实施新法!
反对派如此攻击。
这个时候,辽对宋表现出强硬态度。辽是因为看到宋受困于旱害而一筹莫展,所以才倨傲起来的。针对这一点,有一派人士以“都是王安石措施不对所致”大兴问罪之师。神宗所说的“状况”,即是指这一切而言,王安石对这些状况当然知道得很清楚。
(皇上无力驳回外戚和宦官的压力,未免也太窝囊……)
王安石心里如此想,而神宗也大致猜出王安石心里想的是什么。
“休养一段时期吧,这对卿有好处的……”神宗如此安慰道。
“叩谢皇上的关怀。……只是,新法要经过一段岁月才会奏效,现在却要遽然中断,这一点实在令臣耿耿于怀。”王安石垂头道。
“不,绝不会有中断之事。”神宗斩钉截铁地说,“卿走后,朕已决定指派韩绛和吕惠卿负责日后的事情。”
韩绛和吕惠卿都是新法派的政治人物。皇帝说要起用这两个人,等于是宣布今后仍要以继续推动新法为施政方针。
“那……”
“卿是新法的创建者,而大家对卿的排斥程度,相信卿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要说卿,连新法本身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卿难道不珍视新法吗?”
“臣视新法如己子……”
“为了要推动新法,卿更应该暂时离开朝廷。朕一定会设法,尽早召卿回来。望卿能相信朕说的话。”
神宗果然很快就实现了他的诺言。被左迁至江宁的王安石,来年就复职为宰相了。
——速来京。
接到这个消息时,王安石并未喜形于色。王安石在江宁期间,时常听到有关朝廷的情报。于他走后,新法派依然当权,但二流政客所推动的政治,毕竟欠缺魄力。
更要命的是,新法派内部起了内讧。要是王安石在位,一定压得住阵脚,但要王安石以外的人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事。原来吕惠卿是权势欲望极强的人,性格上也绝难与同僚协调。
(我那样做,对吗?)
除了新法派内讧使王安石失望外,他更时而有这样的想法。他对新法本身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坚定信念了。
“基本上应该没错才对……”
他多次于泛舟江宁秦淮河时,呢喃着这句话。把心里想的事情说出来,是为了明白地告诉自己。他的信念已动摇到非如此做不可的程度了。
(改革科举方式——我那样做,对吗?)
这也是他对自己施政的疑问之一。他过去废止了向来作为科举考试项目之一的诗赋吟作。来到江宁后,他开始对这一点耿耿于怀。
诗歌之类的游戏文字,对参与国政的官僚而言是不必要的东西。虽然王安石本身是个优秀的诗人,但以新法政治家自许的他,在这个视点之下决定将诗赋吟作从考试科目剔除,只以经义和论策为试题范围。
(政治之根本是人,形诸文字目的在于表现人性,由这个观点而论时,我那样的改革不是错了吗?)
在开封忙于政务时没有想到的疑问,现在却一一涌入脑海。改革科举方式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在江宁居住的这段时期,王安石产生让人民悠然自得的生活才是最理想形态的想法。所以在接到朝廷要他回来的通知时,他并没有狂喜。
王安石是临江(江西省)人,因为父亲是地方官,所以曾经跟随父亲辗转各地。于他十九岁时去世的父亲,最后的任地就是江宁。
(如果能在此地度过余生,那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时候的他已有退隐的念头。
由江宁到国都开封,要在长江和运河上做水上之旅,坐在船上的王安石,一点没有凯归的心情。由长江转入运河处是一个叫瓜州的地方,来到此地时,他怀念起江宁钟山,并且幻想他日回归此地的情形,他此时的心情被咏在题为《泊船瓜州》诗中:
京口瓜州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复出后的王安石没有往年的霸气自是当然之事。复出的翌年,寄望甚深的长子王雱夭折,他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
新法派内部的斗争使他失望,而及进士第的爱子之死,使他深深感到人生无常,他因而请辞,并且获准。
“新法已上轨道,而臣垂垂老矣……”
说垂垂老矣的王安石,这时五十六岁。
于他辞职后,政权依旧由新法派掌握,但新法很难称得上已上轨道。新法派成员中的一大部分,并不是对国政改革怀有满腔热情,而是因为新法派掌握政权才投入此派的。
格调降低的新法派政治,变得党派性格极强,因此逐渐失去魅力。
王安石退隐九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十岁的皇太子哲宗即位。成为皇太后的高氏居摄政之位,她是彻底厌恶新法的人。
政界立刻刮起一阵飓风。
“可以担任国政的人,除了司马光以外不做第二人想,立刻派人请他进宫吧!”
这是成为摄政的高氏发出的第一道命令。
反对新法而离开政界的司马光,后来在洛阳埋首编著《资治通鉴》。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的他,仍然从洛阳写信给王安石,述说“不废止新法,国家定将衰微”的战斗性反对言论。
新法以救济贫农和小商人、增强综合性国富为目标,司马光却以“穷人皆懒惰”为理论依据,强调国家没有必要救济他们。这无疑是否定社会福祉的理论。
国家贷款给穷人时,懒惰而不努力工作的他们,最后一定无力偿还借款,这个负担终究会落到富者的肩上,结果是,富者也变成穷人;换言之,新法令使全国人民变成穷人,因此,非立即废止不可——这是司马光的论点。
从洛阳赶到国都开封的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择善固执的他,将新法派人士从朝廷赶出,并且逐一废止新法。
如同王安石向神宗申述的,新法必须经过长时期才会见效,例如订定五年计划,而且这也要经过长时间不断地推展才能有成果。
神宗死后一年,眼看着自己奠定基础的新法迅速崩溃的王安石,在江宁钟山与世长辞;五个月后,甫就任为宰相的司马光也去世。
王安石是新法领袖,而司马光则为反新法——即所谓的旧法——代表,两派领袖人物一前一后辞世了。之后,新法派和旧法派剩下的都是不入流的角色。
虽然互相展开激烈论战,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却有超越政治的友情存在,所以,他们之间有如前所述的书信往来。两巨头亡后,新法、旧法的对立,演变成格调低劣的派系斗争。
哲宗即位八年后,皇太后高氏殁故,十八岁的哲宗因而开始亲政。酷似其父的哲宗,和父皇一样对国政改革有极大热情,年轻的他对执政党旧法的作风有甚多不满。
“朕要继承先帝遗志。”
哲宗遂决定再实行新法。
朝中旧法派人士当然悉数被赶走。
政治方针一举被推翻。在这个情形之下,当然无法推动一贯的长期政策,这对国政而言是一大损失,现实上的情形是,由于新法、旧法两派之争,政治开始衰败了。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