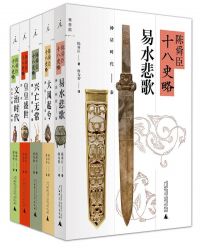一五、青山一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五
青山一发
在太皇太后摄政下执政了八年的旧法派政权,因哲宗亲政而溃灭。但哲宗施行的新法政治,为时仅仅七年。于元祐八年(1093)开始亲政的他,到元符三年(1100)正月就去世了。
哲宗享年二十五岁,未生有皇子。
神宗皇后尚氏此时尚健在,由于事关皇嗣事宜,应该以她的发言分量为最重。然而尚氏虽居皇太后之位,但哲宗并不是她亲生的。尚氏根本未生有孩子。哲宗的生母是一个名叫朱氏的宫女。
由于哲宗并无嗣子,皇嗣必须从他的兄弟中选出来。
“必须立皇弟当新帝,不知选择何人为宜?”尚氏哭泣着对重臣垂问。
当时的宰相是新法派的章惇。
“依长幼之序应该是申王,而依礼律则应该为先帝之同母弟简王……”
宰相毕恭毕敬地回答,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尚氏尖锐的声音打断:
“礼律……此礼律是指何国礼律而言?难道是指大宋礼律吗?”
皇族女性绝不在臣下面前露脸,接见臣下时一定要在前面垂下竹帘,因此,皇太后摄政之事被称为“垂帘政治”。由于皇帝崩殂,皇太后依礼要放声哭泣。但她并没有流泪,因为皇帝并不是她亲生的儿子,而有没有流泪,透过竹帘是看不到的。
糟糕……
宰相章惇为自己说的话深深懊悔。
皇太后尚氏是神宗皇帝的正室,虽然她没有生子,但,依据大宋——不,依据中华传统礼律,侧室朱氏所生的哲宗即位后,她还是以“正母”身份受到皇帝的尊崇。“哲宗同母弟”指朱氏所生的简王而言,倘若如此,朱氏等于受到特殊礼遇。
“宰相岂可谓同母弟之语?”
尚氏的声音更加高昂起来。
“臣不胜惶恐。”
宰相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神宗皇帝诸子,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
“臣不胜惶恐。”
宰相又说了同样的话。
“哀家说的话不对吗?”
尚氏特别追问。
“太后所言一点不差。”
宰相回答。
“相信宰相不敢否定这一点,已故皇上乃是以神宗皇帝皇嗣的身份即位。神宗皇帝之子岂可有尊卑之别?”
倘若正妻尚氏生有子嗣,与其他侧室所生的孩子当然有尊卑之差,但神宗的孩子全都是正室以外的女人所生,因此,其间应该无任何差别才对。
尚氏的观点是“哲宗乃神宗之子”,而宰相章惇不经心口出礼律之语,乃是就“哲宗乃大宋皇帝”的观点而言。这个论争应以尚氏较站得住脚。
哲宗因为是神宗的儿子,所以才成为皇帝,也就是说,哲宗乃是以尚氏为“正母”的皇嗣。
——其他的儿子也全都是我的儿子。
这样的说法绝对言之成理。
“依此而论,应该立申王才对。但事情也不能这样做,是吧?”尚氏道。
“是的,太后所言甚是。”
“申王不可能当皇帝。如此一来,不是该立申王下面一个弟弟吗?”
长子哲宗的下面一个弟弟是申王。但以申王为新帝,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任何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申王因病失明,不能读奏文、也不会在诏敕上署名的盲人是无法就皇帝之位的。
如果依顺序而言,次子申王之下,就要轮到三子端王赵佶。
章惇心想:
糟糕……
因为在性格上最不适合当皇帝的,正是这个端王,这不是章惇一个人的想法,而几近是全体廷臣的意见。端王赵佶对书画有杰出才华,诗文也颇有造诣。他有一流艺术家的天分,但这并不能视为做帝王的资质。由端王就帝位,他的才华毋宁将产生负面效果。
(任何一个都可以,唯独端王绝对不能当皇帝……)
由于宰相有这个想法,所以,皇太后垂问时,他有意排除在序列上居最优势的端王,而以礼律为由推举简王。
结果是,他据以为由的礼律产生反效果,惹来尚氏的反击。他其实应该由正面以皇帝的资质作为论点,推举简王才对。以先帝之同母弟——即朱氏之子为由,可以说是他做法上的失败。
由于有过前述经纬,结果决定由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宋后来等于因徽宗而灭亡,因此,这次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宿命得令人啼笑皆非。
徽宗即位,尚氏就任为摄政。
(虽然新帝为人轻佻,但有尚氏摄政,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虽然尚氏是个女流,廷臣却十分信赖她,由此可见其能力之强。尚氏主持政治的期间并不长,治绩却非常值得赞许。
新法与旧法之争,于王安石及司马光两巨头死后变得更为激烈,层次又降低许多。
旧法派复活后,新法派及其相关人员全被逐出政界;而当新法派取得实权,旧法派则悉数受到弹压。依据石刻遗训,对士大夫不得因言论而处以死刑,而仅次于死刑的重罚是流刑。
大诗人兼杰出书法家苏轼,于新法时代曾因讥讽新法,被捕系狱。那是因为苏轼在致弟弟苏辙的诗中有“读书万卷不读律”之句,被认为有问题。
这句诗的意思是:你有极大才华,却不得发迹,是因为你虽然读书万卷,却没有读到法律。……当时的科举考试已经不考诗赋题目,重视的是论策。论策必须要有法律基础,因此,不爱读法律的人不可能发迹——苏轼是因这句诗系狱的。
出狱后,苏轼被调至湖北黄州。虽然苏轼有黄州团练副使的头衔,实质上这是以左迁为名的流刑。在黄州的苏轼,靠耕作荒地过活。由于耕地在东方坡上,因此,他从此以“东坡”为号。比起苏轼本名,苏东坡之号更广为人知。
神宗死,高氏摄政,旧法时代来临,苏轼又被叫回中央,历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高氏死后哲宗亲政,顿时成为新法的天下,苏轼再度被流放广东英州,被剥夺所有的官职,最后流放至更远的惠州。
由于他是旧法时代的阁僚,因而受到的处分相当严厉,政府并未因流放至惠州就放过他。不久,他又被移至儋州。当时的儋州,是以黎族为主要居民的海南岛。
在海南岛的生活,对年逾六十的他来说,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他的文学精神却因此逆境而更加精进。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被称为“东坡海外之文章”,为后世所称颂。
虽然没有处以死刑,但对反对派的弹压未免也过于苛酷;苛酷的弹压,当然会招来报复。执行国家政治的士大夫阶层就这么一分为二,相互露出赤裸裸的憎恶感情,不断重复抗争。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希望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彼此憎恨,双方应和解。不然,国家会灭亡啊!”
垂帘后的尚氏,传达给大臣这个意旨。
“如何进行和解呢?”
宰相诚惶诚恐地问道。
“对国家有功而被流放或左迁的人甚多。以诗文著名的苏轼年迈而在海南岛受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残酷的事情不可再有。如此下去,一定会被后世史家责难的……苏轼今年几岁了?”
“好像六十五了……”
“卿不认为这样对待他过于残酷吗?”
“太后所言甚是。”
“哀家不是只指苏轼而言。凡是以反对新法为由而被流放的人,应该全数赦免才对。”
“可是……”
宰相露出犹疑的神色,这是因为他没有听懂摄政尚氏的话是否意指要恢复旧法而言。
“哀家并没有意思要改变现在的政治形态,只期望大家能和解罢了。”
“遵命。”
奉了皇太后懿旨的新法政府,当然不敢不赦免旧法派人士。
在海南岛的苏轼,没有一天不眺望海洋。六十五岁的他,思乡之情极为强烈,虽然故乡是四川,但国都开封、担任过知事的杭州以及被左迁之地黄州东坡,都是他怀念的地方。
“在我有生之年,还有重踏大陆故土的机会吗?”
他常以这句话问熟人,实际上,他对这一点已经死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赦免消息传来。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苏轼再三询问使者后,反复读了通知文书,他最后甚至用手抚摸起这张公文书来。
“这是真的事情!……我不是在做梦!”
杳杳天低鹘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
看起来像是一根头发的陆地——中原就在那上面。这是苏轼于在海南岛北岸澄迈驿的通潮阁所做的诗中之一句。
虽然赦免内容只是将他从海南岛移至廉州(广西),但因为这已是五月间的事,因此,苏轼当然知道推动新法的哲宗于正月间去世,后来改为垂帘政治之事。
中国的人事异动,虽然偶有例外,但左迁一般情形以越调越差为特征。苏轼的情形正是如此,辗转被调英州、惠州、海南岛等地,情形越来越差。恢复的情形亦复如此,五月间被调至廉州,八月间被调永州,逐渐接近国都后,于十一月间复职为朝奉郎。至此,他已完全恢复名誉了,与此同时,他开始提举(管辖)在成都的玉局观,这就是前述的“祠禄”。观(道教寺院)并没有什么麻烦工作,他只以这个名目领取薪俸,可以说是一种恩给制度。
苏轼于这一年——元符三年(1100)北上,于翌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间抵达江南。就在南京附近,苏轼病倒。
虽然如此,因为已是长江近边之地,所以他改搭船只行旅。
在由广西廉州前往湖北永州途中,苏轼在广州落脚。
“能够回来,太好啦!多年的辛苦我实在替你委屈。”
故友广州提刑使(法院院长)王进叔热烈欢迎他。
“我是能随遇而安的人,所以没受什么苦啊!”
苏轼适应性极强是事实,不过,“没受什么苦”倒不是由衷之言。
“那是环境峻烈的时代……希望你能谅解……当时我……”
王进叔露出难于启齿的表情。
苏轼被左迁经过广州时,王进叔未能为他做什么。
在这之前,苏轼被流放惠州时,该地地方官曾经对高名文士且为往年大官的他颇为优遇。但这名地方官却因此受到处罚,新法派的报复心何等执拗,由此可见。由于惠州地方官被处罚之事不久前才发生,因此,苏轼路过广州时,王进叔连和他会晤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那个时候……哈!当时的情形如何,你我都知道。换成是我,我也不敢前去会晤在被押送途中的危险人物啊!”苏轼道。
在广州参观王进叔所收藏的书画时,苏轼在画人赵昌(988—1022)所绘以山茶为题的画上,题了如下的七言绝句:
游蜂掠尽粉丝黄,
落蕊犹收蜜露香。
春风待得几枝在,
年来杀菽有飞霜。
蜜蜂掠尽黄色的花粉,将落蕊上的蜜露全都吸尽——这个诗句暗指新法派对旧法派报复之峻烈,是不难想象的事。
“春风”当然是指尚太后因哲宗之死而实施的“和解”政策。在未等到尚太后摄政这春风吹到之前就凄惨枯死的树枝何其多。苏轼弟子秦观就被流放到海南岛的雷州,且在该地丧命。等到春风吹至的树枝有多少呢?——苏轼以此诗表达了他的感慨。
苏轼以“飞霜”譬喻这数十年来的政争,慨叹它使藏有无限可能的无数菽实枯死了。
苏轼是耐到春风吹至为数不多的枝丫之一。但他却未能回到故乡四川,也未能抵达国都开封。他因病情恶化而在江苏常州结束了六十六年的生涯。
虽然如此,比起在流配之地死去的人,苏轼能重踏其以“青山一发”形容的大陆故土,也算是幸福了。倘若苏轼活着进入中原,余生也未必幸福,因为于他去世的这一年,推动和解的尚太后殁故,在徽宗亲政之下,天下又再度归新法派掌握了。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