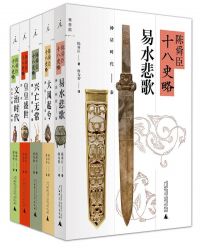一三、新法开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三
新法开张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
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
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卓越,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
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感觉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
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作风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的。”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
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
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
“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
“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官僚。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官僚。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会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
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
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向他询问。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首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之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
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
(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给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给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发表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是,他们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之事。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悖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劳动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
——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念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态度,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愈演愈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