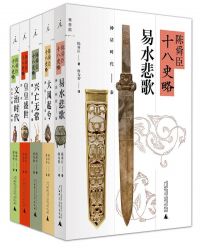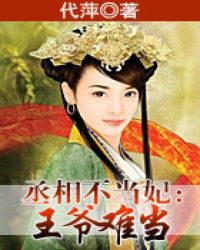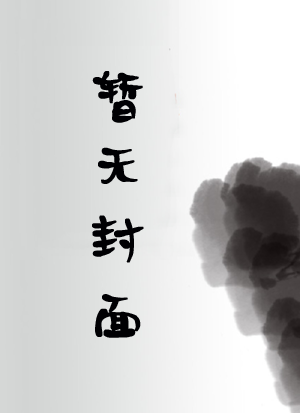一七、海东青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七
海东青
徽宗对书画有极大的兴趣,他本身就是一流的艺术家。此外,他非常喜欢夜游,在这方面留下不少轶事。
虽然如此,他也不是完全置国家大事于不顾。
收复成为辽之领土的燕云十六州失地,是宋最大的国家目标——这一点他当然知道得很清楚。
然而建国一百五十年以来,失地终未收复。连在被称为最盛时期的真宗、仁宗的时代都没有实现,因此,徽宗对收复失地一事已经死心了,他只会以艺术家惯有的心态做这样的幻想:
(会不会有异想天开的妙策出现呢?……)
“禀报皇上一件重要消息……”
一天,宦官童贯压低声音对徽宗道。
“有什么事值得如此神秘兮兮的……?”
“奴才从辽带一个人来……”
蔡京和童贯之间的同盟已有成果。童贯是以副使身份被派遣前往辽刚回来。
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宋虽然从不曾对收复失地之事死心,表面上却时常与辽交换使节,两国要接洽的事务,包括岁币的运输方法在内,还算不少。
与辽的交涉是国家的一级要事,童贯被任命为这个交涉团的副使,对宦官而言是破格的晋升。
“你说的是什么人?”
“这个人名叫马植。他对东方的情况知道得非常详细。”
“东方……?”
徽宗一时弄不清楚童贯说的是什么。
“由于燕云十六州为辽所占据,因此,我们宋对位于该地之东方的地区相当陌生。所以,奴才趁这次前往辽的机会,尽可能地调查了有关东方的事情。”
“你是不是在研究东方历史?”
“不是历史,奴才关心的是东方的现实情形。……皇上不能忘记东方是在辽的背后这一点啊!”
童贯一边说这句话,一边窥看徽宗的表情。徽宗点了一下头。虽然是放荡的失格皇帝,但他是头脑非常灵敏的人。他立刻察知童贯说的是什么了。
对宿敌辽之背后的情况,宋当然需要注目。东方有新动向的情报,近来已点点滴滴地传来。
童贯出使辽归来是政和元年(1111)的事。
东北边境是通古斯系女真族的居住地带。他们是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民族,将狐、貂、水貂、水獭等皮货出售给汉族或契丹族。此外,他们在黑龙江及松花江等处从事渔业,非常擅长于采收天然珍珠。汉民族视为最佳药材、珍而重之的人参也在他们的生活地域采集得到。
女真族的猎获物不只在地上和河中,连空中也有。这是被称为“海东青”的老鹰。喜欢鹰猎的契丹族需要老鹰,因此必须活捉——这是难上加难的事。
女真族当然在契丹族辽的支配之下。居住在平地、很早就与汉族或契丹族接触、以农耕或养猪为业的女真族,被称做“熟女真”,意思是“稍微文明化的女真族”;与之相对,居住在山地森林等内地、未丧失刚毅野性的同一民族,被叫做“生女真”。
对人使用“生”、“熟”的形容词,实在是一件欠缺礼貌的事情。日本曾经也以“蕃人”称呼居住台湾山地的高山族,并且将之区别为“熟蕃”和“生蕃”。
辽似乎不把生女真当做人看待,而视为动物,并要求他们捕猎老鹰以作为贡品。
要活捉有“海东之鹘”之称的名鹰,必须攀登断崖绝壁,下到千仞之谷,过程可谓苦不堪言;据说,为了要捕捉一只老鹰,常有几个人丧命之事。
然而辽的要求非常严峻。辽官员以捕鹰使为名前来监督,并且以严刑峻法对待生女真族人。
虽然辽不把他们当做人看,但生女真也是货真价实的人,他们都有人的感情。
他们因被虐待而憎恨对方。受压迫时会反抗是人的本能。
——他们凭什么可以虐待我们!?
生女真族人当然会有这个想法。
——这是因为我们不团结。就个人的力气来说,我们比契丹人强许多。但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才会被他们任意宰割……
他们得到的当然是这个结论。
——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才对!
小小集团围杀辽国捕鹰使的事件于是发生。
女真族——尤其是生女真——再也不乖顺,辽好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如何才好?”徽宗问道。
“我们应该支持女真族团结起来。他们没有文字,也不能确实掌握四周环境的状况。他们只隐约听说西方中原有一个以宋为名的大国,详细情形则完全不知晓。他们的仇敌是不断对他们榨取的契丹族之辽国。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和我们结盟,他们就能向辽报一箭之仇。”
童贯如此力说。
“你的意思是和女真族联手,以攻打辽吗?”
“是的。”
“可是,女真族是连文字都没有的未开化山地、森林之民,他们怎么配得上和我国结盟呢?说要威胁辽之背后,和他们结盟也产生不了多少力量吧?”
“在现状之下是产生不了多少力量。但,支持、培植他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辽之强敌的。”
“有这个可能吗?”
文化主义者徽宗,对文字都没有的野蛮人集团,似乎没有多大信心。
“东方有一句古语说‘女真盈万不可敌’。这个民族在本质上极为勇猛。让他们团结,并且使之有组织,一定会成为辽的一大威胁。”
童贯滔滔不绝道。他说的话一点没错。女真后来确实成为辽的一大威胁,终至攻灭辽;其力量最后甚至使宋灭亡。但此刻的徽宗和童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竟然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为女真所灭。
“能威胁辽到什么程度呢?”徽宗还是持着怀疑态度。
“不管怎样,我们对女真之事所知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熟知该地情形之人的口中听取有关辽之背后状况。奴才带回马植,用意就在于此。”
“好,朕改天引见这个马植就是啦!”
徽宗不那么感兴趣地道。不仅外交问题,对内政问题他也绝少有起劲的时候。
绘画、书法、文学、音乐以及女人——比起这些,政治多么的无聊!
在童贯多次催请之下,约莫一个月后,徽宗才接见马植。
马植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他除了马植之名外,有时候也以李良嗣为名。自称为辽之望族的他为何要使用化名,理由无人知道。
这个人后来为宋所重用,并且受赐宋之国姓,因此在《宋史》中以赵良嗣之名出现。
生为辽人的赵良嗣,对辽的国情当然了如指掌,此外,如童贯所推荐的,他对其背后之地的女真情形也非常清楚。
“女真日后会成为强大民族是笃定的。东方有一句古语说‘女真盈万不可敌’,现在好像出现了能纠合一万以上女真族的人。辽已产生了危机感。”
“辽产生危机感……!?”徽宗回问道。
对宋而言,辽是一面难于越过的峭壁。这座峭壁高高耸立在眼前,仰望它时,宋人无不感觉无力。现在听到这样的辽也有畏惧的对象,徽宗因而把膝盖往前挨近了。
“快告诉朕……这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呢?是不是蕃人酋长之一?”
“这个人虽然还没有成为酋长,但很快会成为一大力量,日后一定会割据该地。”
赵良嗣指的是生在女真族完颜部首长家的一个人物,名叫阿骨打。
“要成为一大力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女真族完颜部向来杰出领袖辈出。劾里钵、劾里钵的弟弟盈歌、劾里钵的长子乌雅束……现在是乌雅束的时代。这个人非常杰出,但他的弟弟阿骨打更是很有可能使女真成为巨大集团的核心人物。”
赵良嗣一向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话,这样的话有很大的说服力。
——女真完颜部有阿骨打其人。
据说,这在劾里钵首长的时期就已是远近驰名、无人不晓的事情。
完颜部是未丧失野性的生女真族,位居哈尔滨东南以按出虎水为名的松花江支流流域。
辽当然视这个地域为自己的势力圈。因此,他们派遣捕鹰使到此地,处处压迫生女真。完颜部族人当然都反辽。
这个部族之所以兴起,可能是因按出虎水乃沙金产地,因而得以以此为经济基础。
女真完颜部后来建立大王朝,支配了中国的北半部。这个王朝以“金”为名,一说正是因为按出虎水产沙金。
在完颜部首长之位由父亲、叔叔、哥哥每隔一段时间便交替的时期,阿骨打始终居于要职。这个部族急速地变得强大,完全是靠阿骨打的辅佐得宜——这是人们的定论。
赵良嗣对徽宗禀报的事情并不是他的先见之明,而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定评。
在哥哥就任首长时,阿骨打已经是部族内最大的实力者。他就任为联盟长是赵良嗣第一次晋谒徽宗之后的两年——公元1113年的事。
他们经由皮货、沙金、人参等女真族特产物的交易与文明社会接触,当然因而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们的交易对象不只是辽和汉族商人,和高丽的交易也相当频繁,因此,他们也从文明水平相当高的高丽受到文化影响。
女真族也有居住在高丽的部族。阿骨打为了将这些部族也收纳入自己的势力圈之内,多次与高丽交战。
结果,阿骨打赢了这场仗。
他已不再是小部族首长,而是在边境拥有宏大地域的支配者。
——野蛮人有什么好跩的!
——正因为他们是未开化民族,所以不知道文明世界的规律嘛!
——既然如此,我们就教他们文明人的规矩吧!
辽似已忘记自己契丹族过去也处于未开化状态之下,对在阿骨打率领之下的完颜部女真族摆出文明人的姿态来。
在辽的诸多压迫之下,新兴的完颜部女真族并没有屈服,这是因为成为首长的阿骨打,对辽的实态已经了解得很透彻。
阿骨打从前来采购人参、沙金、珍珠或皮货的商人口中,听到许多有关西方的事情。
“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真是个喜欢聊天的人。”
“他相当的和蔼可亲哩。”
“他很好客。像他那样的好人很少见。”
阿骨打成为商人们由衷称赞的对象。
他的确有机会就和商人聊个不停,但这是有企图的。他之所以和商人亲近,为的是要从他们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不过,一味探听会引起他们的疑窦,因此,他采取的方式是打开话匣子,好让商人主动把各方面的消息说出来。
阿骨打以此搜集有关辽的情报,并且测试其可信度,最后亲自下判断。
引爆——
阿骨打的意图在于此。
以火苗点燃民族心,使它燃烧着熊熊烈火——为要使女真族觉醒,必须要有这等轰轰烈烈的事件发生。然后侵攻辽的势力圈,以达成霸占他们土地的目的。
以往的女真族绝对不敢做这等胆大妄为之事,但阿骨打一点也不畏惧辽,因为他由商人口中知道,宋对燕云十六州有特别的感情。
即使女真族此刻在东北之地制造动乱,辽也不可能派大军到这个地区来,因为辽不能放松以北京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之防卫,充其量只会派来以威吓为目的的小部队吧?
辽不足为惧——做此判断的阿骨打,遂决定进兵攻打辽之领土的宁江州。这是他就联盟长之位的翌年公元1114年之事。
“海东青是在我们的领土天空翱翔的老鹰。我们为什么不自己使用海东青狩猎呢?让我们收回自己的土地和天空吧!”
阿骨打召集民众,做这样的演说。听到他这话的人莫不奋起。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