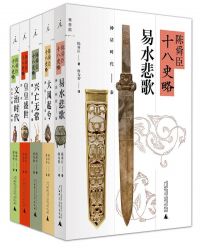一六、新法的堕落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六
新法的堕落
徽宗即位时已年满十八,因此,原本没有设置摄政的必要。
但由于他是在尚太后强力支持之下即位的,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容忍她的垂帘政治。尚太后便是亟思利用这个机会,对从自己丈夫神宗时代开始的新旧党争,以“和解”手段打上休止符。
苏轼得以由流配之地海南岛回到本土,在常州于临死之前以“来到此地,等于回到中原,我已此生无憾矣”之语表示满意,完全是靠尚太后所采取之政策的庇荫。然而,尚太后却于摄政一年之后就去世,年轻的徽宗则以父帝所创造之法为由,决定采用新法。
王安石改革国政的理想,已不见其原本的面目,现在呈现的纯粹是派系抗争的样貌。
徽宗时代的宫廷,居政治核心之位的是一个名叫蔡京的人物。这个人在小说《水浒传》中以坏蛋角色出现,是中国庶民家喻户晓的恶棍。不过,实际上他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暴虐人物。福建仙游县出身的蔡京,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以二十四岁进士及第,是非常有头脑的人。
他的弟弟蔡卞也于同一年成为进士。如《宋史》列传的纪年无误,蔡卞是于十三岁时考上进士的,所以,这人是个异才。
王安石看中蔡卞,因而将女儿许配给他。蔡氏兄弟凭其与王安石的姻亲关系,看似属于新法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单纯。实际上的情形是,弟弟蔡卞另当别论,哥哥蔡京既不属新法派,也不属旧法派,是骑墙派发迹主义者。对视发迹为最大愿望的人而言,理想或理念往往会成为累赘。蔡京就是能把这等累赘抛诸脑后、善于察看时势、充分发挥其嗅觉机能、以迎合当权者为能的人。
高氏摄政时期是旧法时代,司马光复出为宰相之事也已如前述。离开政坛达十五年之久、埋首于著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人。司马光复出时已高龄六十六,而且病魔缠身。
“除非将新法从根拔除,不然,这个国家将无药可救。”
这是司马光的口头禅。
“必须尽早废止使人民受苦的新法才行。”
每次听到司马光说这句话时,周遭的人莫不以同情的眼光看他。
(涑水先生真可怜。他是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所以急成这个样子的……)
由于司马光长年未就官职,周遭的人还不习惯以职名称呼他,因而以其出生地陕州夏县涑水乡之地名,称他为涑水先生。
涑水先生的确焦躁不安,他对生病一事当然也有自觉。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他,急着要把事情做完。
(在我撒手西归之前,非将新法彻底废止不可。)
这是他的决心。
使命感极重的司马光,对废止新法一事,要求负责官员在期限内完成任务。但再怎么急,要在短时间内革除实施十几年的新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光却认为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因而限期完成。他是个精神至上主义者。
这时候的知开封府(首都知事)是蔡京。他于新法时代被任官而晋升,但于新、旧法交替时期尚未就任要职,他也是因此而幸免于被流放的。
发迹主义者蔡京,早已嗅闻出时代趋势。
——对宰相司马光尽量表示忠诚。
这才是晋升之道。
司马光此时正在全国恢复新法派所废止的差役法。
——限定于五日内恢复差役制度。
司马光发出如此性急的命令。
被认定为一等户、二等户的有力富农——即“形势户”——以服务方式担任政府各项杂事,这是过去的差役法。新法则是实行以出钱免除此项差事的免役法。
蔡京拼命地干,结果顺利地使差役法恢复了。他遵照宰相的命令,于五日内完成了这件事。而在限期内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蔡京一个人。
“蔡京是个有才华的官员。日后推动新政治时,他将是很有用的人才。”
司马光颇为满足,在地属开封府的近边各县,政府诸多差事和杂役,全都是在形势户的负担之下完成,而且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差错。
——倘若人人奉法如君(蔡京),有何不可行之事?
《宋史》如此记录司马光于接到蔡京五日内将免役法改为差役法之报告时,用以嘉许蔡京业绩的话。
“如果人人像你这样努力……”
被内心焦急的司马光如此嘉许,可见蔡京是旧法的模范官僚。
虽然底下有具才能的官僚,但推行十数年的政策在短短五日内就被推翻,绝对不是健全的现象。相反的,事情因此也有随时爆发的可能。
到了哲宗亲政的新法时代,差役法以及所有的旧法政治,全都又恢复为神宗时代的新法。对将差役法恢复为原本在新法之下的免役法一事最为努力而且成效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蔡京。
废除免役法以及将之恢复——负责完成这些作业的,都是同一个人。
官僚原本就是遵奉上司的命令、忠实执行行政业务的人。依这个原则而论,蔡京确实是个模范官僚,但由其经历来看,他给人的是“无节操”的印象。
事实上,不只是给人的印象,蔡京无疑是个无节操的人。由于在徽宗的新法时期屡次担任宰相职,因此,他被归类为新法派领袖,但一点也没有弟媳妇之父王安石所持的高迈理想。
他喜欢游走宦界,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京也有过垮台的经验,曾遭御史陈次升等人之弹劾而被左迁至杭州。
——居住杭州,提举(管辖)洞霄宫(道教寺院)。
他当时接到的是这个命令。苏轼被赦免后,第一次担任的是道教寺院提举之事已如前述。事实上这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闲差。
“无所事事地过日子多无聊——”
在杭州的蔡京,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他为了解闷,开始过着鉴赏字画、写写文章的文人生活。
杭州、扬州、苏州等被称为淮南或江南的地方,从唐代起就非常富庶,是国家岁入的最大财源。安禄山造反最后归于失败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未能控制这个地区,这一点已如前述。
此地富豪比比皆是。他们凭其财力搜集许多字画,并且建造美轮美奂的宅邸和庭园。天下字画之泰半,大概皆已被江南搜集家所收藏吧?
蔡京对字画的鉴赏力颇高。
“帮我鉴定这个东西可以吗?……最好给我开一张证明……”
搜集家时常带着字画前来访问闲居的蔡京,因为著名字画在当时就有许多赝品出现坊间。
也就是说,蔡京是以鉴定字画为副业的。经中央高官且又是著名文人的他开具证明的作品,身价自然倍增。除了鉴定以外,蔡京本身也搜集字画。
就在这个时候,名叫童贯的宦官被派遣到杭州来。这个童贯也曾在《水浒传》登场,他虽然是宦官,却是个俊才,头脑非常灵敏。就政治感觉的灵敏度而言,这个人和蔡京诚可谓一时双璧。
童贯是以明金局供奉官身份前来杭州的。明金局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搜集美术品的机构。
徽宗是个艺术家气质的皇帝,不,他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皇帝做的字画古董搜集,规模之大当然不言可喻。
徽宗搜集的对象不止于字画古董,连名木、名石都包括在内。字画古董搜集得再多,体积上也不庞大,但名木、名石运输上的作业则相当艰巨。而真正的名木、名石,以产自远离国都开封的江南之地为多。举例来说,作为庭园石最珍视的是太湖石,此物必须从水底凿取,这个作业已经不简单,而长途运输更是难上加难。
童贯是为这个工作而来杭州并且得到蔡京这个助手的。
“在书画这方面,没有大人的协助,我就无法达成任务,请多帮忙。”
听到童贯说这句话时,蔡京做出相对的提案:
“要我帮忙没有问题,只是……我是从中央被逐出的人,其原因相信你也知道,这一点我到现在都耿耿于怀,我很不甘心受谗言而被迫离开中央。你是皇上身边的人,应该有机会替我雪冤才对。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蔡京和童贯等于缔结同盟。蔡京在搜集字画古董这件事上协助童贯,而童贯则利用自己在天子身边伺候的身份,为蔡京说情,让他能重返中央。
蔡京过去是宰相级人物,因此,只要能返回中央,一定会居于国政核心的地位。
(大人成为宰相时,务请多多关照……)
童贯不但央求蔡京在目前的工作上给予协助,更请求他将来也给予照顾。
勾结——事实上,蔡京和童贯的关系,以这个字眼来形容最为恰当。
不久之后,蔡京果然复出为相。童贯由一介供奉官成为监军,领枢密院事,持掌南宋兵权。
历代皇帝致力于推动新法,目的在于重建国家财政,新法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增加岁入。
一般皇帝会以增加的岁入谋求国家经济的健全化,而徽宗却不是一般的皇帝。他企图以增加的岁入搜集更多的字画、古董、珍花、名木、奇石等等,实际上,这正是宋帝国灭亡的原因。
徽宗应该以一介皇族身份过其艺术家生涯才对。他是不适合当皇帝的。
有了蔡京这个同好担任宰相职后,徽宗的搜集癖好更到了离谱的程度。
花石纲——
“纲”原本是总括货物的名称,但是宋朝现在称珍花、名木、奇石等为“花石”,并且称依朝廷命令运输花石之事为花石纲。
——舳舻相衔于淮(河)汴(河),号“花石纲”。
《宋史》有此记载。
粮食、军粮、民需品等国家重要物资,同样利用淮、汴水路,由南方输送至北方,不过“花石纲”优先于这一切。
为了运输花石纲,沿道住民每每被征用,这是在与西夏以及辽之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刻,在这个状态下,连运输军粮的船只都以花石纲为目的而被征用。
船运巨石时,成为障碍的民宅一律被拆除。成为宰相的蔡京,命令一个叫朱勔的人担任这项工作,因此,老百姓莫不痛恨朱勔;北宋末期,各地频频发生叛乱,而人们所竖起的都是“打倒朱勔”的旗帜。
说起新法时代,人们就会联想到王安石,认为那是清廉、峻法如山、一切有规律的时代,但徽宗时期的情形完全走样。当时的新法纯粹以筹措供应皇帝过奢侈生活之钱财为目的,新法至此已完全堕落了。徽宗对政务并不热心。
“朕听到政治之事就想睡觉,大臣们最好不要拿烦人之事来向朕报告。”徽宗道。
“遵命。”蔡京诚惶诚恐地回答道,“这一点卑职一定会交代大臣的。”
不谈政治,徽宗就精神百倍,拿起画笔、准备描绘花鸟而将视线投向实物时,他的眼睛炯炯发亮,和在庙堂时的慵懒迥然不同,数日后,在上好绢纸上画出来的当然是灿烂夺目的作品。
每次画完画,徽宗就命令身边太监准备微服。微服出巡,在夜晚的街巷溜达,是徽宗的乐趣之一。开封府是座不夜城。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