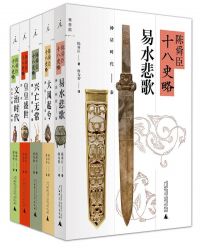二一、再渡黄河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二一
再渡黄河
金是在短期内窜起的政权。一直到渡过黄河、包围宋都开封时,他们都还存有浓厚的狩猎民族气息;换句话说,他们并不热衷于支配中原。
金兵没有预料到,在李纲统率之下的开封守城军竟然如此顽强。情况远远不能和渡河作战同日而语。
开封城中的将兵莫不拼死抵抗,但朝廷的态度却摇摆不定。在御前会议席上,主战论与媾和论完全对立。李纲当然是主战派,媾和派则以李邦彦为代表。
“如此困守愁城,到底有没有战胜的把握呢?”
对钦宗这番质问,主战论者李纲等人只能说一些精神层面的话,根本提不出具体的胜算。钦宗最不满的一点是,自从开封进行守城战,各地几乎没有勤王军崛起的迹象。
“为何如此!?”
被诘问以这句话时,主战论者无言以对。
(如果不实施公田法……)
他们很想以此回答,但这句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方田均税法”是新法政策之一。这个时代的大地主,拥有许多土地而不据实申报以图逃税的情形甚为普遍。王安石经实地测量,查出不少过去隐匿不报的田地。由于目的在防止大地主逃税,应该不能以恶法相称,国家岁收也因而增加不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实际上,实地测量全国田地是不可能的事,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实施而已。
徽宗时期的“公田法”,不像前面所说的方田均税法单纯,使用的是“乐尺”。自古以来,宫廷教坊(歌舞团)用以测量乐器长度的是一种独特的尺,尺度比一般的尺稍短,相差大约百分之八。
以现代的说法,这是把用九十二厘米长的尺测量的长度算做一米。实际上这并不需要实地测量,只要把原来的登记数字加上百分之八就可以;不用说,这样的做法纯粹是以增加税收为目的。
政府的另一个措施是审查土地买卖合约书。没有正式买卖合约书的土地,一概没收为“公田”。在这个时代,土地或物品的让渡一般都只凭口头约定就成立,顶多找人证明便完成。但徽宗时期的执法者一概不承认口头契约或立会人的证言。
大地主都是地方上的豪族,自然雇有账房,该有的文件一应齐全。在这个新法之下,田地被没收的都是小地主或自耕农。
“这块田地我们家已耕作五代之久了。”
尽管跪伏哀求,土地被没收的噩运还是无法避免。
“我们官吏一切依法处理。这块田地必须充为公田。如果想耕作,你可以向政府缴纳租金,租来耕作。”
官吏给他们的,是如此冷淡的回答。
——土地被国家没收。
多数人持的是这样的想法。
这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虽然征募勤王义兵的诏敕已发出,但应该响应的阶层却对国家的不讲理甚为痛恨,而大地主的子弟当然更不可能响应募兵。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征不到兵。
李纲等主战论者,对这一切内情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以为是增加国家税收之妙案的公田法,招来的是国家中坚阶层背离政府的结果。
金提出的媾和条件,宋朝廷中议论百出,莫衷一是。金提出的是如下苛酷条件:
一、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二、以宰相、亲王为人质。
三、赔偿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一万头牛马、百万匹表锻(丝)为战费。
四、以“伯父”称呼金国皇帝。
五、送还居住于宋之领土的燕云住民。
赔偿金金额可以说是漫天开价,在当时,把开封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只有二十万两金和四十万两银。
“将宋的国库全都拿出来,也不够应付他们的要求。割让三镇,根本谈都不用谈,三镇乃我国的生命线,如果割让,无异自毁长城。”
李纲坚决主张拒绝金的要挟。
“拒绝他们的要求,我国就得以安泰吗?开封城命在旦夕。他们的要求不讲道理,这一点,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最好先答应他们,然后再进行交涉,以缓和这些条件。”
李邦彦如此反对主战论派的主张。
——那你们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主战论派的弱点在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有闪烁其词地如此说:
——敌军从远地一路攻来,全军一定疲惫不堪。我们只要能固守一段时期……
虽然勤王义军响应的情形不甚踊跃,但也不是完没有。老将种师道和姚平仲招募的一些兵马,已经来到开封附近。
包围开封的金军号称六万,而救援义军为数多少则不甚明了。
——听说有二十万……
有人如此说,但它好像是经过灌水的数字。表面上看似士兵的这批人,实质上很难以军队称呼。暂时保持观望态度,等到看出有打胜仗的希望才投入战场,以获得恩赏——这是这批人的卑鄙心理。
“唯有接受媾和一途了。”
钦宗遂下这个决断。
苛酷的条件以后再进行交涉——这是此刻的定论。
“野蛮人不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虽然某大臣做此发言,但当务之急还是先让敌军退兵。
“关于人质一事,以宰相为人质尚可,绝不可答应以亲王当人质。”
李纲试图作最后的抵抗。
“现在提出这种事情,对方会怀疑我们的诚意,说不定因此不肯退兵。”
李邦彦如此表示反对。
“构说他愿意去。”
听说对方提出以亲王为人质之条件时,钦宗的九弟康王赵构曾经志愿前去。
此外还要有作为人质的宰相。依据广义解释,阁僚以及身份相等的重臣,也算是宰相。朝廷决定的是,授“计议使”的称号予少宰张邦昌,让他随同康王前赴金军阵营。
张邦昌是媾和派分子,曾经在会议席上坚决主张此际任何屈辱都得忍受,以达到使金军撤退之目的。
因此,他被指名为人质应该无话可说。然而他却惊慌失措地向皇帝恳求道:
“恳请皇上赐给书明绝对信守割地之约的诏敕,好让微臣携带前往。”
宋违反约定事项时,人质有被杀的可能。张邦昌这是以保全自己性命为目的的请求。
“你这是什么话?条件经由交涉可以变更或缓和,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保证绝对信守割地之约,这等于自缚手脚,以后怎么能进行交涉呢?你怎么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
钦宗叱责道。
康王和张邦昌于是渡过黄河,进入金军军营。
奇妙的现象在这之后发生。
原来,分散在郊外的勤王军人数突然增加了。
——金军准备撤退,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加入宋军,绝对不会死。
这句话传出去后,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那批势利眼“勤王军”,开始陆续投入宋军了。
“有这么多人,我们不是有反攻能力吗?”
看到这么多人数时,将军们起了这个念头。听到将军所做的报告时,钦宗表示赞成这个计划。突袭正在撤退渡河的金军,胜算似乎很大。
但急欲抢功的诸将军,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争执。突袭渡河中的敌军——这是种师道献的策。因此,攻击军理应由他指挥。果真如此,击破金军的战功将全归老将种师道。
姚平仲对这一点耿耿于怀。
(老头子还想出什么风头……)
姚平仲向来就对种师道非常看不顺眼。他于是企图抢先立功,准备率领一万步骑发动夜袭。未料,他这个计划都被金军密探探知。
夜袭因而归于失败,害怕受处罚的姚平仲于是亡命逃走。
金军当然派遣使者,以严厉态度诘问违约之事。
“那是姚平仲擅自的行动,绝非朝廷的意思。”
李邦彦连连向使者叩头道歉。
金军使者除了就割让三镇之事再度确认外,更要求更换人质。
他指名要由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
姚平仲夜袭时,人质张邦昌害怕被杀而哭叫不已,丑态百出。而康王则神色泰然,丝毫没有惧色。
他好像早就有被杀的觉悟。视死如归的人不适于做人质,因此,金要求改以钦宗五弟肃王为人质。
以上部分以《宋史》为依据。被送还的康王就是后来的南宋高宗,因此,历史记述有偏袒他的可能。依据《金史》,更换人质之议是宋提出的。
金军终于解除对开封的包围,收兵北归。
老将种师道再度提议先前策划的袭击渡河中金军的作战方案,但钦宗这次却不表赞同。对方已有戒心,因此,再度实施这个作战,成功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金军离去后,宋朝朝廷再度响起主战论调。这与其说是主战论,毋宁是反对割让领土论。由于不守割地之约的结果,金军一定会再度南下,因此,这也算是主战论。
媾和派李邦彦被罢免。
太学生陈东提出由他发起、经数万名首都住民联名的上书。
徐处仁成为太宰,唐恪则成为中书侍郎。他们都是强硬派分子。蔡京被决定流放至海南岛,结果,年迈的他在被送往海南岛的途中病殁。
就在这个时候,传出退位避难至南京的徽宗,准备在江南复辟建立朝廷的风声。
钦宗将父亲所用的大臣悉数罢免、左迁诛杀。退位而成为道君皇帝的徽宗,对这一点想必耿耿于怀吧?但复位而在江南建立朝廷的结果,将使宋王朝一分为二。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钦宗是正式由父亲受让而成为皇帝的,所以是真正的皇帝。既然有此大权,冒牌皇帝出现时,即使是自己的父亲,也非得讨伐不可。
“就是因为道君皇帝在南京,所以身边权臣易于进行诸多策划。现在金军已离去,应恭请道君皇帝回京为宜。如此一来,那批佞人应该无法再有所蠢动。”
李纲如此进言。
“这是上上之策。可是,由谁去恭迎呢?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微臣愿意担任这项任务。”
李纲因而成为关系有些恶化的这对父子之间的调停人。
实际上,徽宗也很想返回开封,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开封街上夜游了。妓楼有相好的女人在等他。退位后的他,在行动上比以前自由许多。
徽宗于这一年四月返回首都。人们莫不为此额手称庆。
然而和平尚未恢复。
于金军北归后,在开封诞生的新政府为强硬派所把持,丝毫没有履行与金之间的诺言之意。
——不可将三镇二十州交给金。
皇帝发下此一严命。
三镇——山中、太原、河间——乃今日河北省至山西省一带地域。金认为宋已割让这个地域。
“我们前来接收此地……”
金以兵不血刃的心态来到宋的三镇,结果发现当地宋军有抵抗的意图。不仅如此,宋还有援军前来的迹象。
“你们应该依约交出此地。”
金军开始包围太原。此时,由种师道之弟种师中以及姚古等将军率领的宋的援军正好来到。
宋的援军和金军在一个名叫杀熊岭的地方发生冲突,结果宋军大败,种师中阵亡,姚古则败走。
这是五月中的事情。
金军遂于九月攻陷太原。
金并没有夺取三镇就罢手的意思,他们以宋违反协议为口实,准备将宋一举攻灭。宋对金的了解,可以说太过皮毛了。
金军大举南下。
开封朝廷大为狼狈。
十一月,金兵渡过黄河。在这之前的正月间,金兵首次渡河包围开封,因此,金兵在这一年里就有两次渡河作战的行动。
事态变得极为严重。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