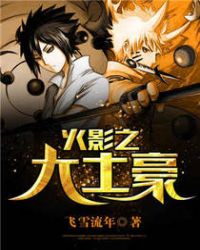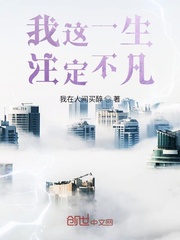1994 “天王”杀手“过江龙”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1994 “天王”杀手“过江龙”
早期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奖歌手唱过了获奖金曲后,还得加唱一首曲目;再之后,获得“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歌手只能唱半首歌,这不是欺负“新人”,“金曲”的待遇也一样,无论“天王”“天后”,都要把歌重新编到3分钟以内。1995年以后,进一步发展到有人没机会唱的状况,比如“最受欢迎新人奖”之类的小奖项,金奖歌手有登台机会,而银奖、铜奖说几句感言就下台了。
这不得不说到“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项逐年增多的状况,就拿“最受欢迎新人奖”来说,它是1988年第一次设立的,好在顶替了以前的“最佳乐队组合奖”,奖项总数量变化不大,而且,当时的“新人奖”只有一名得主,即草蜢。到了1989年,奖项得主变成了王杰和关淑怡两个人。口子一开,这项奖就逐年增多了,1990年、1991年这两年都设置成了金、银、铜奖,1992年之后,又进一步分男女、各颁金银铜3个奖项,这么一搞,1988年的1座奖杯4年后竟然变成了6座。在这种状况下,“无线”还在增加新设奖项,1994年设置了“新一代杰出表现大奖”,也就是日后“年度杰出表现奖”的前身。
实际上,增加奖项的最终目的是在搞平衡、“分猪肉”。在“谭张争霸”的时候就不得不这么搞,不过,当年是两个人搞平衡,怎么都好办。到了“四大天王”时代,就得费点儿脑筋了。1993年张学友和刘德华各拿两支“金曲”,黎明一支。张学友的获奖歌曲是《只想一生跟你走》和《等你等到我心痛》,从歌曲的质量上说,这些歌与刘德华、黎明的歌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因此,张学友必定要拿“金曲金奖”。而从当年的人气考虑,张学友拿“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无线”不能这么办,如果真这样颁奖,张学友可就甩了黎明几条街了,所以,只能把权重比较大的“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分给黎明。说来好笑,张学友竟然是1996年才“最受欢迎”,可眼下只能先委屈张学友,否则平衡没法儿搞。
不过,即便这样,刘德华也难办,因为黎明只有一首“金曲”却拿了“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而刘德华拥有两首“金曲”,难道不应该更受欢迎吗?况且刘德华是张国荣之后连续3年的“最受欢迎男歌星”,怎么就落后了呢?“无线”只能继续“分猪肉”,设置了一个新的奖项:国内最受欢迎香港男女歌星奖。
看明白奖项分配的猫儿腻,歌迷们对偶像获奖多少、获了什么奖,其实都不必在意,看看热闹、听听歌就得了。可就这样,歌迷们听歌也听不过瘾,偶像们没机会唱整首歌,献唱时间都得被压缩。
让颁奖礼上的献唱歌曲压缩时间的因素,还不止是奖项的增加,1994年竟然搞出了12首“金曲”。
据“无线”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出现了票数相同的特殊情况。照这么说,那等于是最后3首歌同分。可是,这个说法有点儿不可信,1993年颁奖礼上,主持人郑丹瑞说过评分规则:观众投票占1/3,“无线”占1/3,专家评委占1/3,在这种投票评分机制下,3首歌同分的概率到底能有多大呢?
如果不是被“十大”这种名称限制住,往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评出“十二大”亦无不可。就说1983年第一届吧,据说排名第十一位的就是张国荣的《风继续吹》。这段故事是真是假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年都有遗珠之憾。
而从香港流行乐坛的历史来说,放开名额也属于与时俱进。
香港电台有个叫“中文歌曲龙虎榜”的节目,要说起它的历史,则要说到1975年开始的一档叫《青春交响曲》的节目,其中有个版块叫“新天地”,即听众点歌,过了一年,它便改名为“中文歌曲龙虎榜”。
最早,“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公布10首上榜歌曲,1987年,因为香港流行乐坛进入黄金期,本地流行歌曲的产量增加,“龙虎榜”就改为每周公布15首歌曲,1989年更是增加到每周20首。
“龙虎榜”的改变是顺应市场潮流的,但它却并未影响到各类年终颁奖礼,它们还是在增加“其他奖项”上下功夫,从来没有想过增加“十大”的名额。显然,“十大”的称呼是一个天然的障碍,但在1994年,“无线”也不知道怎么想开了,干脆抛开“十大”的包袱,多放了两个名额进来。
至于“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此后也出现过超出10首“金曲”的情况,而“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更是在2013年开始革新,从名字里抹去了“十大”的字样,这就彻底甩开了包袱,选出了20首“金曲”,甚至允许翻唱歌拿奖——可问题是,早干吗去了?金曲如潮的时代不放开,到了这年头儿,真的有这么多“金曲”吗?
还是说回1994年,究竟是什么导致了12首“金曲”的状况?
看看这一年谁是最大的赢家,或许就有了答案。
巫启贤,本年度获得了一支“金曲”、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奖铜奖、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银奖、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金奖。此前一年的“金曲金奖”《只想一生跟你走》就是他的作品,而此后,他被马来西亚政府颁赠“马来西亚歌神”的称号,这是华语乐坛歌手中惟一得到国家政府认证的“歌神”。
周华健,本年度获得了一支“金曲”、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银奖、新一代杰出表演大奖金奖。此前,他曾4次入围并获得一次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手男演唱人”奖,此后,他还在1995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获得了一支“金曲”和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铜奖、最受欢迎创作歌手金奖,被称为“天王杀手”。
这两位“王中王”级别的歌手,是为数不多的能冲击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的人,因为他们来自台湾,借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的奖项名称,这类歌手被称为“过江龙”。
严格来说,“叱咤乐坛流行榜”中的“过江龙”奖是颁给香港以外的国语歌手的,其中,1993年、1994年这两年的银奖都是周华健,而1993年“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银奖却是来自台湾的王馨平,到了1995年,周华健反而不是“过江龙”,成了“叱咤乐坛男歌手”铜奖。
这恐怕会让很多人看不懂。按说周华健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才去台湾上学的,而王馨平则正相反,她是台湾出生,大学后才进入香港流行乐坛的,怎么看都好像王馨平更应该属于“过江龙”,而周华健是香港本土歌手才对。
实际上,王馨平出道的时候就签约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当时,她就快毕业,打算去美国读硕士,可无意中录了几首小样,就此选择了唱歌。她的父亲是著名影星王羽,将她托付给老朋友甄妮,甄妮又带着王馨平去见泰迪·罗宾的弟弟关维麟,就此签约到了香港“宝丽金”,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粤语,所以算作香港歌手,没有做“过江龙”的资格,却可以角逐有“新人奖”性质的“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
而周华健虽然是香港生人,但1993年的身份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的国语歌手,这时候他可以算“过江龙”。1993年,“滚石”在香港设了公司,周华健在1994~1995年连发的3张粤语专辑属于香港“滚石”的产品,这样,1995年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当选为“过江龙”,反而可以以粤语歌手的身份参加“叱咤乐坛男歌手”的评选了。
其实,这种事以前就发生在另一位传奇身上:王杰。
王杰是香港生人,但也是在台湾进入乐坛的,前3张国语专辑已经把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搅了个天翻地覆,只是当年没有“过江龙”的奖项。1989年他出版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后,立即获得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同时,因为他在香港市场算是“刚出道”,竟然连“最受欢迎新人奖”也顺便拿走了。
像王杰、周华健、巫启贤这类在国语市场已经是“歌神”级别的人物,进入已经疲弱的香港粤语音乐市场,无异于直入无人之境。
这么说当然有些夸张,却未必不是现实。至于他们和香港歌手的唱功高下,我们且不去评判,在唱功后面,他们一定还有过人之处。
细心地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创作型歌手。
在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里,别说许冠杰、林子祥这样的殿堂级艺术家,就连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黄家驹这些当时的“后生”都有相当水准的填词、作曲能力。可这些人隐退后,歌坛上出现了大量没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所谓“歌手”,连唱歌都走调,能指望他们创作什么作品?
举个例子,前面说过,1989年“亚视”举办的“亚洲太平洋歌唱赛”,就是用卡拉OK发掘“新人”。这项比赛分两个阶段,一是举办港区赛;二是邀请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选手举办亚太区赛。当年,香港派出的选手是叶子楣,澳门派出的选手是李莉莉,实在没法儿想象这两个“波霸”级别的“歌手”怎么唱歌。再看看台湾派来的选手:黄小琥,那是她签约唱片公司的第一年,可此时的她已经有七八年的舞台经验了。
港台流行音乐的差距不在叶子楣与黄小琥的唱功上,也不在创作型歌手的多少上,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态度。
我们先说一位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叫陈达,是一位民谣歌者。16岁时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吟唱生涯,29岁目盲,39岁半身不遂,妻离子散,孑然一身,只有一把月琴陪伴在他身边;直至62岁的时候,他才为人所知,66岁时录制了第一张唱片;72岁时被当作台湾本土音乐的活化石,受邀去台北演出;74岁时患有精神疾病,据说曾因蓬头垢面地在街上游荡而被当作乞丐送进收容所;76岁那年,他因车祸去世——这是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一年,张艾嘉唱了《童年》。
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说:“在碰撞的那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月琴弦歌声成为绝响,陈达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像一阵风飘去,只留下满地的凉意。”但是,陈达以及他所传承的音乐,却不可否认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台湾流行音乐,尤其是闽南语音乐。多年以后,曾与李宗盛一起组建过“木吉他合唱团”的一位音乐人接过了陈达的月琴,他就是今天的“台湾民谣大师”陈明章。
或许,陈达是一个太久远的记忆了,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台湾音乐人,他叫胡德夫。1976年,他和杨弦、李双泽开启了“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从此,台湾正式进入了流行音乐时代。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音乐大师”,第一张专辑竟然要到2005年才出版。
虽然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但胡德夫音乐生涯的最初阶段是深受西洋音乐影响的。20世纪70年代,还是学生的胡德夫就在咖啡厅唱英文歌,并且小有名气。正是这段时期,他认识了李双泽。
胡德夫的父母都是台湾当地的原住民。有一次,他偶然唱了父辈教给他的歌谣,李双泽听了很激动,告诉胡德夫:我们要“唱自己的歌”。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胡德夫和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教父”许冠杰。他们都是受西洋音乐影响,都在酒吧、餐厅唱过英文歌,也都意识到要唱本土音乐,虽然他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但两位“教父”音乐生涯的起步别无二致。
而此后,港台流行乐坛的发展也多有相似之处。比如,香港受到了电子舞曲曲风的影响,几乎同时,1986年,台湾也有纪宏仁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可是,为什么香港流行音乐的路越走越窄,仅仅十几年之后就被台湾的“过江龙”们超越了呢?
答案很多,但最根本的,也许就在陈达身上。
陈达是被台湾的音乐学者史惟亮和许常惠发掘出来的。当时,他们正在搞“民歌采集运动”,这项工作有点儿类似王洛宾所做的,经常深入到民间采风。1967年,他们遇到了贫病交加的陈达,并对以他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进行挽救。这项“民歌采集运动”持续了多久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至少有十多年,因为在1978年,许常惠又发现了郭英男。此时,郭英男已经将近六旬,而史惟亮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就是史撷咏,电影《滚滚红尘》的配乐师。
郭英男是谁?也许跟陈达一样,内地的歌迷们并不熟悉,但要说到英格玛1993年的作品《Return to Innocence》(《返璞归真》)恐怕无人不知,它在1996年作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宣传片歌曲风靡世界。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首绝世天唱的部分旋律以及其中的男声,都是出自郭英男。为此,郭英男和英格玛之间还产生了一场版权官司。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的民间还有多少“陈达”和“郭英男”,也不知道这片土壤还蕴藏着多少音乐瑰宝,大部分内地歌迷对此一直很陌生,直到多年之后,我们才有幸接触到这类音乐: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不仅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令人感慨的悲壮故事,还让我们听到了让人不可思议与心潮澎湃的音乐。
这种藏在台湾民间的音乐,与我们以往听过的“国语时代曲”和“国语流行曲”完全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楚它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中起到多少作用,但有种作用是一直存在却无法言说的,它叫滋养。
这就是香港流行音乐和台湾流行音乐的本质区别。
因为存在着信息资讯与文化交流的种种原因,我们对香港流行音乐了解得更多,对台湾流行音乐的了解,往大了说,恐怕连十分之一也没有——这么说并不危言耸听,大部分歌迷了解的是罗大佑、齐秦乃至“小虎队”之后的台湾流行音乐。若不是齐秦这两年在内地电视节目中唱过几次《张三的歌》,又有几个人会想起李寿全呢?我们认识的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李宗盛,但不知道“木吉他”时代的他;我们认识的是《梦醒时分》的陈淑桦和当了评委的黄韵玲,却完全不记得她们的天才少女时代;我们只知道唱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的潘越云,却不知道她是当年台湾乐坛的试验田,几乎所有音乐人的奇思妙想都要找她实现;我们只知道李丽芬唱过几近烂俗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却不知道她是1979年“民谣风”比赛的冠军,顺便说说其他人吧,亚军是郑怡,第四是蔡琴,第五是苏来,也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苏来的《天水乐集》,但恐怕没人不知道他创作的《你的眼神》……
对台湾流行音乐的陌生,让我们错过了太多的好音乐,也错过了太多优秀的音乐家。同时,我们的耳朵习惯了“港式流行曲”的曲式和曲风,如今回头再听齐豫、郑怡和潘越云,都感到那种音乐太过陌生、太不舒服,进而有些排斥和怀疑——难道,这是流行歌曲吗?
是的,那是流行歌曲,只不过,我们头脑中关于它的概念太过狭隘和浅俗,我们的耳朵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反而固定在了一种模式上,使得我们忘记了什么是好音乐。
在对音乐的追求上,香港流行乐坛走在了后面。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陈升的音乐在香港市场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在“反流行”,他的作品根本不符合所谓的“音乐常识”,香港唱片公司不可能像“滚石”一样容忍他的自由创作和个性风格,就像不可能容忍Beyond一样。
进而,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台湾音乐在做“专辑”,一张专辑是一部统一而紧密的作品,比如李寿全的《8又二分之一》,虽然只有8首歌是成形的,但整张专辑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甚至当年,很多台湾流行音乐专辑还有《序》的部分;而香港呢,他们在做“单曲”,一张专辑中有那么一两首歌足够打榜、获奖,就可以了。
音乐土壤本就不如台湾,唱片公司对音乐的态度又退化到只追求流行和销量的层面上,香港流行音乐的水准被台湾超越便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创作力不足,要从台湾引进歌曲版权。
引进歌曲对香港流行音乐来说,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引入欧美流行音乐,这个阶段的代表是林子祥那一代歌手;第二阶段是引入韩日流行音乐,典型的是谭咏麟、梅艳芳和早期的张学友;第三阶段才是引入台湾音乐。这三个阶段与歌迷群体的欣赏习惯和香港唱片业的海外市场都有关系,比如,引入欧美音乐时代的歌迷们,多半是听这类音乐长大的,他们对英文歌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华语歌曲;此后香港唱片产量大了,要发展亚洲市场,对日韩、中国台湾音乐的引进显然也有营销策略的考虑,“天王巨星”唱台湾创作人的金曲,无疑会更加顺利地进军台湾流行音乐市场。
当然,香港流行音乐与台湾的联系,要往远了说,是说也说不完的。在“我系我”时代(1974~1983年)之前,粤语歌还没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国语时代曲”可不就是台湾的流行音乐吗?在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的姚苏蓉、青山、刘家昌、尤雅、刘文正,他们的歌曲在当时的香港有很大的市场,即使是粤语歌的开山级代表人物甄妮,其实也是从台湾过来的。就算进入了“我系我”时代,香港流行乐坛也有台湾音乐人的参与,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齐豫就获得过“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引进台湾音乐”,需要限定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滔滔两岸潮”时期,黄霑的这一命名也是意指港台音乐的互动和交融。
在这段时间里,最早与香港流行乐坛发生联系的,是1983年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蔡琴,1984年、1985年两年,苏芮也连续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奖项。1986年,台湾乐坛搞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标签式作品《明天会更好》,借着它的流行,很多台湾歌手步着蔡琴、苏芮的后尘,都跑到香港探路。据香港著名的乐评人、流行音乐史专家黄志华先生回顾,当时有陈淑桦、娃娃、李宗盛、李寿全、张清芳、纪宏仁、文章等优秀歌手入港,李宗盛顺便还把电台DJ朱卫茵拐跑了。
虽然台湾音乐人并未在香港乐坛站住脚,表面上这次探路的结果不甚理想,但他们的音乐却吸引了香港乐坛。
1986年,张艾嘉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最爱》,电影同名主题歌就是李宗盛作曲的,唱过这首歌的人太多了,潘越云、张艾嘉、齐豫、李宗盛和许景淳都唱过。2013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杨宗纬又演绎了一版。它和香港流行乐坛产生的联系,是张国荣的同名翻唱,收录在1988年的《Virgin Snow》专辑中,同年他的《Hot Summer》专辑又出现了一首翻唱自台湾音乐人的作品,它就是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无需要太多》,国语版叫《我要的不多》,作者是台湾流行乐坛的一代奇才马兆骏。
《无需要太多》只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没有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好像“无线”在有意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搞出差异化来,但是,两项颁奖礼都无法回避一首歌,都把奖项颁给了它,甚至“香港十大劲歌金曲”还多给了一座“金曲金奖”,这首歌就是叶蒨文的《祝福》,它是台湾音乐人梁弘志的作品,国语版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台湾音乐人如此生猛,1988年一过,香港流行乐坛就再也挡不住台湾音乐的势头了。1989年让李克勤红透一时的《一生不变》,翻唱自台湾歌手张镐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让陈百强再创高峰的《一生何求》,翻唱自王杰的《惦记这一些》;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是童安格的作品;再过了一年,1990年刘德华的金曲《再会了》是伍思凯的作品;张学友的金曲《只愿一生爱一人》是庾澄庆的作品。
香港流行音乐还不仅仅是翻唱台湾歌曲,更有台湾歌手直接来香港拿奖。1988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中,评选出了一位台湾歌手:齐秦,获奖的金曲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里程碑式作品《大约在冬季》。这个口子一开,1989年,王杰用粤语歌曲在“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上双丰收;1990年,张洪量、伍思凯用国语歌曲拿走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奖杯;也就是在这一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设置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否则,粤语歌曲实在无法抵挡国语歌的汹汹势头。
现在看来,“无线”对国语、粤语歌曲分别颁奖的设计是正确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没有分国语粤语,所以此后的“十大”中进入了不少国语歌曲,让粤语歌的成色大减,无形中也是对粤语歌的一次冲击。不过,真正的冲击是1993年台湾“滚石”唱片正式在香港设立支部,直接发行出版“滚石”旗下所有的中外唱片,这一下,周华健等人就直接跑到粤语歌颁奖礼上拿奖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就算把国语、粤语歌曲分开颁奖,“过江龙”们也毫不客气地来侵略“四大天王”的领地。
国语歌曲对香港流行乐坛的冲击,还不仅仅来自台湾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内地音乐就与香港有了互动。
内地的音乐作品销售到香港,大概是从崔健开始的,但产生影响的专辑出现在1991年,它的名字不能被遗忘:《黑月亮》,它背后的名字更不可遗忘,他叫侯牧人。此后,香港流行乐坛也开始购买内地音乐版权,代表就是吕方1992年的《弯弯的月亮》。
几乎同时,内地的音乐人也进入了香港。1992年7月,香港开了一场内地歌星的演唱会,参加者有毛阿敏、蔡国庆、腾格尔、那英、解晓东。香港歌迷对这些内地歌星非常陌生,但就像1986年台湾音乐人去香港“探路”一样,虽说一时没站稳脚跟,却为两地交流开了个口子。
歌卖过去了,演唱会也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流行乐坛与内地歌星签约便是顺理成章的举动。现在说不清楚谁是第一位和香港唱片公司签约的内地歌手,大概应该是常宽,1991年他和香港“百代”唱片签约,但据黄霑说,同时签约的还有解晓东和毛阿敏等内地歌星。
当年更出名的是一位艺名叫“红豆”的歌手,他的本名叫王真颜,是个很有潜力的歌手,后来的事儿嘛……那就怨不得别人了,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这还不算完,1994年5月,一位内地歌手竟然出版了一张奇怪的专辑:高林生的《我会陪你到永远》,如果记忆没错的话,这大概是第一张由内地音乐人创作的粤语专辑。
内地歌手出版粤语专辑,这在以前,对盲目崇拜香港流行歌曲的内地歌迷来说根本不可想象。可这并不奇怪,这一年的内地叫响了一个名字:“94新生代”,内地流行音乐工业的第一代“造星”产品集体爆发。更不能让香港流行音乐史忘记的是,同样在1994年,香港的红磡体育馆还上演了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而这,恰恰发生在香港流行乐坛被台湾“过江龙”们席卷的同一年。
“天王杀手”过江了,“94新生代”崛起了,摇滚乐火爆了,内地和台湾流行音乐不但挤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内地市场份额,而且还对香港本地市场跃跃欲试,在这双重压力下,香港流行乐坛该如何应对?
这或许是香港流行音乐唯一的一次“自救”机会,如果它选择与内地、台湾进行深入的文化融合,利用自己十多年来发展成熟的娱乐工业经验成果,未必没有前途。但是,香港流行乐坛却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行为,它的出发点是好的,行动起来也貌似有道理,可在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偶像时代,它不但是一厢情愿,而且,更像一种自杀行为。
这种极端行为,就是香港商业二台发起的“原创歌运动”。
1994年 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 《梦中人》 王菲
2. 《铁幕诱惑》 郭富城
3. 《让我跟你走》 彭羚
4.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张学友
5. 《向全世界说爱你》 许志安
6. 《女人的弱点》 叶蒨文
7. 《终有一天感动你》 李乐诗
8 . 《缱绻星光下》 关淑怡
9 . 《哪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
10. 《谁人知》 刘德华
11. 《心酸的情歌》 巫启贤
12. 《昨晚你已嫁给谁》 周华健
最佳作曲奖:《哪有一天不想你》 作曲:林慕德
最佳填词奖:《缱绻星光下》 填词:周礼茂
最佳编曲奖:《昨晚你已嫁给谁》 编曲:江建民
最佳歌曲监制奖:《缱绻星光下》 监制:叶广权
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奖:
金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主唱:苏永康、彭家丽
银奖:《非一般爱火》 主唱:许志安、郑秀文
铜奖:《爱情来的时候》 主唱:巫启贤、杨采妮
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
金奖:《忘情水》 主唱:刘德华
银奖:《太傻》 主唱:巫启贤
铜奖:《用心良苦》 主唱:张宇
最受欢迎创作歌星奖:
金奖:巫启贤 银奖:周华健 铜奖:李乐诗
最受欢迎新人奖:
男歌星:金奖/古巨基 银奖/海俊杰 铜奖/曹永廉
女歌星:金奖/吴倩莲 银奖/刘雅丽 铜奖/李蕙敏
新一代杰出表演大奖:
男歌星:金奖/周华健 银奖/郑伊健 铜奖/梁汉文
女歌星:金奖/彭羚 银奖/周慧敏 铜奖/郑秀文
最佳音乐录像带奖:《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主唱:草蜢编导:曾宪宗
最佳音乐录像带演出奖:《希望》 主唱:李克勤
最受欢迎男歌星:刘德华
最受欢迎女歌星:王菲
亚太区最受欢迎香港男歌星:张学友
亚太区最受欢迎香港女歌星:王菲
金曲金奖:《哪有一天不想你》 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