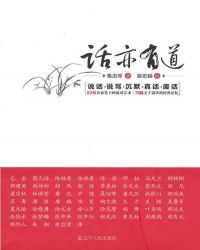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话亦有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论读书与谈话 陈炼青
书籍是一种怪物:它能使你越读越爱,越爱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瘾,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总离不了它。到了上了瘾,无论你有何种忧愁,当你拿书静看时,刹那间便忘怀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领略书中无穷的妙味。如其一拿书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见,那不算对于书籍有深刻的爱好。真正的读书人,只是“行其所无事”的读,丝毫对于书籍没有功利的念头。古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原是以金钱和美人的磁石,来吸引人们走上读书之路,自己骗自己的讲下,与书籍毫无相干。看书上瘾的人,视书为娱悦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当它是知识的宝库,并不想借它来钓名,来取利,来博得美人的青睐。
人们常说,书籍是知识之宝库,里头藏着许多用不尽的好东西,需要知识的总要时时亲近它,保管不会受亏。不错,我也相当的承认。然而话虽这样讲,事实上,不是件件知识都由读书得来,得之于别的,如大自然的现象,现实社会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书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们今日晓舞文弄墨,知道我们自己心眼中所谓真是与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门外汉)甚异其趣,未始不是多半从它得来的结果,体识事理,虽然有脑筋供我们判断,可会直接帮助我们的心灵到广博的地方游历,间接又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理,洞悉人生,这是确实的话。我没有勇气敢否认这话。
历来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说他自己是顶厌恶书籍的。虽则曾听说斯宾塞尔是一个著名的憎恶书籍者,然而你能够承认那是他心里抒发出来的吗?说不定当他嚷出憎恶书籍的呼声,他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一肚学问罢,因之就无妨随便讲讲。这好像我们的李太白,因为天才不可一世,胡乱拿起笔挥了一下,就有好诗由他的毫端吐出来,一朝碰着杜子美那个“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呆子,怎么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总喜欢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间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内玩看窗外的景色一样,望舒凝睇,无论什么东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们站在公允的地方看,书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进化的巨大就靠着它。并且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在书堆里呼吸了长期的气息,而后能成就其伟大,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者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愉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萧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借读书来疗养,来消忧,不仅追求知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著作,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深浅,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庐骚①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代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吗?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它拿来和朋辈讨论一遍,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知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S.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辗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寻求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一概都无忌的全盘说出。既有正经的问题,又有玩笑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营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聚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再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见,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几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租会址,并且交换知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炼中。上面所讲的谈话会,能够磨炼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炼,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尝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究有得,欲发表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一起讨论一二遍,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如何?
(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3期)
陈炼青(1907—1940),广东潮安人。1921年赴新加坡。1922年入华侨中学。1928年主编《叻报·椰林》,同年创办《晓天周刊》。1931年因健康问题辞去工作,回到故乡养病。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