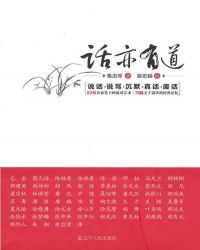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话亦有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编后赘语这本书的诞生,说起来应该感谢一位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诗人。此前,我虽然也受了新文学影响多年,还编了两年教人说话的刊物,但却从未考虑过将新文学与“说话”联系起来编一本书,直到一次逛旧书市时买下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朱湘》一集。
今天知道朱湘的人已经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以诗人名,却没有写出能够打动大多数今人的诗句。这种情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例子,比如李健吾,若早早便以批评家名,也不至于得到现在的冷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诗人的称号对朱湘来说再合适不过,这个1920年代的清华学生,在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几年后(1933年),毅然决绝地投入了江中,据目击者说自杀前还朗诵过海涅的诗,终应了自己的诗篇“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诗人之死,无论何种结局,也许都不让人觉得欷歔,但是如果你曾读过朱湘与妻子霓君生前的通信,你一定还是会慨叹运命的无常。
罗皑岚曾说:“如果有人问我,文学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我可以马上回答说,我顶喜欢书信和日记,但也有一个附带的条件,那便是写这书信和日记的人,生前没有存着要印给大家看的心思。如果存着这样的心,他无形中便把真情藏了一半,读者能看到的,不过是他那副摆给观众欣赏的面具而已。”但是,胡适之的日记可能存着印给大家看的心思,朱湘的书信则是没有一丝旁枝的目的,他只是想用这些文字去爱抚、安慰一个他心爱的姑娘。爱情的悲剧无法避免地落在了诗人头上,“说话”的悲剧也成了诗人生命中的无法承受之轻。
朱湘的《说说话》也许不是一篇关于说话的最漂亮的文章,却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用朱湘自己的话讲,他是一个口齿极钝,连普通的应酬都不能够对付的人,却偏偏也要站出来谈说话。无独有偶,语言学家王力也是这样一位无法温饱却出来给人上课的人。在《说话》中,王力写道:“说话比写文章容易,因为不必查字典,不必担心写白字;同时,说话又比写文章难,因为没有精细考虑和推敲的余暇。基于这后一个理由,像我这么一个极端不会说话的人,居然也写起一篇‘说话’来了。”两个不会说话的人,不约而同地谈起了说话,看来,人不仅有说话的欲望,而且还有说说话的欲望。
如果说说话是一种欲望,那么它肯定与教别人说话无关,否则你就会觉得王力、朱湘之流是那些在各种讲座里夸夸其谈的骗子。当然,这些作家诗人愿意将自己的说说话拿出来发表,也肯定不仅仅是满足私欲的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在他们看来,说话太重要了。否则古人也不会留下那么多与说话有关的成语、俗语,比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刀子嘴豆腐心,话不投机半句多,言多必失,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人之言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会说话,在学校讨老师同学的喜欢,在单位受领导同事的欢迎,就连找女朋友也远比那些笨嘴笨舌的天生就该当光棍儿的容易。如那爱哭的孩子有奶喝一样,甜嘴的人不会吃亏,简直就是真理。甚至,说话已经与人类的本质产生了联系,孙绍振先生就在文章中说过:“有一种新学说,说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会说话,用声音符号来唤醒经验,象征意义,达到交流的目的。这个说法可能更加有道理。”
说话太重要了,但是,一定还有但是。还有比说话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的心灵,比如人的良知,比如人的友谊,还比如爱情本身。否则贾宝玉就一定不会在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选择前者。所以,编这样一本书的目的,只能是通过这些涉及人的本质的文字,来表达编者的一点点认识,因为在编者看来,说话和说说话是能够反映人的心灵、良知、友谊和爱的。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关于这本书的编选。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民国时期的作家,这里我想引用谢泳先生在《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中所述的一段文字来作为我这种编选界限的理论依据:“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曾在南京办了一次‘民国油画展’。后来我在太原见到了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划、著名美术评论家李小山先生,我就问他这个‘民国油画’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我又问他,如果‘民国’出生的油画家,他们在‘共和国’时期创作的油画算不算‘民国油画’?他说算。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民国油画’的概念,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考虑外,主要着眼于那些油画家主要的成长和活动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正是基于此,我选了“民国”出生的作家在“共和国”时期的文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先提出一个“民国说话”的概念。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文学史价值。这终究是一本与文学有关的书,从开始酝酿编辑这本书时便已经明确,但有一点是我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的,这便是对一些作家及文体意识的理解。前面我已经提到了朱湘与李健吾的文体问题,实际上给我以最大触动的作家是向来给人以温文尔雅印象的作家朱自清,他的一组“说话”文章为本书贡献极大,也使得与《背影》的作者截然不同的朱先生以新的姿态站到了另一派散文家的队伍之中—小品文作家,而几乎就在这一瞬间,中国现代文坛的这些重要作家(让人欣慰的是冥冥之中这些作家都为我们留下了说说话的经典)多成了小品文写作的实践者,成为了至今依然应该延续的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次不易觉察的、自发的齐心协力的、不谋而合的行动主体。进一步讲,我们是否可以在说话—小品文写作—新文化运动—现代作家这几个词语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关系,从而达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体与作家风格、说话与作家风骨的再认识。对于这一点,我也只想在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最后,感谢我的父亲姚润武、母亲张玉芬,你们的儿子虽然不会讲出漂亮的话,却继承了你们善良而纯真的心;感谢韩石山老师,不仅推荐刘绪源先生的“谈话风”系列文章,还亲自为之作序,提升了这本小书的价值与品位;还要感谢陈子善老师,在百忙之中写信对此书的编排等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对它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感谢其他为这本书的诞生付出过努力的朋友,恕我无法在这里一一致谢。
姚宏越
2010年3月 于沈阳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