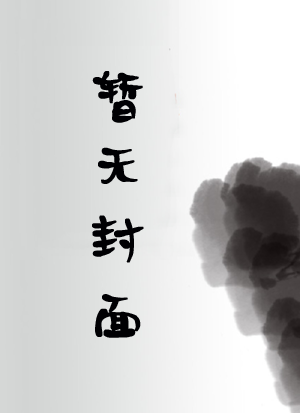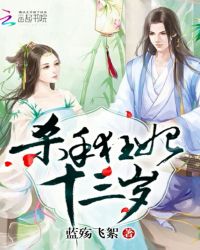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一念之间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顶门杠
正月的最后一天,观头村叫“月尽”。月尽这天,要吃煎馍。
关于吃煎馍的习俗,谁也不知道是从哪朝哪代传下来的,反正那时候所有的节令都和吃有关,有句骂人的俗语说的是:吃嘴婆娘盼节令。只有节令到了,才能理直气壮地吃,光明正大地吃。月尽摊煎馍对家家户户来说都是大事,吃了煎馍,年才算正经过完。
头天晚上,牛娃娘已经把面水搅好,醒上,又从麦秸垛拽了满满两筐麦秸堆在灶火跟前。
牛娃刚过十四,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点也没有牛犊健硕的样子。但牛娃学习好,喜顺爷看见牛娃就摸摸他的头:这娃将来是块材料。牛娃爹听了这话心里高兴,更舍不得让牛娃干一点活,光让他学习。
月尽清早,鸡叫头遍,牛娃娘就起来,点了灯,开始摊煎馍。蒸馒头用的大铁锅用油抹了,醒了一夜的面水加了干花椒叶,光滑如缎,舀一勺,沿着半锅沿快速倒下去,趁着面水往锅底流的时候,用铁铲从下往上刮均匀。放了锅铲,灶火里填一把麦秸,一拉风箱,“轰”的一声大火起来,锅里的煎馍熟了一面,铲子把薄脆如纸的边一铲,双手拉着,一抖,翻个个儿,再添一把麦秸,一张圆如大鼓,香软薄透的煎馍就上了大篦子。
牛娃娘煎馍摊得好是出了名的,牛娃爹害病以前,年年月尽都抓着煎馍,端着辣子蒜水碗在崖头上显摆,一害病,再走不上崖头了。但牛娃娘不马虎,攒了劲儿,日子得往前过啊。
鸡叫三遍,牛娃起来了。他抓起煎馍就吃,牛娃娘说:“还早,再睡会儿。”
牛娃说:“不睡了,我跟天柱叔说好了,今天跟他们进山。”
牛娃娘吓一跳:“老天爷,你进山干啥?”
牛娃又抓了一个煎馍:“割蒿。”
牛娃娘的煎馍煳锅底了,她咋也劝不住牛娃,又不敢让牛娃爹听见,只能一声接一声叹气。
吃了五个大煎馍,又包了几个,牛娃拿了绳子、镰刀去找天柱叔,牛娃娘在窑里摊着煎馍抹着泪。
村里人一年四季有空就上山割蒿,青蒿沤粪,干蒿烧火。山里经常有蛇之类的野物出没,进山割蒿都会喊几个人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牛娃跟着天柱叔进了山,牛娃娘在家提心吊胆一整天,太阳还在树梢上挂着,她就站在村口望着,一直到天麻麻黑,她才看见挑着担子的天柱他们一闪一闪进了村。
“天柱,牛娃呢?”
“在后头。”
挑着担子的男人们陆陆续续进了村,牛娃娘见人就问,都说在后头。可天都黑透了,依然没见牛娃的影子。
她又跑去天柱家,天柱在喝汤。他说一天都和牛娃在一起,牛娃割了一捆干蒿,拾了一小捆硬柴,都说他拿不动,又不会挑担子,让他只背一样,可他不干,都要拿,大伙就帮他把硬柴和干蒿捆在一起,弄扎实了,让他背着下山。刚开始,牛娃走前头,走着走着,挑担子的大人们就走他前头了,一路走一路喊着,听着他答应了,脚底下才走快些,到沟口还听见他应声呢。
牛娃娘听完,放了心,赶紧去沟口接。天柱放了碗,也慌忙跟了去。
正月的风还很硬,越往沟里走,到处都是一片黑,各种声音在风中纠缠,最后形成一种古怪的响动,似风吼似兽叫,要不是天柱跟着,牛娃娘自己说啥也不敢走,想着牛娃还在沟里,她更是揪心。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喊,沟里响着回声,但听不见牛娃应声。
又往沟里走了四五里路的样子,耳边突然响起几声像人大笑似的鸟叫,以往偶尔听到这种声音,村里人都觉得不吉利。天柱说:“嫂子,不敢再往里走了,回村叫人吧。”
吃饭早的人家已经睡下,听见天柱喊叫,又从被窝爬起来,几十个男人、女人很快聚在场院。喜顺爷也来了,他喊天柱,拿上明火,男人进山,女人都在场院等着。
也许是明火的作用,也许是人多,再进山,那些声音似乎消失了。
进了沟口没多远,就有人发现了牛娃的蒿捆子,再找,在一个干草窝子里找到了牛娃,他居然睡着了。
大家七手八脚把牛娃和他的蒿捆子弄回场院,牛娃娘抱着牛娃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牛娃倒没事人一样,他说:“路上有条蛇,我不敢走。蛇走了,蒿捆子放下,我又背不起来了,喊天柱叔,他们听不见。想着歇会儿,就睡着了。没事,没事,这不好好的吗!”
牛娃娘扬起手,想打他,又舍不得,最后轻轻落在儿子瘦削的背上。
牛娃说:“辛苦喜顺爷、叔叔婶婶们了。”天柱摆摆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天宝笑说:“小鸡娃身子,顶不了事。”
喜顺爷呵斥他:“你懂个屁,这是老牛家的顶门杠嘞。”
(原载《小小说选刊》2018年第8期) 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