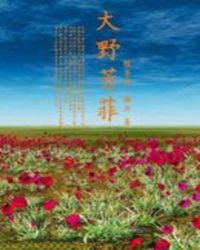1771年2月初,土尔扈特蒙古人在沙俄军队的残酷追杀下,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穿过奥琴默峡谷,奔向通往祖国的必经之路——吐尔盖河。正值严冬,白雪皑皑的东迁之路,撒满了土尔扈特人捍卫民族尊严的热血。宫殿的熊熊大火,象征着一去不再复返的决心。
一部描述土尔扈特蒙古人东迁历史的《鞑靼人的反叛》,再次了加深哈斯伦德对东方的了解。站在烈日骄阳下的古曾河畔,他的眼睛穿越东方的海岸线,土尔扈特人的祖国,像一块巨大的磁盘吸引着他,同时,他也被这个可歌可泣的民族所折服。
土尔扈特蒙古王女就要离开哈斯伦德神往的东方了,溪流,小径,山峰,草海,毡帐,羊群,所有熟稔的东西因分离而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只有牧人的歌声还回荡在她的耳畔。泪水,终于还是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北欧的古老王国丹麦,是一个临海的国家,范围包括日德兰半岛北部地区、波罗的海入口处群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面积只有16629平方公里(不包括格陵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中为最小的一个国家。
丹麦与瑞典是兄弟国。
早在1894年,闻名世界的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开始了他的新疆探险生涯。他在中国西部沙漠以及高原地区,游历探险过八次。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壮举,再一次激励了丹麦少年哈斯伦德。
未结证明的事情,最有吸引力。
暑假来临,心怀梦想的哈斯伦德背起行囊,像真正的旅行家,和好友卡尔一起乘坐着邮递马车上路了,像试飞的鹰雏,游历在丹麦的国土上。
他们都是迷恋东方的少年。
站在丹麦最长的流河古曾河的岸边,哈斯伦德想象不出长江黄河带给他的那种冲击。他看着波涛汹涌的河水,十分懊恼,“真没意思,在这种行程中,我永远也体会不出东方的魅力。”
躺在沙滩上的卡尔也觉得这是一次很无聊的旅行,“我也觉得没有意思。我都被你讲述的东方迷住了,古曾河在我们的眼里,也许只是长江黄河里的一滴水吧!”
近处的农庄,散发着浓烈的田园气息,似一幅欧洲风景画,铺展在丹麦王国的土地上。弥漫在天空中的晨雾,没有遮住它们瑰玫红色的尖形屋脊,显现出浪漫的色彩。可是,在哈斯伦德的眼睛里,很大的一片农庄,也只不过是那片广阔草原上的一个极小的土丘。
隆冬的雪,在丹麦少年的幻想中溶化。
春天的风,接续着哈斯伦德新的梦想。
随着日月的运转,哈斯伦德更加关注古老的东方,关注着发生在东方的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
不久前,他有幸阅读到了英国人德昆西所著的《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他在这部书的第一页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而东归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的了。”
土尔扈特蒙古是中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约在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分为绰罗斯特(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并形成了厄鲁特四部联盟。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所部,联合和硕特和杜尔伯特的一部分,约有五万帐的牧民,越过哈萨克草原,来到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下游。
土尔扈特西迁,主要是由于厄鲁特四部联盟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引起的,同时,也因为受到了沙俄扩张侵略势力的威胁。新疆蒙古四部虽已形成联盟,毕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此之间,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势力日渐强大,并持其强横之力,意图兼并土尔扈特部。
至此,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对准噶尔的侮意更加不满,更不愿屈从准噶尔部,丧失本部落的独立性与自主权。于是,便于1628年(明崇祯元年)通知联盟各部首领,决定就此分离。
从此,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于1630年前后,西迁来到当时还未被俄国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游牧部落。
正当土尔扈特蒙古人挥舞着牧鞭,沉浸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乐园之中,北邻的沙皇俄国,为巩固其既得利益,已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扩张蛮势,伏尔加河流域从此就成了沙俄觊觎和侵略的主要对象。
土尔扈特蒙古人开始反抗了。
这个历来不愿“为人鞭下之奴”的民族,为了寻求自由,举起自制的箭镞与火枪,骑上曾经征服过世界的蒙古马,高举蓝色鹰旗,蔑视着涌入伏尔加河流域的沙俄,举弓怒射,大展刀剑长矛,以烈酒般蒸腾的豪情,东方人的自豪,史诗一般的语言,公开向沙俄宣战!
苍天,赐给我们的牧场,
大地,赐给我们的河流。
山峰,赐给我们的自由,
溪水,赐给我们的快乐。
……
战旗猎猎,战歌飘飘。土尔扈特人用赤诚的心在唱,他们是如此地依恋着曾经给予过他们无比快乐的家园。
他们——
把伏尔加河之水,当做安抚土尔扈特蒙古人的上苍。
把阿赫图巴之水,比做养育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母亲。
把乌拉尔河之水,比做滋润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圣乳。
英勇善战的土尔扈特人,把伏尔加河看成是一片不容沙俄欺侮的神圣领地,将这片神圣的领地,视为上苍赐予的家园。在西迁倡导者——和鄂尔勒克设帐的阿赫图巴河畔,为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土尔扈特人聚集在一起,立下了震撼山河的誓言。
为自由而战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在捍卫与赞颂这片神奇土地之时,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俄国是奴隶之国,祖国是理想之邦。
宁为大清鞭下奴,不为俄国鞭下马。
乾隆三十六年(1771)1月5日,英雄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刻写下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俄国的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东方!向着东方!”
这一天,在三万三千帐近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的呐喊声中,东归英雄渥巴锡汗亲手点燃了庞大的木制宫殿,以破釜沉舟的义举,带领部族,离开了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踏上震惊世界的东迁之路。
1771年2月初,土尔扈特蒙古人在沙俄军队的残酷追杀下,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穿过奥琴默峡谷,奔向通往祖国的必经之路——吐尔盖河。
正值严冬,白雪皑皑的东迁之路,撒满了土尔扈特人捍卫民族尊严的热血。
宫殿的熊熊大火,象征着一去不再复返的决心。
滴滴鲜红的血液,怀念故土的热泪,一如颗颗回归祖国的赤胆忠心。历经不堪忍受的磨难,所剩的八万多土尔扈特人,高唱着东进的战歌,于是年六月底,甩掉了追杀的沙俄军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至此,踌躇满志的大清皇帝乾隆,不无感慨地用惬意而愉快的得意之笔写下了“自斯凡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刻在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的碑文之中……
这就是震撼东西方的土尔扈特人,一个让世界为之骄傲而又令人崇敬的民族!
一部描述土尔扈特蒙古人东迁历史的《鞑靼人的反叛》,再一次加深了哈斯伦德对东方的了解。
站在烈日骄阳下的古曾河畔,他的眼睛穿越东方的海岸线,土尔扈特人的祖国,像一块巨大的磁盘吸引着他,同时,他也被这个可歌可泣的民族所折服。
这一天,他对卡尔说:“上帝如果赐给我走遍中国的机会,我一定会到土尔扈特蒙古人的聚居地,亲眼去看一看这个伟大而又坚强的民族。”
这个说着日耳曼语、信奉福音派路德教的丹麦少年,这个被丹麦王国种植出的燕麦、大麦、小麦以及萝卜、马铃薯喂养大的哈斯伦德,伫立在古曾河的岸边,面向红日初起的东方,真想以梦当舟,用臂做桨,一步跨过这条河流,去找寻他久久不能释怀的异国之梦。
民国二年(1913)仲夏,进入北京女子贵族学校学习的尼茹黑德玛,较两年前出落得更加漂亮了。
十八岁的蒙古王女,面部五官及身材具备了一个东方美女的全部特征。她的身材修长,四肢均匀,手指细如葱尖;肌肤保持着土尔扈特蒙古人的特征,红润而富有弹性。最动人的是一双溢着秋水的眼睛,它时而涌动着,犹如一汪波澜,闪现出活泼与快乐,时而静如止水,闪现着宁静与沉稳。
她的性情与少女时代相比,更趋向于温顺,启唇微笑间,总会露出一副委婉温和的样子。
蒙古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易感、易善、易燃、易娱、易诚、易盟、易誓的情感。她,亦是如此。
除了多门学科外,学校还开设了音乐课和钢琴课。在音乐教师的培养下,自幼有着音乐天赋的尼茹黑德玛已充分地显示出她的音乐才能。
进入贵族学校的那一年,蒙古王女结识了一个叫作朱丽娅的法国姑娘。她的父亲原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离任后带着夫人去了英国的伦敦,而她却因迷恋中国文化而执意留在北京,与蒙古王女就读于同一所学校。
朱丽娅的汉语讲得很吃力,为此,王女就担当起她的汉语课外老师,朱丽娅教授她法语。
这位法国姑娘性格开朗活泼,她的来临让蒙古王女对法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帕勒塔王在北京就任清政府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期间,曾在北京东城区建有一座豪华的府邸。后来,被清政府任命为科布多办事大臣的帕勒塔王返回新疆后,举家迁回喀喇乌苏的王府,从此,座落在京城的王府,一直由笃诚的管家带着十几名侍卫和几名仆人代管。
每到周末,管家就会派出两名侍卫乘坐大鞍子车来到学校,迎接被他们称之为“尊贵的”公主和“蓝眼睛”的姑娘回府。
晚餐后,她们坐在王府的后花园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让她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繁星闪烁,才在女仆的催促下回到寝室。
民国三年(1914年)春天,帕勒塔王派来迎接蒙古王女返回家乡的侍卫队抵达包头。
王女和准备返回欧洲的朱丽娅一起,乘坐着北京王府管家为她们鞴好的大鞍子车,由北京王府的侍卫护送着,自北京城向西驶去,到包头与帕勒塔王派出的驼队会合,在新疆喀喇乌苏王府侍卫的护送下,骑着骆驼直线西行,进入沙漠地带。
喜欢大野芳菲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大野芳菲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