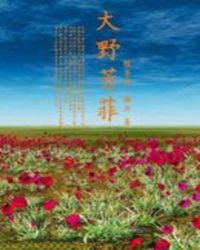在浓缩着土尔扈特蒙古人虔诚信仰的巴仑台黄庙,他有幸瞻仰到了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藏达赖13世喇嘛赠给黄庙的一尊麦德尔佛像。
转眼,春天来临。
土尔扈特人为纪念始祖在肯特山、杭爱山游牧形成的“塔格楞节”(祭敖包)即将来临,僧钦活佛的汗王府,开始为此次祭祀忙碌起来。
汗王府西面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敖包,敖包建立于土尔扈特蒙古人东归祖国的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
当年,英雄渥巴锡汗为了让族人永远牢记回归祖国的日子,特此垒石为记。印记着东归历史的敖包,在时间的推移和渥巴锡汗后裔的繁衍中,像一座不朽的山峰,永远地长存在尤勒都斯草原。
在土尔扈特人的眼里,它即是祖先敖包,也是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光辉遗迹。
农历三月二十一的晨曦,哈斯伦德在一阵法号声中醒来时,住在汗王府附近的牧民,已潮水般朝着敖包涌去。
参加祭祀的人们,身着盛装,鲜艳的服饰点缀着初绿的草滩。
汗王府内,进行着排列有序的祭前活动。
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分立在城堡南侧公园的甬道两旁,汗王府的大小官员,东归英雄渥巴锡汗的直系后裔都云集在七座帐篷庙宇前。哈斯伦德在好朋友蒙古尔达的陪同下,站在人群中等待出发。
随着一阵具有神威的低沉法号声,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手持“浩日特”(即**)开道,尾随在他身后的数十名喇嘛乐队也从庙宇中走出来,随后,此次祭祀活动的主祭人僧钦活佛也随着手托祭盘的喇嘛们依次鱼贯而出,同时,手持“黑白族纛”的两个骑兵,也加入了祭祀的队伍。
**开道,“黑白族纛”引路,数千人组成的祭祀队伍就这样步行着,朝着他们心目中的圣地敖包走去。
几天前,伫立着敖包的山脚下,还是空无一人的草滩,现在,沿途中,数百座雪白的毡帐在一夜之间,如同蘑菇群钻出草滩,星棋般布满山脚。
远道前来参加祭祀的牧民们,在祭典尚未来临时就在此扎营,等候参加祭祀敖包的活动。
赫然挺立在山坡上的敖包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祭祀队伍立刻安静下来。祭祀的人们看着敖包,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英雄渥巴锡汗,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祭祖先敖包的仪式还没开始,有些牧民就翻下马背,摘下帽子,跪在山脚下,双手合什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祭祀队伍稍做调整,大形的祭祀活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辰里开始了。
敖包面向南方,用石头垒起的敖包顶端插着柳枝,柳枝上悬挂着五色幡旗。土尔扈特人视鹰鸮为图腾,矗立在敖包顶端的敖包杆上除了镶嵌着日、月、火图案,还立有一只象征着“族神灵”的木雕鹰。
在蒙古人的心里,敖包是神灵的栖息之所,是顶礼膜拜的圣地,是神圣之所在,即便不是祭祀的日子里,经过此地者,必下马添石表示敬仰之心,否则为不敬者。
“凡我土尔扈特人,自古都以牢记祖先的业绩为荣幸之事,英雄的渥巴锡汗是指引我们回归祖国的族鹰,为此,‘九九祭’祭祀敖包仪式现在开始……”
僧钦活佛咏诵《敖包祭》经和致祭词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间,这声音冲撞着山谷的岩石,冲撞着广大民众感怀祖先的情感。
《敖包祭》的致祭词完毕,立鼓、大钹、法号、羊角号、铜铃、叮沙(撞钟)、达姆乳(摇鼓)、海螺、两丈长的大“筒钦”(长号)齐奏。手托祭盘的喇嘛们走向用九块平石垒成的祭台,将祭盘中的各种奶制食品和奶酒供在祭台上,点燃香炉中的供香。
随着袅袅升上天空的圣烟,祭祀敖包的活动达到沸点。在主祭人僧钦活佛的带领下,数千名参祭者分别拾起三块山石轻轻地垒在敖包上,跟着僧钦活佛口念啊、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围着敖包绕行三圈。此后,众人向敖包献“三宝”(盐、茶、肉)、口念祭祖之语,向敖包敬献哈达的活动才真正开始。
渥巴锡汗的后裔们,已无法抑制情绪,他们手托哈达“噗噗嗵嗵”地跪在敖包前,在喇嘛的带领下,从他们的始祖王汗喊到带领他们回归祖国的英雄渥巴锡汗,又从渥巴锡汗喊到僧钦活佛和小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名字。
有的人,还像背诵史诗一般,抑扬顿挫地念诵着祖先抗俄的英雄事迹,缅怀他们对部落以及族人的种种恩德,连续叩拜九次,才向敖包敬献哈达。
有的牧民甚至长跪不起,面对敖包手推胸椎,祈祷或哼唱着赞颂祖先的民歌,甚至泪流满面。
一直陪伴在僧钦活佛左右的哈斯伦德看到了,宏大的祭祀场面,使得这位活佛的眼睛晶莹一片。
这位让全体土尔扈特民众为之敬仰的活佛——英雄渥巴锡汗的化身,心,已回归到平民之中,成为民众中普通的一员。
他长时间地站在那里,不再以摸顶的方式,赐予民众吉祥的祝福,而是面向着一队队走向敖包的民众,背诵着祖先留给后人的格言,向民众讲述部落的迁徙历程。
活佛还向女孩子们讲述,座落在草原上的敖包是地母神的象征,是蒙古人崇拜敖包的根基,她们长大成人后,要像她们的母亲一样,教育后人永远敬仰敖包。
他还抚摸着男孩子们的头顶,告诉他们,土尔扈特人之所以把“上苍看成是阳之本”,是因为他们把太阳看做是光辉的父亲和男子汉的形象,也是天神的代表,从容大度和剽悍的具体表现,阳刚之美的具体体现。
他还像父亲一般,谆谆教导着孩子们,要长久地保留着拜肯特山、杭爱山、斡难河、叶赛尼亚河、伏尔加河、阿尔泰山、开都河、天鹅湖、天山、辽阔的草原这一习俗,不要忘记祖先游牧迁徙的历程。
活佛的眼睛里充满慈爱,他一边对孩子们述说着,一边将祭台上的奶干、糖果分发给孩子们。
在情感的交流中,这位遍体金光的活佛,已成了普通孩子眼睛里的父亲,浑身充满魔力。
敖包前人山人海,祭祀的场面异常壮观。面对庞大的祭祀活动,哈斯伦德像真正的土尔扈特人那样,与僧钦活佛一起亲手拾起三块山石添在敖包上,献上洁白的哈达。
他已忘记了自己是西方人,涌动在胸膛里的血液,和蒙古人一样冲动,对敖包充满崇敬之情。
《清会典》规定,蒙古“游牧交界之所,无山无河为志者,垒石为志,谓之敖包。”
矗立在哈斯伦德眼前的敖包,不再是“垒石为记”的标记。敖包将与天地同在,与蒙古人同在,与世界永存。
它,会随着日月的运转增高,会因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五色的幡旗,在敖包顶端飘动,向着辽远的蓝天,广袤的大地,诏示着它的神秘。哈斯伦德面对的,是蒙古人的丰碑,是蒙古人眼里的圣殿!
绿色幡旗,是蒙古人的母亲神,是生命之色。
蓝色幡旗,是崇拜苍天的象征,父亲的形象。
黄色幡旗,象征着光芒的大地,兴旺的景象。
白色幡旗,是蒙古人渴望吉祥的象征,纯洁之色。
红色幡旗,更像是蒙古人时刻沸腾的豪迈血液,延续着这个民族的骁勇。
敖包,似一座神邸,静立在山坡上,它仰望着蓝天,俯瞰着脚下的世界、对它朝拜的蒙古人。
蒙古人认为,天赋予人生命,地赋予人形体,他们由此才尊苍天为父,大地为母。
哈斯伦德感受到,这神圣的敖包,为什么会具有如此这般的向心力,会具有如此的神威。他真正地理解了,为什么有的牧民策马经过长途旅行,携带家人来此参加祭祀的意义。面对神圣的敖包,一个北欧人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之所在折服了。
盛大的祭祀活动,包括“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的那达慕活动,从太阳尚未升起的时辰,一直持续到太阳转头向西移去,方才结束……
哈斯伦德从祭祀敖包的场地归来,已是撑灯时分。随着夜晚的来临,城堡内安静下来。
他的心一直处在激动之中。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他用西方人的眼睛和西方人的心灵了悟到:座落在草原上的敖包,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用石头为自己垒起的一部历书!
草原上,敖包的种类很多,有和硕敖包(旗敖包)、努图克敖包(乡敖包)、艾力敖包(屯敖包),还有巴颜敖包(喜庆)、白音敖包(致富)、先祖敖包、纪事敖包以及马敖包等不同的敖包。有的敖包已存在千百年,它被蒙古人的祖先垒起,就溶汇着祖先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缅怀先祖的夙愿,成为蒙古人的保护神。在哈斯伦德的眼睛里,每一块石头都是一块有知有觉的灵魂。
敖包,浓缩着蒙古人的全部精神,浓缩着蒙古人对生活的全部热爱,它使游牧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是蒙古人的爱之圣殿!
新的葛根殿,已复制完毕。
它是一个令哈斯伦德失望的神殿。
他站在复制的葛根殿前,被一种新的情绪所困惑。
崭新的帐篷庙宇,没有经年日久所产生的那种原始气息,缺少古老的光泽,尤其是那些献祭的器皿,它们完全失去了因常年磨擦所产生的寓意。
这一切,都使复制的庙宇缺少了浓厚的神秘味道。重要的是,这座庙宇,没有溶进土尔扈特人对宗教的那种炽烈的忠诚。
他的失望是多余的。
僧钦活佛看出一份失望从他眼睛里流露出来,当即留下复制的葛根殿,慷慨地将散发着古老宗教气息的葛根殿献了出来,送给了瑞典古斯塔夫五世国王。
这一时期,斯文·赫定正在美国,为考察团的生存奔忙着。哈斯伦德接到了瑞典方面的指示。瑞典当局决定,由他护送活佛赠送给瑞典国王的帐篷庙宇前往迪化,等候新疆政府允许他将这座帐篷庙宇带出新疆的指示。
分别在即,视友情为重的蒙古人,依次拍打着外国友人的后背,送上一句又一句的吉祥祝福。
哈斯伦德与僧钦活佛之间的感情在长久的相处中,已趋于完美,活佛对即将离开汗王府的丹麦朋友非常留恋。
“甘言,醇酒,美色,都是醉人的魔王,喜乐的极点,便是晕狂!”这是活佛经常告械人们的话。
活佛与众多的蒙古王公有所不同,鉴于信仰又皈依佛门,他是忌酒的。他不主张人们像他一样忌酒,主张人们在喝酒时不要忘记,圣祖成吉思汗当年的训导。
下午,哈斯伦德来到僧钦活佛的书房,二人以茶代酒,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们从西方谈到东方,就像喝着烈酒,频频地碰杯,说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丹麦人的梦想,是尽快地回到尤勒都斯草原,这恰恰迎和了活佛的愿望。
夜里,活佛用整整一个晚上,为即将启程的丹麦朋友祈祷着,祝福他平安地抵达自己的祖国。
这个季节,尤勒都斯草原被春天染得一片碧绿,站在城堡内,可以听到从远处冰山上传来的淙淙流水声。聚居在城堡附近的牧民们,也开始顺着流水的声音而去,去寻找更为丰美的牧场。
第二天清晨,阔别丹麦七年的哈斯伦德与僧钦活佛依依惜别,带着六名护送帐篷庙宇的土尔扈特骑兵启程了。
与离开黑天雕草原时的心境相比,他的心情已经截然不同。他决定,在祖国与母亲做一次短暂的相守之后,他还会回到土尔扈特人民中间。当他视游牧文化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库,就把尤勒都斯草原当做继续研究蒙古民俗的基地。
哈斯伦德与僧钦活佛最后告别时,僧钦活佛将祖先的遗物——英雄渥巴锡汗曾经使用过的一支滑膛枪赠送给他,还将土尔扈特最名贵的一匹骏马送给了他。
那是一匹驰名全国的焉耆马,是活佛从俄国引进的中亚马种的后裔。经过改良后的焉耆马,体态适中,两耳竖立,胸廓宽厚,蹄质坚硬,敏捷温顺,善走能跑,具有持久耐劳的特点。
哈斯伦德在一曲轻快的进行曲中启程了,在活佛“平安归来”的祝福声中,踏上前往迪化的路程。
此一去,他将不会带着凝滞的神情去回望这片土地。他确信自己还会回来,不仅要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一场深入彻底的文化研究,还将在这片土地上一直等待下去,直到见到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
在他的臆想中,如今的蒙古王女,已经成了一位具有真实形象而又完美的女性!
喜欢大野芳菲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大野芳菲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