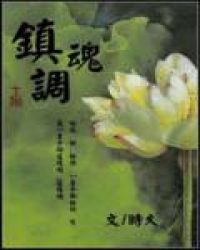菡玉从来没有连续赶过这么多路。从井陉东口回京师,近两千里的路程,来时花了十多日,回去竟只用了四天。她反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要镇静,不要着急,手中的马鞭却停不下来。若不是随行的其他人熬不住,或许她真会马不停蹄一口气奔回长安去。
六月初三中午行经潼关。潼关两侧是高峻山壁,依山而建,城墙与山石连为一体,远看如一道大坝截断山隘,拔地而起数十丈,无从攀援,当真是一道雄关。菡玉亮出官牒,潼关守将便放她过去了,畅行无阻。
潼关内有朝廷派给哥舒翰的八万将士,并高仙芝封常清旧部共十四万余,号称二十万。入关后只见山坳腹地密密麻麻的营帐,近处还一座座看的分明,到远处就连成一片,遥不见尾。哥舒翰治军严厉,十几万人驻扎的营地竟是悄寂无声,只听到山风从顶上刮过,吹得旌旗猎猎作响。
忽一声呜咽,由低而高,如劲风掠过空穴,声音不大却是尖利非常。紧接着嚎啕声起,竟是妇人孩童的哭喊,在这肃穆沉寂的营地里显得格外刺耳鲜明。
菡玉因问那引路的守将:“军营中怎会有妇孺,还喧哗恸哭?”
守将道:“这是罪人的家眷,来领尸首的。”
菡玉问:“罪人?是谁触犯军规?”
守将答道:“是杜乾运将军,前日刚被斩首。”
“杜乾运?”她皱起眉,“可是左骁卫大将军?”
守将道:“正是。不过他统领的一万军队前几日已经划归潼关管辖了,应算是哥舒将军副将。”
菡玉点点头,又问:“杜将军为何获罪斩首?”
守将也觉得难以启齿:“是因为……杜将军贪图享乐,从长安私运酒馔……哥舒将军向来严以令下,如今又是危急存亡之刻……”
就因为贪口腹之欲便将一员大将斩首,哥舒翰治军再严,这理由也难服人。何况这杜乾运……还是杨昭亲信。
菡玉不再多问,匆匆告辞。潼关到长安还有近两百多里路程,又走了半日,总算赶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天色也擦黑了。
她看天还未黑透,便先去了省院。三省六部灯火通明,尤其是武部,战时数他们最忙碌。菡玉报上来历,立刻得到召见。
竟是左相韦见素在主持全局。他兼任武部尚书,大约是最近操劳过度,容色憔悴不堪,看到她还是打起了精神招呼:“吉少尹,你可算回来了。你一走这三四个月,也没个音信,右相他……”
菡玉打断他道:“下官也是为战事所阻。如今郭李二位大夫在河北打了胜仗,大破史思明五万大军,河北稍定,我才得以回京,并献捷闻。”说着取出战报递上,“此战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获军马万匹,捷报上都有细数,请左相过目。”
“好,太好了。”韦见素喜上眉梢,接过军报大致浏览一遍,又问:“少尹是今日刚回的京师?”
菡玉道:“大夫所托,下官不敢延误,一回京立刻就来见左相了。”
“少尹辛苦。”韦见素合上军报,“那少尹还没见过右相了?”
菡玉道:“本准备将捷报交付左相后便去文部拜见。”
韦见素道:“右相现在不在文部。”
菡玉一怔,说:“那明日朝上再见不迟。”
韦见素微微摇头:“少尹今日要是不忙,就去右相府上探一探他罢。”他略一停顿,叹了口气,“前日他路遇刺客,受了重伤,这两天都告假在家休养。”
菡玉心头一紧,追问:“严不严重?”
韦见素道:“右相闭门谢客,我也未及上门探访。但以右相行事,若是不严重,也不会丢下朝政大事不管。少尹就代六部同僚前去一探,也好让大家定一定心。”
菡玉心乱如麻,摇了摇头,见韦见素看着自己,又忙点了点头。辞别韦见素出了省院,她也无心回自己寓所了,策马直奔杨昭府邸。
门房全都认得她,告知相爷人在书房。书房门外照例是杨宁在守着,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杨昌正端着一盆水从屋里出来,四个月没见,看到她忽然回还一点也不诧异,微笑道:“少尹,您回来了。相爷就在屋里,少尹请进。”仿佛她只是如平常一般从府衙回来。
她有些紧张,脑子里胡乱闪过各种各样可怕的画面,进门就见他坐在书案旁,一颗悬着的心猛然落了地,却又不知所措起来,停步站在了门口,呆呆地望着他。
天色已黑透了,书房四角都昏昏暗暗的,只他身侧一丛烛台火光熊熊,照见那张四月未见的面容,霎时与脑中多日来萦绕的容颜重合。他粲然一笑,便叫那一树流光都失了颜色。
“怎么,没看到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很失望么?”
他左边袖子卷起,半条胳膊上打满了绷带。一旁大夫打开药箱来帮他换药,他摆一摆手,大夫放下药盒退出门外。身后房门轻轻关上,她犹站在门边,忘了走近。
“玉儿,你再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真要以为你是数月不见思之如狂,见了我惊喜到连话都不会说了。”
菡玉回过神来,脸上一红,垂下眼走到他近旁。“听说相爷前日遇刺,两日不理朝事,要不要紧?”
他笑问:“你是问我要不要紧,还是朝事要不要紧?”
她红着脸不答,蹲下身去,低声问:“我能看一看么?”
他心中一动,点头道:“正准备换药呢,拆吧。”
她仔细地检查了一周,看清楚纱布是怎么缠的,才动手去解。第一下碰到他手臂,他微微一颤,她连忙缩了手:“疼么?”
他深吸一口气,缓缓道:“不疼。”
她更加小心翼翼,慢慢将纱布揭起,一层一层绕出解开。他从未见她如此尽心地对自己,便是那次为救她出狱而自灼手臂,她也是感激有余关怀不足,匆匆包扎了事。他有些受宠若惊,心中甘苦交杂,又舍不得这片刻温存,心想就算她又像临走前那样虚意逢迎,能让她如此对待,被骗也是甘愿。遂柔声道:“玉儿,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你若有什么要我帮忙只管直说,我一定都依你。”
她手上一顿,脸色渐渐沉下去,闷闷道:“我没有什么要相爷帮忙。”
他轻叹道:“我不会介意的。”
“原来在相爷眼中菡玉是这般功利,只有要相爷帮忙的时候才会来假意讨好。”她放开他站起身,“我去叫大夫进来。”
“玉儿……”他一抬手拉住她,大约是牵到了伤口,痛呼一声。
“相爷!你、你别动!”她以为自己伤到了他,顿时慌了,回身又蹲下,捧着他胳膊的双手却不敢立即放下来,“你别动,慢慢来。这样疼不疼?”
他摇摇头,脸上却在笑着:“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他越是这样说,她越以为他是在强忍,心中又悔又怜,动作更柔。待到拆开纱布,只见一道三四寸长、半寸宽的伤口斜贯小臂,已经结了痂,并未裂开出血,看起来并不深,只是那血痂泛着微微的青绿色,烛光下看来有几分瘆人。
她的声音微颤:“刀上有毒?!”
他本以为她看到之后会恼怒,谁知她如此紧张,竟是关心则乱,不由心下大动,生生忍住,软语道:“已经内服过解毒药了,刀口上沾的一点余毒不妨事的。”
“这血痂里都有毒,就怕万一再渗到血脉中去。大夫确认没事么?”
他盯着她忧心的面容,心中顿时溢满柔情,轻声问:“玉儿,你不恼我?”
她抬起头:“我恼你什么?”
“恼我……骗你。”
她疑惑道:“骗我?相爷瞒了我什么事?”突然脸色大变,“难道这毒……”
他连忙撇清:“不是不是,你别乱猜。”
“那是什么事?”
他不知该如何说起,想想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人人都说我骄横跋扈,却不知其实我骨子里这般不自信。”
她凝眉不知所以。他许久才止住笑,指了指药箱:“没事没事,换药罢。”
她无奈地瞪他一眼,拿起大夫刚刚放在一边的药膏,又拎过药箱来翻了翻:“只敷这一种药么?有没有其它外用的解毒药?”
“这盒药膏是多种药材调配好的,只用它便可。箱子里有一个白瓷罐子,每次都是用里头的药水洗了伤口再敷药。这药不能直接涂在伤口上,需先敷一层纱布。”
“我知道,这些事我以前常做。”她先盥了手,取过那白瓷罐子,用净布蘸了药水为他清洗伤口。一下一下轻轻点拭,若即若离的清凉触觉,竟毫无不适之感。
“以前常做?你以前行过医?”
她笑道:“也不能算行医,只是经常帮人处理外伤,医病我可不会。我没学过岐黄之术,久病成医无师自通而已。”
他眉毛一挑:“久病成医?”
她洗完了伤口,放下瓷罐去拿纱布。“以前在外行走,受伤是家常便饭,医馆可不是随处都有,只能买些药带在身上,自己胡乱摆弄多了也就熟悉了。尤其到后来城池镇甸都毁了,往往几百里也看不到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来。那时我经常闯入店铺人家,随意拿别人的财物,就像山贼匪寇一般,如入无人之境,”她玩笑似的说着从前经历,笑容里却掩不住苦涩,“因为满城都没有人了。”
他这才明白她说的以前其实是以后,她还是小玉的那段时间。他轻声问:“是因为战乱?”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归根究底是因为战乱。”
他沉默片刻,才问:“玉儿,六年后究竟是何境况?”
她不答反问:“相爷,如今长安城内有多少人?”
他想了一想:“不下百万。”
“那如果长安城里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一百万具尸体,相爷说那是什么境况?”
他微微吃惊:“安禄山竟如此凶残,将长安百万之众全部屠戮?他造反是想自己称帝,把京师屠城,他不想坐这江山了?”
她只是摇头:“安禄山没有屠城,他自己也是死于非命。”
他略有些明白。安禄山手下胡人居多,不若汉人从小受礼仪教化有三纲五常尊卑观念。安禄山自己犯上造反,便是给他下属带了个坏头,可以想见日后必是一团糟乱。他看她愁眉不展,有些后悔自己说这话题让她想起从前遭遇,便岔开话道:“玉儿,别发呆了,再不给我包上,纱布上那药膏都该结成块了。”
菡玉回过神,把药膏在纱布上涂匀了,再覆上一层,就着他臂上伤口裹住,照原来的样子用绷带一圈圈缠紧,一边缓缓道:“相爷,我今日从潼关经过,看到左骁卫大将军杜乾运……”
“被哥舒翰借故斩首,前日我就知道了。”他皱起眉,“是我一时大意,杜乾运手下一万兵力被他釜底抽薪,现在索性连杜乾运自己也送了命。”
她沉默片刻,才迟疑道:“相爷,那刺客……”
他知道她要问什么:“我仔细盘查过了,没有人指使,完全是私怨。玉儿,你可还记得吴茵儿?”
她垂下眼点了点头。吴茵儿是她第一次刺杀安禄山失败后,被杨昭栽赃顶罪的驿馆侍女。
“这回的刺客就是吴茵儿以前的未婚夫婿。他俩虽然因为吴茵儿被安禄山霸占而退了亲,这刺客对她还是念念不忘。前日我从他家附近经过,身边扈从不多,被他撞见,便趁机持刀刺了我。”
她心下愧疚,又不知该道谢还是该致歉,片刻之后方道:“这刺客也是个痴人,退了婚的女子,都九年了,还这般执念。”
他笑道:“他好歹还定过亲,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还不是一样执念这么多年,怎没见你夸过我?”
她心里正难过,这个时候被他调笑,颇是不自在,默默地替他放下袖子来。
他又道:“我这条胳膊也算多灾多难,又是刀砍又是火烧,能留到现在还真是福大命大。”
每次受伤还都是因为她。她低声道:“是菡玉对不住相爷。”
“那你打算怎么弥补?”
菡玉一窘。他继续谑道:“你当了这么多年官还是一穷二白两袖清风,也没什么财物可以送我,又不像杨宁有一身本事,看来除了以身相许还真没有别的法子了。”
菡玉双颊飞红,腾地站了起来:“相、相爷有伤在身,该好好休息保重,下官不打扰了……”转身欲走。
他追上一步,伸手拉住她:“玉儿,时候不早了。”
她回过头,他的脸背着光,没在阴影中看不清楚神情,只听到喑哑低沉的语声:“留下来过夜罢。”
她一怔,他的双臂便立刻环了过来,将她严严实实地圈住。她张口欲言,他的脸又覆下,话未出口就叫他全封在了唇齿间。他的气息热烈而熟悉,顷刻将她缠住,无处可退。她只觉兵败如山倒,毫无抵抗之力,完全落入他掌控之中。他伸手一抄将她抱了起来,转身大步向内里的床榻走去。
她费尽全力将他推开寸许,呼吸都已不顺:“相爷,你的手……”
“没事。”他将她放到榻上,立即又缠上来。她只隐约想起,去年……也是在这张榻上,就再无空暇去想其他事。
门外突然传来笃笃的叩门声,菡玉一惊,手忙脚乱地推他:“有人敲门。”
他哪里肯停:“不管他。”
她好不容易避开他的围追堵截,连连喘气:“也许是有要紧的事……”
“怕什么,天塌下来也有我在上头。”他顺势向下转移,轻咬她的脖子,手溜进她袖子里,顺着胳膊一路向里探去。
菡玉满面通红,又挣不过他。门外的人也着急了,朗声道:“相爷,中书舍人宋昱有要事求见。”正是杨昌。
杨昭仿若未闻,仍是不停。菡玉却明白杨昌明知他俩在屋里还来通报,定是事出紧急拖延不得,挣扎道:“你先见过宋舍人……”
这时杨昌又喊了一声:“相爷,宋舍人有要事相告,望相爷赐见!”
他这才停住,怒道:“叫他明天再来!”
杨昌还未回答,宋昱已经等不及了,抢道:“相爷,潼关有变!”
杨昭黑着脸坐起身,见菡玉大松一口气的模样,更加恼怒,欺身上来狠狠咬住她唇瓣。她痛得龇牙咧嘴,又不敢叫出声,只能睁大眼瞪着他。他这才满意,放开她低声道:“你别得意得太早,我一会儿就回来,到时候叫你尝尝什么叫变本加厉。”
菡玉脸上滚烫,垂下眼去不敢看他。他转身出门,将房门虚掩上,就听宋昱嘈嘈切切地说了一通,杨昭冷笑道:“好个哥舒翰,我一再忍让,他真当我是怕了他了。把陛下今天下午那道圣旨连夜给他送过去,看他还敢不敢搞这些名堂!”
宋昱应下,又问:“那京师这边……”
杨昭道:“既然他们耐不住性子了,那我也只好奉陪。”低声对宋昱嘱咐了几句,宋昱领命而去。
他回到屋里,见菡玉正坐在榻边整理衣衫,笑道:“别穿了,反正也阻不了我片刻。”
菡玉忍着脸红,问:“相爷,潼关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一点小事。安禄山还在洛阳做他的春秋大梦,用不着你担心。”他走近来坐到她身边,欲摁她肩膀,被她躲开,又问:“那陛下的圣旨又是怎么回事?”
他懒懒道:“哦,陛下让哥舒翰出关收复陕洛,他一直不听,只好下道圣旨催催他了。”伸手去搂她,却被她一掌打开,啪的一声,分外响亮。
她脸色都变了:“你让哥舒将军领兵出潼关?”
他纠正:“不是我,是陛下。”
“陛下难道不是听了你唆使?”
他略有些不悦:“什么叫唆使,说得这么难听。”
菡玉深吸一口气,稳住情绪。“相爷,你和哥舒将军的私怨能否先放一边,眼下最要紧的安禄山。哥舒将军失了潼关险地优势,难敌安禄山精兵,潼关不保则长安危矣。相爷一定也不希望长安百万民众尽亡之幕再度上演。”
“我当然不希望,不过,前提是我得活得好好的。”他眉梢微挑,“要是我自己的命都没了,别人是死是活跟我还有何关系?”
她忍着怒意:“哥舒将军并不想要相爷的命。”
“他不是不想要,他是不敢。”他眼角露出鄙薄的冷意,“有人劝他上表请诛我这个奸相,他不肯;人家又劝他派兵把我劫到潼关杀了,他说那样就不是安禄山造反,而是他哥舒翰造反。他当然想要我的命,就像这满朝文武百官,想要我死的多了去了,只是没人敢出这个头。所以哥舒翰只敢帮着扯扯我的后腿,夺我的兵力、杀我的心腹,至于我这颗项上人头,还要等着别人来取。”
菡玉疑道:“别人?朝中除了哥舒将军,还有谁能和相爷一争高下?”
“正是因为争不过我,所以才要我死啊。”他笑睨着她,“玉儿,敢情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谋划着要我的命呢。”
她紧紧蹙起眉,犹豫半晌,缓缓说出一个名字:“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他笑容愈深:“看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多。说说看,你还知道些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他,目含悲戚。“我还知道,潼关被叛军攻陷,长安危急,相爷建议陛下幸蜀,西行至金城县马嵬驿,将士饥疲愤怨,兵变暴乱,将相爷乱刀分尸,杨氏一门尽死乱兵刀下。”
喜欢镇魂调请大家收藏:(321553.xyz)镇魂调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