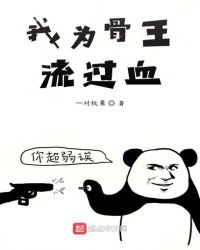入冬那天,妈妈抽着烟,指挥白衡把她买的那些村气的淡灰色布褂子发给我们。
大家伙儿怨声载道,尤其是平日里以自己傲人身躯为招牌的那几个女人,横着眼,两根手指捻了灰褂子灰裤子。
“是不是我们还得梳两根麻花辫儿来衬这土了吧唧的衣服啊。”
阴阳怪气儿的声调引得大家伙儿都笑了。
妈妈一脸猪肝色,翻了两下白眼,“滚滚滚,有劲儿朝那些大爷们使去,别跟我这儿添堵。”
一伙儿人叽叽喳喳小声埋怨的都走了。
我被妈妈给叫住。
她从烟盒里捻出一根烟,递给我,我摆手,咳嗦了一阵。
“有病抓紧去治。明明自个儿就抽烟,还对烟味儿这么过敏,你丫不是变异人类吧。”
玩笑开的不咸不淡,我看出来她有话说,犹豫半天,最后也没能把自个儿给逗笑。
“有话您说!”
她捻了烟,看我一眼,皱眉,说:“干咱们这行,走了第一步,往后甭管是十万步也好,还是一百万一千万也好,就一步都不能回头了。”
我笑着把玩儿她前段时间给她那个老相好买的烟灰缸,干干净净,看起来还没用呢吧。
“以浅啊,别对那小子动了心,他可不是什么善茬、”妈妈冲我苦笑一下,继续她的话题,“这种骨子里贵气的人可比那些大金链子小手表的暴发户难搞多了,一个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最后你想给自己弄个坟,恐怕骨头渣渣都找不到!”
我心里咯噔咯噔,疼的厉害。
她是过来人,我在想什么,我每天心不在焉的陪人喝酒,她都能看出来。我也不想隐瞒什么、
打和许朗在地下室分开这一个月以来,我白天晚上,只要脑袋沾了枕头,眼前过的全是许朗的画面,全是他胸膛里传来的响亮声音。
“好,我知道了。”
我躲在休息室里,拼命抽烟。然后满屋的烟气,把我自己呛到差点儿窒息、
我打小讨厌烟味儿,确切的说是妈妈死后,我梦境中那灶台前的烟火味儿呛得我全身器官都疼。弟弟在我梦中鼻涕和泪涂满脸,瞪着惊恐的大眼睛跟我说,他不想跟人贩子走。
“没事儿吧以浅姐,怎么一身的冷汗啊。”
白衡递给我一张纸。
我摇摇头走开,手机在包里一直震动。
“快回来吧,你妈想不开要自杀了。现在脑袋已经搁在白绫上了,你要是再不回来,真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了!!”
我呛着眼泪说好,马上回去。
走廊里的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抹去眼泪,高傲的走出夜场、
————
“说吧,这次是钱让人偷了,还是被人借了不还?”
我点了根烟,笑着看座位对面愁眉苦脸的养父。
养母坐在阳台上,呼天抢地的哀嚎。
“你听我说以浅,”烟灰缸被他推过来,“前几天你妈她受了人家的骗,借了高利贷去赌?就昨儿晚,人家高利贷堵门了!说要是不再不还就火化了我们老两口的骨头下饭吃!”
我站起来,刚走两步,就被他扯了胳膊,“别走以浅,我没说完呢。”
我甩开他手,重新坐沙发里。
“真的是被逼到没有办法了,但凡有一点儿办法也不能腆着我俩这老脸求你,我们知道你挣钱不容易?可是你看这!!”
“哎呦呦,真是天杀了啊,让雷劈死我这个老婆子吧,我混蛋啊,连累了自己的闺女,我真该死啊!!”
养母倒配合不错,一声高一声的哭。
“最后一次!”
“好好好,就当你报我们养你这么多年的恩了。”养父赔笑。
“最后一次恩?”我看他,他眼神儿缩了回去。
要是我没记错,这俩人儿在我面前演双簧,要死要活让我去挣大钱,逼得我走投无路当了陪,女的时候,他们好像就说了。那是最后一次、
“多少钱?”
“二百万!”
我笑笑,二百万,二百万,扒皮抽骨都没办法去筹这二百万。他们倒真是敢借,也真是敢开口。
我给那些之前来夜场点我的老板们挨个打了电话,他们基本都没接,仅有少数接了,斥责我打错了,然后无情挂断、
果然男人的话都不能信,之前的信誓旦旦呢,什么共患难,全是狗屁。
妈妈突然推门儿进来,二话没说,让我换衣服。
“就穿今儿发的衣服,楼上最贵的包间!”
那身衣服虽然是紧身儿的颜色比较质朴,但谁都没想到,会那么透,料子薄的一掐就能破。底裤颜色看的一干二净。
倒是胸显得特别大。
坐在一老板身边儿,他正跟边儿上的其他人讨论他最近找的那个傍家多漂亮多漂亮。
“比这丫头还要细嫩!”
“嚯,那可够真够嫩的。”
我只能陪着笑,看着他们对我指指点点。
我陪的那老板,看我一眼后突然停顿了,“嘿,这丫头今儿穿的挺别致,要啥有啥啊。”
“那是,不是看苏老板您来了么,您可是我们的贵客啊。”
“这小嘴儿简直抹了蜜了。今儿高兴,只要你能喝完这瓶子酒,就给你这个数,怎么样。”
五根手指头,五万。
“好。”
一瓶伏特加,喝到一半儿,上头了,脑袋晕不说,嘴也发飘,嘬不住瓶嘴儿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着喝完了那一瓶子,歪头笑得低廉,“苏老板,五万。”
钱拍我手里,厚厚五叠,特踏实。
胃里翻腾,我用最快的速度跌跌撞撞走出包厢。
倚墙上大口大口喘气儿。
白衡抱着一方形快递盒子,“姐,这是你的快递,在吧台,我给你拿过来了。”
我点点头,推开他手,打开、
“我擦?”白衡吓得退后几步。
血淋淋,腥臭味儿。
我张嘴就吐了。
盒子里那半截手指,滚到地毯上,离我呕吐物不远。
纸条斜贴在顶盖儿上。
还钱,不然下次就是一条腿!
“报警吧姐!”
“滚!”
清洁员忙不迭的打扫,我扶着墙慢慢往前挪,白衡也很无奈的跟着。
即使这样,我腿还是飘,
一个不小心撞到一人怀里。
酒劲儿上头我抱着那人的胳膊死活不撒手,我甚至都能听见自己死乞白赖的声音。
“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她要被人杀死了,手指头都被人砍了。”
“甭管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给钱就成?”
“钱?钱、”
手里拿的钱也掉了。
醉倒稀里糊涂不省人事。
等我醒来的时候,白衡一脸大难临头的皱眉看我,“完了,姐,你被开除了。”
“什么?!”
我被开除了?
他尽量轻描淡写的,描述,其实我知道事情有多严重、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撞到许朗,吐了他一身。
许朗怒了,让妈妈开除了我、
“当时你手里的钱全砸到许朗脚下,他当时愤怒的表情我都没法形容。”
完了完了,我抱着脑袋装孙子,头皮发麻。养父母的连环夺命call响个不停。
没敢接。
钱,钱,真特么为了钱,难为的要死。
“姐,我不知道你家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缺钱,昨天我给那些跟你挺好的老板打过电话,他们一个都不接,甚至还说不认识你。现在你又被许朗害的丢了工作。”
他塞给我一条毛巾,“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办法,眼下还有办法?
“反正是他害你丢了工作,你想方设法赖着他,不然,你真走投无路了!!”
白衡走后,他的这些话在我耳朵里响了一夜,抽了一宿烟。
我决定了,黏住许朗,这是我唯一的活路,也是短期可以快速来钱的办法。
虽然他救过我的命,这样不仗义,但在他眼里我无非就是一表子,就算是我对他感恩戴德,也无非是一竖着贞洁牌坊装腔作势的表子。
何必呢。